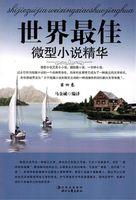二人取了几坛窖藏好酒,席地而坐,朱敬福原先还担心眼前的公子哥嫌弃铺有稻草的地面不干净,可见对方神色平静、随意大方的坐下,老人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实属多余;随即他心中一凛,那帝狮之子输给眼前这人,被打落悬崖,果真不冤枉,要知这一切都是表象,都是伪装的啊!
百里阳波拨开放在脚旁的竹叶青封泥,递给了老人一坛,二人这就喝了起来。竹叶青酒,以扬州汾酒为“底酒”,保留了竹叶的特色。再添加当归、陈皮、广木香等十余种名贵药材,有性平暖胃,消食生津的功效。
该酒色泽金黄透明而微带青碧,有汾酒和药材浸液形成的独特香气,芳香醇厚,入口甜绵微苦,温和,无刺激感,余味无穷。早年,帝君林文清对此酒大为推崇,还有‘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的赞誉流出。
百里阳波举起酒坛,灌了大大一口,抹嘴道:“不瞒老先生,小子突然玩了这么一出,老祖宗八成早已知晓;老祖宗早些年就是化灵境高手,对天地素精似有感悟,肯定感知到我在这酒窖里,之所以没来抓个现行,还不是对我这孙儿的宠爱。”
老人心下一惊,他没想到百里疆远也在抚仙楼,有些事恐怕早已暴露了,喝了一口酒,缓了缓心中的不安,道:“这世道,谁家老的不护着自家小辈?!”
百里阳波举起酒坛子又灌了一口,似觉着老人的话太过讽刺,眼神深处闪过一抹冷戾。
放下酒坛子,百里阳波又变得温煦谦和,打趣道:“听老先生的口吻,定是百般疼爱子女咯?!”
朱敬福打了个酒嗝,揉了揉褶皱的脸庞,唏嘘道:“老朱我就山中一药农,采了一辈子的药,哪有女子看得上,膝下无儿无女更无孙,有万般疼爱也是无处给啊!”
“倒是前俩个年头,在那山中金蟾岭捡到个娃儿,貌似被人从崖顶打落,全身骨骼碎了七八,老朱我看他还有一口气,就把年轻时候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几颗丹药给他服了,其中还有一颗返命丹,可把老朱我心疼得紧。”
可能酒意上涌,老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可那小子一点不争气,服了我从八荒辛苦讨得的返命丹,仍是昏迷不醒,老朱我就寻思着可不能做了赔本买卖,就将他背回了茅屋,一照料便是俩年。”
百里阳波道:“先生是个善人。”
老人叹了口气,道:“有什么善不善的,见着了总不能坐视不管,我照顾了那小子这么长时间,总有些感情,再说也不能扔在山中让野兽叼了去。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前些天他终于是醒了,这让老朱我开心得整晚都没有睡着,那心情就好比辛苦种的庄稼终于有了收成。”
百里阳波没有说话,与老人又碰了一个,如今他八成已经确定眼前的老头儿与慕怀风有关,接下来便是让对方带自己找到那帝狮之子,悬在心上的刺儿,终于要拔出了啊!
老人看了眼窗外的余辉,豁然道:“这些日子的相处,我早已将那小子当做了半个儿子,这不他醒了,就寻思着终于有了个伴儿,以后把采药的本事交给他,在偌大个祁连山脉也能活下去。哪天我老朱进了棺材,清明时分也有个上坟的人不是。”
“可我把人家当儿子,人家不把我当爹啊。”老人又喝一口酒,碎碎念道:“自那小子醒转过来,一天就跟我念叨着回金陵、回慕家,还说什么他的父亲是那一朝闻道的帝狮,母亲是云蔷薇。”
百里阳波食指有节奏的敲击着膝盖,若有所思。
“老朱我虽是山野鄙夫,早年还是走过很多地方,甚至还到达过剑荒,武道修为虽说弱得可怜,但还算见过世面,帝狮的名号自是耳熟能详。万一我收留的小子真是那帝狮之子,借我百个胆子,也不敢当对方的老爹呐!”
朱敬福挪了挪屁~股,出声道:“这不就寻思着老朱我先来金陵打探一番,若那人真是帝狮之子,可得让幕府的人尽快将其接回去,现在那小子可经不起半点颠簸了。”
百里阳波停止敲击动作,眼神骤然一缩,语气有些急切,“先生去过慕府了?”
也不怪他如此紧张,实在是刺杀慕怀风这事牵扯太大,得罪金陵五世家之首不说,还很有可能将整个云阳王朝推至百里家的对面,最为重要的是,那人可是帝狮之子。
帝狮,何许人也?单论坊间的传说就足够震慑人心,一指败云阳帝君,在那八荒的藏青云地连败七曜世家之主,连机枢阁都未能给出准确修为,这样的传奇,世间能有几个?恐怕就算猛如徐势舟,都不敢说稳赢帝狮吧?
传说之所以是传说,不正是因为它的逆天和不可及?
老人接下来的话让百里阳波暂时安了心,“还没哩,这不我昨前日才骑着匹瘦马赶至金陵,却遇上浮屠惊招考这般盛况,就想着先看看城中的风土人情,再去慕府也不迟。再说跟高门士族打交道,说话可不得谨慎些?哪能像与公子这般随意扯皮,怎么也得先有个腹稿才行。”
百里阳波笑了笑,点头道:“一些高门士族规矩确实挺多,其实底蕴不咋地,说到底就是穷讲究。可慕府不同,上到少主慕兴然,下到管家门房,待人都亲和温顺,没有丝毫架子,尤其是慕老爷子,就像一朴实憨厚的老农,让人见了便亲近自然。”
“所以老先生担心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如今来了金陵,想必先生也听说了慕家二少爷、也就是小子的昔时好友失踪的消息,不知先生可否详细描述一番你口中的糟心儿子的形象?”
老头儿想了想,比划道:“那小子应该比公子你稍矮一些,面目清秀,一双眼睛极为明亮,整个人透着股书卷气,具体的老朱我形容不上来,再说躺在床榻都快来俩年了,在精神的人可不都被折磨得如霜打的茄子,病怏怏的。”
百里阳波若有所思,看了眼窗外的落日,道:“据老先生所述,你口中的糟心儿子八成便是俩年前失踪的慕家二爷,想必先生也有耳闻,我与其是从小到大的至交好友,不知我们能否一同前往祁连山脉,将其接回来?”
朱敬福盯着百里阳波,纳闷道:“可以是可以,但怎么也得通知慕府一声吧?”
百里阳波灿烂一笑,站起身道:“先生误会了,这里的我们自然包括慕家之人,稍后我自会派人与慕府知会一声,如此大的事儿,很有可能便是慕家嫡长子随我们一同前往,或许慕老爷子都会亲自跑一趟,到时有劳先生带路了。”
他对着老人一揖到底,自对方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抚仙楼,他就心生警惕,这莫不是个陷阱?加上与老人的交谈,对方的回答可谓滴水不漏,这让他防范更甚,最后故意露了个破绽,没想到对方居然也注意到了,是心思缜密还是确实这般想?
朱敬福忙不迭起身,搀扶起百里阳波,“如此也好,到时候公子准备好知会我一声,老朱我就住在檀槐街的入浮屠酒楼。”
“轮到公子试考了。”
恰在此时,轻轻的叩门声响起,崔代谢如磨盘沙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百里阳波道了声知道了,打开木门,对着崔代谢道:“崔老,这位先生与我一见如故,烦请你将其送回入浮屠酒楼,好生照料。”
“待我将这酒葫芦装满再走。”老人取下青色葫芦,对着二人摇了摇,就自顾自装起酒来。
百里阳波与崔代谢对视一眼,这位南方公认的纨绔又对着角落里的伙计交代道:“宋小哥,我们走后,劳烦你将酒窖整理一番,喝掉的酒算在我头上,稍后自有人将银钱送至抚仙楼。”
酒楼伙计俯身应了一声,心下有些窃喜,百里家的二爷竟记得自己姓宋,莫不是可以凭此‘香火情’在抚仙楼捞个总管的位置?
老人将酒葫芦装满,装得不是那剑南烧、竹叶青,而是那辣人舌尖的黄酒。喝来喝去,还是原来的味道够劲儿。
三人朝着院外走去,那姓宋的乡下伙计则转身进了酒窖;出了院子,百里阳波一摸腰间,歉意道:“看我这毛躁性子,竟将合欢扇忘在酒窖里了,先生在此稍等片刻,我去去就回。”
从始至终未将后背示人的朱敬福面色平静的道了声无妨,可没有谁看到他瞬间攥紧拳头,手背青筋暴起。
渐下的夕阳,将繁盛的金陵渲染得越发美轮美奂,而有些人没有欣赏的兴致,至于另一些人,恐怕连明日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老人忽然明白了那帝狮之子为何做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了,这样的人,的确让人生恨啊。
这场套路与反套路究竟鹿死谁手?他开始有些期待数日前与少年的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