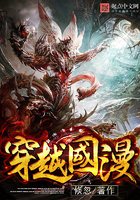清晨的阳光是只柔顺的猫,挠得人皮肤发痒,苏紫阳用手搔搔腮帮子,抱着被子呼呼大睡,口水顺着嘴角淌出。而苏青阳已捯饬好衣装,偷偷地潜入哥哥的房中,他虽然在人前尽显儒雅的气质,但内心还有顽劣的本性,他将哥哥脚绑在床柱之上,点起一把鞭炮,扔在床边,噼里啪啦的声响吓醒了苏紫阳,苏紫阳大呼一声道:“谁?”便立即抄起宝剑,准备下床追去,不料却被绳子绊住了脚,跌了个狗吃屎。苏青阳在一旁捧腹大笑,苏哥哥拍拍身上的灰尘,苦笑两下。捉弄人确是一件快事,因为生活就像一泡无聊的goushi,踩上去就令人抓狂,只有把自己的快乐会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才勉强能够残喘。
苏紫阳的气不打一处来,怒道:“你这坏小子,没个正经,昨天在别人面前装得人五人六,今天就戏弄哥哥,看我怎么收拾你。”两人打作一团,苏明云恰好路过门口,看到兄弟俩扭作一团,便制止道:“你俩别闹了,我先出去办点事,你们初来长安,没事就出去转转,好长长见识。”说罢,苏明云转身离去,两人松开对方,各自去整理衣装,然后又勾肩搭背地上街溜达,街上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有人卖烧饼夹肉,有人耍着戏法,有人卖文玩字画。卖肉夹馍招呼道:“两位不尝尝我们的肉夹馍吗?我们可是选用上好的硬肋骨,熬制成的腊汁,再浇到用谷物发酵的白馍馍上,那是一个香”。苏紫阳如豺狼般的盯着腊肉,而后用袖口擦擦嘴角,戳了戳弟弟,乞求道:“我没带银子,请我吃个馍呗?”苏青阳捧着旁边摊位的竹书,道:“我也没带银子,自己想办法。”苏紫阳眼冒绿光,手已经按捺不住,抓到了馍上,卖馍者用肩上的抹布扫开苏紫阳的手,凶道:“没银子就别拿脏手乱碰,想挣钱到前面打擂去。”卖馍者指向圆形擂台,苏紫阳顺指望去,只见它由木桩垒成,四个彪形大汉站在四个角落击鼓而鸣,周围的观众把擂台围得水泄不通。擂台上,两个人正在比试,一个男子光着头,袒露上身,生得虎背熊腰,他手持双斧,不断地碰撞两斧,弄得砰砰响。另一个男子细皮嫩肉,衣冠楚楚,看着有些手无缚鸡之力,他拿的兵器也有些奇特,是一杆玉笔。押注榜上毫无疑问是一边倒,赔率竟然达到了50比1,只有几个玩命的赌徒把老底压在了那玉面书生的身上。
两人挤进人群中,苏青阳拍了拍前面男子的肩膀,问道:“大哥,为何这赔率如此的悬殊?”男子白了他们一眼,“这都不知道,一看就是外乡来的吧!这擂台已经摆了半把个月了,持双斧的是青州的南天臧,曾是胶东王手下的一员大将,不过因行为不检点而触犯了军法,还好胶东王念其军功累累,只是劝离了他,他如今未尝一败,大家自然压他,你们要想捞点银子,也赶紧下注吧。”苏青阳道了一声谢,转身问苏紫阳道:“哥哥,你怎么看?”
苏紫阳得意地说:“论别的你在行,可说起这武学,你就不如我咯,我听说云台山有七位隐士,都是特立独行的神人,只是不满于朝局昏暗而不愿出来为官,其中有一人擅使一杆玉笔,名叫阮灵韵,人称玉面书生。你看这个人虽然面相柔弱,但腿边生风,脚底稳如泰山,他很可能就是本尊。”正在这时,赔率一下上升到30比1。
苏青阳赶紧向庄家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庄家不厌其烦地说:“茶楼上有两位客官在这个小白脸身上下了重注,具体情况你自己去问吧。”
苏青阳转动着眼珠,有条不紊地说:“哥哥,我看这茶楼上的人眼光不俗,我们不妨前去认识一下。”苏紫阳挽了一下袖口,“能和我有一样眼光的人不多,看看也行。”兄弟二人拾梯而上,来到茶楼的二层,只见两名男子坐在露天看台的桌边,一个长相粗犷,穿着粗衣,露出孔武有力的臂膀,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另一个长相文弱,面若粉桃,眼如明珠,甚是俊俏。
苏紫阳拱手问道:“可是两位在玉面书生上一掷千金?”稍长的男子爽朗地答道:“没错,正是在下。”苏青阳说:“可否请前辈赐教大名?”稍长的男子客气地说:“赐教不敢当,我名叫刘枫衍,来自南阳郡,这是我弟弟刘元秀。”
苏紫阳莞尔道:“真是巧了,我们兄弟也是初来长安,不知两位前来,有何要事?”
刘枫衍摆摆手,道:“要事倒是没有,就是送这孩子来太学读书,长长见识。”他摸摸刘元秀的头。
苏青阳冲着刘元秀笑道:“你看起来和我年纪相近,不知平时都喜欢什么?”
刘元秀稳稳地说:“我都二十多了,应该比你大一些。平时在南阳放放牛,也识些字,一直在读《尚书》和《管子》”。苏青阳瞪大了眼睛,“这两本书都是奇书,能通略的人必然是当世的豪杰,今天有幸见到你,不知可否与你结拜成兄弟?”
刘枫衍大笑道:“还有人看上我家这小娃子了,今天是缘分到了,我看你俩就拜个把子吧。”
刘元秀腼腆地说:“我才疏学浅,承蒙贤弟抬爱,我在此先饮一碗”,刘元秀端起大碗,一口气就喝完了,苏青阳赞叹道:“大哥好豪迈,我陪你一起喝,”苏青阳咕噜噜地干完了一碗,“我们先看比试的结果把。”众人向台下望去。
南天臧抬起右手,一斧子向左劈去,阮灵韵双手后背,右脚稍微后撤,他的衣角飘起,轻松得躲过了。然后,他用小腿踢到南天臧的手腕,只听咔嚓一声,南天忍痛收回斧子,怒目相视,继而扔出一柄斧子,斧子在空中划去,阮灵韵不慌不忙,用双手撑地,两脚接住斧头再砸到大鼓之上。他拿起玉笔,在隔着擂台的一段距离上,用内力写出“止”字,只见木板瞬间崩裂,映衬出相同的字,南天臧大惊,后退两步,此时他已经意识到玉面书生绝非等闲之辈,但现在认输下台岂不是颜面大损,想到这,他硬着头皮,挥舞着斧子迎面扑上,可是脚步已经凌乱不堪,阮灵韵使出一招‘钻心笔’,玉笔在空中自旋,攻向南天臧的腹部,只见南天臧被击飞到数米开外,嘴角也流出了鲜血。
南天臧喘息道:“多谢手下留情”,阮灵韵拱手谢过。苏紫阳看得津津有味,佩服地说:“不愧是云台七隐士的头儿,就是不一般。”
刘枫衍琢磨道:“阮灵韵驾临长安,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苏紫阳好不容易逮着比试的机会,有点压抑不住自己的欲望,他右手紧紧地握住酒杯,登时青筋绷起,只听啪的一声,他握碎了酒杯,然后腾空而起,越过围栏,飞到擂台之上。
苏紫阳微微鞠躬,兴高采烈道:“机会实在难得,请恕晚辈无理,想上来讨教几招。”阮灵韵摸摸下巴,客气道:“年轻人就是一副牛脾气,只知猛劲往前冲,既然你那么想讨教几招,我们不妨就比划比划,让彼此都有所提高。”语毕,苏紫阳拔出宝剑,用娴熟的轻功飞至大鼓之上,然后将剑身后摆,他一左一右挥舞两下长剑,只见两道剑气嗖地飞出,恰好击中了阮灵韵两侧的鼓面,那鼓面当即震破,发出咚咚两声巨响。台下顿时起了一阵叫好声,苏紫阳得意地笑了笑,然后使尽内力,用手掌将长剑顶飞,那剑尖直刺阮灵韵的心窝,苏紫阳跟着剑气扑出,如同一只捉鸡的雄鹰,想将阮灵韵衔在口中。
刘枫衍惊愕于苏紫阳的剑法,诧异地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这招是太室山的‘峻极绝顶’”,他转过头问道:“你哥哥师从于太室山?”
苏青阳轻描淡写地答道:“这倒没有,不过我哥哥曾跟嵩山派的元重掌门学过一些剑法,他对武学相当痴迷,恨不得梦游时都在比划招式。”
阮灵韵显然意识到对手有些实力,他两个脚尖轻点地面,向后撤去五步,苏紫阳以剑尖戳地,顷刻回旋起身。阮灵韵惬意地说:“好剑法,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能学会这么难的招式,要是再多调理内息,前途不可限量。看来我也得使出看家的本领,好好领教一下你的剑法勒。”阮灵韵提起笔,用双脚在地上画八字,向前迈去,速度越来越快,如同移形幻影,在苏紫阳的周围出现了无数的分身。苏紫阳额头渗出一些汗,他嘴里默念道:“这不是‘子虚八路’嘛!”原来这是阮灵韵研习《子虚赋》而总结的笔法,是阮式的三门绝学之一,威力好生了得。阮灵韵不给苏紫阳喘息之机,接着念道:“再吃我一招‘笔下生风’,”那玉笔突然击中苏紫阳的脚踝,使得他身体后倾,向下倒去。苏紫阳赶紧用左手撑地,哪知下一招‘玉面判官’已经袭来,顺着他的脸直劈而下,他用剑反手挡住,但无法招架阮灵韵的力量,只听‘砰’的一声,手边的木板全部破碎,笔尖已刺到他的喉咙边,阮灵韵顿了一会,伸手拉起了他。
苏紫阳嘟着嘴,不服气地说:“前辈的功力深厚,晚辈不如,”他虽然嘴边挂着不如,但心里的鸡血止不住,他觉得早晚能打得阮灵韵落花流水,自大的心态充斥在年轻人燥热的心间,还好苏紫阳没有膨胀到太阳上,要不烧了下体,就连小蚯蚓都留不住了。苏紫阳渴望学到更多的武功,尤其是学会阮灵韵的一招半式,唯有这样,他才能用钢铁之躯保家卫国,这份理想不切实际,但终归是理想,理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理想型更是得有的,万一上了呢?苏紫阳的膝盖仿佛中了魔,偏要往地上吸,准备磕头拜师,让阮灵韵教他武功,再做他的武林春梦,可他的膝盖还未碰地,阮灵韵已用脚垫了过去,颔首而笑,道:“收徒就免了,若日后有缘相见,再打上几十回合,跟你学上一招半式。”阮灵韵句句谦辞,而后抬头看了一眼苏青阳的方向,顺着屋脊飞走了。
刘枫衍对苏青阳说:“这比试看得过瘾,紫阳小兄弟真是年少敢干呐。我们今日还有些事情,来日再会。”
苏青阳起身与刘元秀击掌为誓,叹息道:“今日能结识元秀兄,也不枉此行,如果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倾力相助。”刘元秀答道:“希望日后再见,我们兄弟能一起吟诗作画,评论天下大事,今日就此别过,来日方长。”刘枫衍兄弟先行离开茶室,苏青阳也紧随其后,下楼去找哥哥同回云来客栈。
苏青阳赞不绝口道:“我看刘元秀年纪轻轻,读的书却不简单,而且他气势不凡,谈吐稳重,日后必成大器。”苏紫阳正比划着姿势,思考用什么招式才能打败阮灵韵,哪有心情理会苏青阳喋喋不休的话,就哼了一声,反问道:“你刚才说了什么?”苏青阳拿扇子敲了一下他,没好气地说:“就知道想你那点破武学,每次都害我白费口舌。”
两人走到路口,看到客栈的门前有一顶轿子,轿子的周边镶嵌了八颗暗红的珍珠,轿子的顶部安上了紫红色的宝石,轿子的周围站着八名轿夫,他们个个目光凶狠,手不离刀柄,显然不是普通的抬轿人。
苏紫阳小声对弟弟说:“这轿子里的不是普通人,不知找爹爹有什么事。”
苏青阳诺诺应道:“是呀。”在天朝上国,数字九意味着至尊,苏青阳见轿顶悬挂了八颗宝珠,心道:“这轿里的人可真是野心勃勃呀,”他蓦地猜出这顶轿子属于爹爹的顶头上司。
苏紫阳用剑柄捅了捅弟弟,机警地说:“我们去窗外偷听一下?”苏青阳顽皮地说:“说的也是,我也好奇他们在谈论什么。”两人蹑手蹑脚地爬到屋外的行道,偷听里面的对话。
苏明云担忧地说:“自从我们的风头盖过法派后,皇上越来越不待见我们,反而愈发倚重法派,杀害了不少的儒臣和各方的名士,最近连孔大人也被抓了起来,不知法派的人在捣鼓什么阴谋。”
两兄弟向里瞄去,只见王蟒长得伟岸挺拔,器宇轩昂,眉毛粗犷,眼睛锋利,他轻声说:“树大招风,我们的势力盘根错节,皇上又怎么会纵容我们一家独大,他深谙平衡之术,就是再打击我们,也不会赶尽杀绝。倒是孔有光的事很奇怪,他不知被什么人从牢中劫走了。”
苏明云不解道:“我们的人并没有出手,是谁做的?”
王蟒面色凝重,道:“我也纳闷究竟是谁在背后使坏,听布置在牢里的眼线讲,是一个长相俊秀的人,可单凭这点线索,根本查不出什么。”
“如今大臣再斗,皇子在斗,后宫也在斗,我们走错一步,就可能满盘皆输。”
“这几个皇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得小心应付,现在暂时积蓄力量,不要和各派发生正面冲突,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在成算大的皇子身上押上全部的筹码。”说话间,苏紫阳不小心将头磕到窗户棱上,发出隆的一声,苏明云目光警觉,大呼:“是谁在外面?”
苏青阳狠狠地捏住哥哥的胳膊,略带不快地瞪着他。苏紫阳咬住牙关,沉默如金。还没等苏明云去揪出两个猴崽子,窗外就有乱箭射入。苏明云赶紧抽出铁锏,挡掉数只箭矢,不幸的是有一只未能来得及挡掉,擦伤了他的肩膀,他命令破门而入的侍卫去追刺客,可惜那帮刺客身手敏捷,早已不见踪影。苏氏兄弟周围的墙上插满了箭矢,苏青阳心有余悸地拍拍胸脯,低声道:“还好没被射中。”苏紫阳愠怒道:“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弄什么不好,要偷听。”苏明云此时睥睨着窗外,狠狠拍击桌面,愤怒地说:“这帮混蛋,大白天也敢刺杀朝廷要员,真是胆大妄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任凭他们恣意妄为了。”
王蟒点头附和,沉稳地说:“此事不可草率,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派出的杀手,现在行动还为时尚早。何况宫内宫外的情况都不稳定,我们要是走错了一步,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苏明云拍了一下大腿,生气地说:“哎呀,差点忘了这两个小兔崽子了,你俩还要在外面躲多久?”两兄弟从窗户翻进了屋,低着头,不停地抓耳挠腮。
王蟒瞄了眼两人,顿愕道:“难道这两位就是被誉为神童的苏兄的儿子?”苏明云叹叹气:“谈不上神童,神经病还差不多,每天上蹿下跳,惹是生非,差点把我气死。”苏紫阳挤挤眼睛,调皮地说道:“我那是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爹爹何时见我打弱者。”苏明云说:“顶嘴你最强,学了这么多年武功,连路边卖艺人的拳脚也接不住两三招,每天就琢磨点鸡毛蒜皮的怪招,这样能有什么气候。”
王蟒打圆场道:“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刻苦钻研,日后也会不同凡响。”
苏青阳向王蟒拱手拜礼,恭敬地说:“晚辈拜会王大人”。王蟒侧目而视,很开心别人认出他,这证明他的名气不是吹的,他的脸皮比猪皮还厚,这都得益于官场的千锤万凿,他笑意盈盈地说:“你怎么认出了我?”
苏青阳稳重道:“当世能有大人这般气度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不难猜。”他懂得官场的规矩,无论才学好不好,官职高不高,该吹的还是得吹,你把别人捧上天,别人才会把你捧上树,做只供人愚弄的猴子。
王蟒老被夸成玉皇天仙,脸皮即使厚如石板,也难免害臊,他假装对苏青阳的话充耳不闻,侧着头向苏明云说:“明日得进宫觐见太后,我看两位公子本事不小,不妨带上他们长长见识。等完事后再一同去我府上,看看我给你们备好的住所。”他心道:“两个小家伙看着有点能耐,如果能好好栽培,说不定能成为儒派的储备军,在仕途上助我一臂之力。”
苏明云感激地说:“谢王大人厚爱,”他送走王蟒出门后,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两兄弟一顿,而后驱他们回房休息。两兄弟一脸不悦地走回卧房,苏紫阳念念有词道:“不就偷听了一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苏青阳说:“别发牢骚了,明天是我们第一次进宫,太后可不是容易对付的人,我们得小心应对。”苏紫阳打个哈欠,道:“管她呐,我先睡饱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