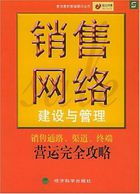西历公元2016年杭州
夜幕下的梅家坞格外的宁静,与喧闹的霓虹都市相比,这儿仿佛是另一个时空,一个平行世界下的2016年。
一辆红色法拉利缓缓行进在青山绿林怀抱间的山道上,开车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姑娘神色凝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的道路。车载收音机里正舒缓地播放着音乐,女主持柔和的声音向听众娓娓讲述一个传奇老太太的故事:“这位'伊甸园之母'最近的身体状况也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钟女士生于上世纪初,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伊甸园'创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虽然不过百年,但是所投资的项目,建立的基金、公益事业等覆盖了社会多个领域……“
车子绕过几道弯,驶入了一座江南园林式别墅。姑娘匆匆地下了车,来迎接的人向姑娘一鞠躬,便在前面带路进入一栋格局简易但不失品味的房子。来开门的一个小保姆一见到来者,便说:“老太太在楼上等着。“
几人轻轻地上了楼,只见一张黄花梨雕花木的大床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的老太太,老太太深壑的皱纹满脸的老年斑,这些都是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
姑娘鼻子一酸,凑近前去,在老太太耳边唤了声“曾祖母。“老太太并没有反应,还是闭着眼睛睡着。站在一旁的一个中年女人低头对老太太说:“奶奶,阿雪来看你了。“老太太还是没有反应。姑娘再凑近一些,略带哭腔地唤着:“曾祖母,是我,阿雪,阿雪来了。“中年女人摇了摇头,示意这个叫阿雪的姑娘暂时先别叫醒老人。
这位行色匆匆赶来的姑娘叫谢雪莉,是老太太的曾孙女,那位中年女人是她的堂姑谢舒霞。老太太全名叫钟毓秀,生于一九一一年,宁波籍人士,穷苦人家出生,因家里弟兄姊妹多,十岁时便被父母卖给了有钱人家当佣人。所幸主人一家待她不薄,教她读书识字,接受先进思想,所以年轻时也算是见过很多世面。后来主人家落魄之后,钟毓秀便嫁了人,成家后就立起了业,与丈夫一同创建了甬城饭店。八十年代初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之后甬城饭店升级成了甬城百货。八十年代末,与她一起风雨同舟的丈夫撒手人寰,钟老太因伤痛沉寂了一年,然后又将甬城百货更名为“伊甸园“,至于为什么要更名,老太太曾经说过,年轻的时候有太多的回忆,经历了太多的获得和失去,“伊甸园“这个名字寄托了她无限的向往。如今已是百来岁高龄,不是一般的高寿了。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无论多厉害的人,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一关,钟老太也不例外。
雪莉与众亲戚在楼下大厅里候着。来的这些人,雪莉并不都认得,有些甚至毫无印象。雪莉捧着一杯热水静静地靠在墙角,她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从她进门到现在,仿佛觉得自己每过一秒都是那样的艰难。
曾祖母很疼爱她,从小就把她带在身边,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安排地相当完美。雪莉的童年就像童话里的公主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曾祖母对于自己的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因此当得知曾祖母卧倒不起的消息后,雪莉一直魂不守舍,她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安排,连夜从上海驱车赶到杭州。
“老祖宗这岁数,走了也是喜丧,善始善终嘛。““如果这回真的走了,也不用太伤心,在的时候儿孙都不错,走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老太太这样子有个几天了,怕是有什么心愿还未了,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咽气。“亲戚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对于上了九十岁的老人的离去,在人们的眼里只是一种福气。人终将一死,无痛无病而终,何尝不是幸福呢?但对于雪莉来讲,她是万分地舍不下的。
堂姑下楼来,握着雪莉的手,悄悄地说:“醒了,你上楼去看看她。“雪莉听闻曾祖母醒了,便将水杯一放,三步并作两步小跑着跟堂姑上了楼。
钟老太微微地睁着无光的眼睛,也知道自己大限不过这两天。见孙女舒霞带着曾孙女进来,眼睛便看着曾孙女,但是又讲不出话来,也动弹不了。雪莉挨近她,轻轻地唤了声“曾祖母“老太太眼珠子动了一下,嘴巴也抖了一下。谢舒霞一手扶着钟老太的枕头,一手支着身子也凑近去:“奶奶,你有什么要跟阿雪说的吗?“钟老太将视线移向床对面的一口黄花梨五斗柜,雪莉便会意打开了柜门,只见里面放着几个锡罐,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舒霞问老祖母:“奶奶,你要拿什么东西?““锡……罐……“老太太努力地挤出几个音。雪莉小心翼翼地捧下一个锡罐来,打开盖子,里面也就几张当年钟老太跟她爱人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以及钟老太第一个儿子也就是雪莉的爷爷的周岁照,然后是一把金丝楠木的梳子和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式剃胡刀。难道这些就是老太太要的东西?雪莉正要把锡罐以及罐子里的东西拿给曾祖母的时候,却发现原先锡罐摆放的位子再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包着锦缎的盒子,便放下锡罐,伸手将盒子移了出来。
这是一个凤戏牡丹花纹的红漆雕花木盒,木盒不大,长二十二公分,宽十三公分,高九公分。木盒盖子上还有把黄铜小锁,锁着整个盒子。雪莉回头看了看曾祖母,曾祖母的眼神告诉她要的就是红漆雕花木盒。
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陪夜的人们大部分已经回各个屋去睡了,剩下的嫡系子孙按照规矩得守着。尽管困,但是还是得留下来,就怕冷不防老人家忽然就走了。钟老太的长孙谢谦(雪莉的爸爸),安排料理着楼下的事情,尽管亲戚们陆陆续续都回去休息了,但是几个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却怎么都不肯走,钟老太是死是活都是一个重磅新闻。谢谦胸中有恼火,但也不能发作,只能是努力地好言劝说他们离去。
正当谢谦与记者们周旋时,别墅外来了一辆黑色的别克,从别克车内下来一个年轻人。他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鞋底轻轻地碾压过那些鹅软石铺成的花纹小径,踏上了防腐木搭建的台阶,不紧不慢一步步地走向那幢小楼。
正忙于跟谢谦打发记者的管家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旁若无人地进来,便急忙撇下记者,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来者。
“先生,你找哪位?这里是私人住宅,未经允许,请不要随便进入。“
年轻人缓缓地上前一步,廊檐下的灯光刚好照清楚了他的脸。那是一张俊俏不凡的脸,白皙的皮肤、高挑的鼻梁、还有一双深棕色让人过目难忘的眼睛。“我找钟毓秀。“年轻人神情严肃地回答。
管家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不速之客,看着神情模样也不过二十来岁,却直呼了钟老太太地名讳。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叫老太太了,因为可以叫出这三个字的人都已成历史,再则老太太的名望和对社会的贡献,一般人都是尊敬着,谁敢这么无礼貌。
“先生,你是哪位?老太太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管家见那群记者送不走,却又来了一个不知名的黄毛小子,怕是来搅是非,便想推搡着叫年轻人离开。那年轻人哪会让管家近身,退了一步,抬眼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对窗户说道:“沈家的后人来看你了。“
前边的谢谦和几个记者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正当一众人困惑之时,小保姆从楼上下来,小跑着来到谢谦身边,耳语一番,谢谦又惊又喜。小保姆又对廊檐外的管家喊:“老太太说,放他上楼去,要见见他。“这一下,管家懵了,老太太传话来,那就得放行,难不成,老太太认识这个人?
年轻人整了整衣袖,默默地从管家身边经过,随着小保姆进去了。
“谢先生,您认识这个人吗?“管家问谢谦。
谢谦也一脸迷茫,望着二楼的窗户说道:“老祖宗居然能说话了……莫不是回光返照?“
二楼卧室发黄的灯光,好似煤油灯照着整个屋子的感觉。屋内只剩下钟老太和那个年轻的后生。
年轻人坐在床沿上,默默地看着老人。此时的钟老太神志清楚了许多,她笑着看着来看她的“陌生人“,泪水从她眼角处淌了下来。年轻人俯下身去,用手轻抚着老人的眼角、鬓发、耳垂,就像一位母亲在爱抚孩子一般。
“我是不是老得不像话了?“钟老太忽然开口了。
年轻人抓着老人的手,眼里噙着泪水。看着眼前这个年过百岁,干枯褶皱的人,欲想说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只是抓着手放在腮边。老人能感觉到年轻人滚烫的泪水以及来自他唇边的气息在她手背上的流连,她下意识地伸展了手指蹭了蹭那年轻的肌肤。
“老天对你真好,你还是你,那个英俊的少年。“
窗外的月光如此的皎洁,和着微风,这是个多情却又伤情的夜晚。风拨动着落地白纱窗帘,窗帘就像白色的琴键流动在窗格倒影间。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伊人已阑珊。
钟毓秀在她临死前终于见到了一个人,给她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人的出现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意料之外,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青年,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甚至跟钟老太是什么关系。只知道那天晚上他说他是沈家的后人。
沈家原是钟毓秀年轻的时候服侍的那户人家,旧时在上海富甲一方,在商界声名显赫。后来因战乱和变革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消失在新世界的曙光里。沈家到底有无后人,谁也不知道,也无从去考证。既然老人家没有拒绝这个年轻人的造访,那人们也不会去过多地怀疑是真是假。沈家已经不复存在,留给钟老太的也只是一段回忆罢了。
钟老太葬礼那天,别墅外四下无人处,雪莉将一只红漆雕花木盒给了那个自称是沈家后人的人。“曾祖母说,你知道怎样打开它。“
年轻人摸了摸黄铜锁,沉思了片刻,将一枚胸针从西服上解下来。这胸针形状奇特,是一只戴着皇冠的狮头,别针的另一边居然是做城锯齿状的金属丝圈。年轻人将金属丝圈插进锁孔,不多时只听得“咔“一声,锁居然开了。这只木盒分上下两层,上面一层有一块绒布包着一样东西,打开来是一把小巧的琉璃口琴;拿掉上格,下层有一个小锦囊袋,袋子下面压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几个字“沈燕西亲启“。
“亲爱的燕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完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很幸运能认识你们,并且能成为你们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和值得珍惜的几年。那年一别,我也不知道我们何时再能重逢。我试图找过你,但是毫无结果。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我却帮不了你。没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离去却又束手无策更难受。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它物归原主,算是为你做了点事情吧。如果有一天,当奇迹再一次降临,请一定好好把握,好好珍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
钟毓秀“
看完信,年轻人默默将信折叠好重新装进信封里。随后解开那个锦囊,这里面原来藏着一块老式怀表。怀表的盖子是七朵连成一圈的镂金百合花,表的背面刻着一张缩小迷你版世界地图,打开怀表,时针分针停在了九点二十八分。
年轻人看着怀表许久,一言不发。雪莉见此景,觉得有些奇怪,曾祖母藏在柜子里边的盒子看着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这里里外外整合起来也不会超过两千元人民币。若值钱早就藏于银行保险柜里了,遗物也将会由律师做公证。可是这盒子既然不值钱却又藏得这么隐秘,不提示也不会有人刻意去寻找,而有关于眼前这个男人,曾祖母也未曾向任何人提及过。这种种实在令人费解。
“沈先生,要不要进去喝口热茶吧。“雪莉对于这个男人的好奇心越来越重,想进一步去了解一下,谁想这位沈先生却拒绝了她的邀请。“不了,我想我该走了。“说着将东西放回盒子,拿着盒子转身离去。
“沈先生,你真的不进来喝口茶吗?“雪莉有点不死心,对着他的背影喊。年轻人止步,回头对雪莉说道:“你曾祖母是个好人,一定会去天堂的。“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雪莉有些失落,她拉了拉身上的披肩,怅然地回别墅。走着走着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飞奔至别墅的露天阳台,举目俯视,果见一辆黑色的别克开出车库,向山间公路而去。雪莉迅速拿起手机,对着即将开走的别克连按了几下快门,直至车子消失在了视线里。
“喂,易鹏吗?我是Shirley,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帮我查一辆车。''
雪莉挂下电话,凭栏看着远方,她强压着剧烈的心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有些不明白自己的举动了,为什么会对这个陌生的男人感兴趣。“不,绝对不是那样。“雪莉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她坚信对他的兴趣仅仅是因为他出现在了曾祖母弥留之际——一个谁都不曾见过的男人,曾祖母也未曾提及过的男人。
夕阳西下,公墓园中的墓碑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钟毓秀的墓就坐落在其间。在这片土地上,无论你生前多么的显赫,或者多么的不如意,所要面对的结局都一样。芸芸众生都固有一死,想逃都逃不掉。然而这个生命的法则却对一个人无可奈何。
沈燕西靠在一棵矮松上,风吹着他的风衣和丝巾乱舞,他深情地望着离自己不远的钟毓秀的墓碑,从口袋里掏出那支琉璃口琴。
《送别》的曲子飘荡在山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