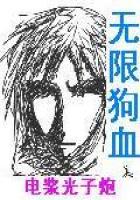阿丽探出一只脚,试了试地板的温度,真冷啊。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全年最冷的一天。阿丽觉得,这样的冬天真奇怪,和北方相比,既不下雪,也无霜冻,一降温,所有物体就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凉意。阿丽这么想着,裹上一件毛衣,下了床。脚底板触碰到水泥地,冷得她倒吸一口气。她怔怔地望向窗外,天边迷蒙一片,雾霾都吹到这里来了,她想,还是不出门吧。
外面响起鞭炮声,噼里啪啦一阵乱响,阿丽吓了一跳。她穿好衣服,站在镜子前,看自己浮肿的眼。昨天一夜没睡好,黑眼圈长上来了。她嫌恶地用手揉一揉,仿佛要揉掉一层颜色。
阿丽满嘴泡沫,一边刷牙,她想起昨天回乡路上遭遇的事故。那辆小型货车不知怎么了,停在路边,司机站在高速护栏边大声地打电话。阿丽侧躺在卧铺上,听不见他说什么,只看见他满脸愤怒,表情都扭曲了,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和谁在吵架。到现在阿丽还心有余悸。她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太过愤怒,司机本可以躲过一劫的,然而愤怒让他忘了逃开。他站在高速路边,迎着冷风打电话,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完全没想到,货车会突然爆炸。阿丽乘坐的大巴车刚开过去不远,货车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接着,响声失控了,一声接着一声。空气在震动,大巴车的玻璃窗,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狠狠地撞击,整节车厢像个闷罐子,“嗡嗡嗡”响个不停。阿丽和车上的人惊呼起来,车里小孩吓哭了。大巴司机急刹车,阿丽差点被甩出铺位,她坐直了,抓住护栏,和对铺的女孩子面面相觑。
交通陷入一片混乱,喇叭声此起彼伏,货车爆炸波及的范围如此广,整段高速路,就像一截烧焦了的木头,火光冲天,护栏被炸得变形,只是短短一瞬间,货车车厢就烧成了空壳。阿丽坐的大巴因为开出一段距离,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破坏,与后面的车流隔开了,留在了一片相对安全的区域。阿丽脸色铁青,当下第一反应是,那个打电话的司机,会不会就这样死了?她心扑扑跳,透过玻璃窗往后看,只看到一片浓烟,火山爆发一般冲上天。阿丽根本看不见什么,她隐隐觉得,货车司机现在一定躺倒在地上,在流血。一想到司机可能面目模糊,甚至头被炸飞,阿丽就一阵惶恐,说不定,大巴车如果开得慢一点,这时候,头破血流的就不只是货车司机了,整辆大巴的人,都会没命。
阿丽听到大巴司机骂了一句粗口。车里原本睡着的人都醒来了,有的在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复述事故经过,最后不忘添一句,真危险啊。
过了很久,大巴车才重新发动,驶离危险的路段。车在震动,阿丽的血液也在震动。天色渐渐暗下来,她趴在窗边,瞥见最后一抹火光消散在视线中。窗玻璃沾上阿丽哈出的气息,贴紧她的脸,凉凉的。阿丽喘了一口气,在心里默念: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阿丽回想起来,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死里逃生”。窗外有小孩在喊,刚刚的鞭炮,就是他们放的。阿丽现在对鞭炮有一种恐惧,爆炸声一响,她就心跳加速。据昨天大巴上的乘客讲,那辆小型货车,装的是烟花爆竹,一炸起来,威力凶猛。阿丽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故,总觉得爆竹烟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破坏力,那辆货车说不定是自燃,可是自燃也说不过去啊。那阵爆炸,就像她逢年过节听见的鞭炮声,只不过更集中、更响罢了。
后来阿丽就接受了那是烟花爆炸的说法。大巴车停在阿丽老家的公路边,下车时,阿丽回望一眼车厢,夜幕笼罩下,大巴车看起来像一具灵柩,吓得她赶紧走开。父亲骑着摩托车,远远朝着她驶来,一束车灯照在她惨白的脸上。
阿丽洗漱完,朝门外喊了一声,喂,你们,去其他地方放!那群小孩没有理会阿丽的警告,他们围成一圈,其中一人将鞭炮放在地上,罩一只铁罐,露出一小截引信。他们用香枝点鞭炮,香枝一头亮起红色,一靠近引信,那群孩子就跳着脚逃开了,只有负责点鞭炮的那个,慢悠悠的,为了向同伴们展示勇敢,连转身都很慢。鞭炮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炸开了,铁罐“砰”的一声跳起、落下。阿丽穿着棉拖鞋,缩起脖子跨出门槛,站到大街上,和点鞭炮的小孩对视。阿丽说,还要不要命啦?
也许阿丽故作凶狠的架势吓到他们了,他们悻悻然往其他地方走去。阿丽本想上去教训他们一番的,但天气实在冷,风很大,她被冷得浑身哆嗦,只好裹紧外套,赶紧躲屋子里去了。
阿丽躲进屋子,眼前忽地又浮现出昨天高速路上那一幕,孩子们用铁罐炸鞭炮的场景,和昨天可怕的一幕重叠到一块。阿丽脑子一片混乱,不自觉地坐在沙发上,盯着地板发呆。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见阿丽出去了又进来,便出来看,说,跑来跑去的,不要感冒了。阿丽呆呆地望着母亲,说,妈,我冷。母亲走过来,手背贴着阿丽额头,一脸疑惑,没发热啊,怎么会冷?阿丽说,妈,你说那个司机死了没?母亲说,你乱讲什么,什么死不死的。阿丽说,我昨夜没睡好,梦见他死了,好吓人。母亲见阿丽脸色惨白,坐下来,挨着阿丽,说,你肯定被吓着了,我去求道符水,给你压惊。
阿丽没来得及喊住母亲,母亲穿上外套,关上门,出去了。
她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没想到“惊吓”会产生后遗症。
昨夜回到家,一边喝粥,阿丽和父母讲起高速路上的遭遇。阿丽讲得怪吓人的,母亲一脸嫌恶地打断她,别说了,吃饱了去洗浴。父亲听完,沉思片刻,说,前几日新闻说一个制鞭炮的黑工厂爆炸,整栋楼都塌了,死了不少人。母亲瞪他一眼说,没事你关注这些做什么?父亲噎了一口,吞吞口水说,阿丽说那辆货车是装烟花的,我就想到这个。阿丽粥没吃完,搁下碗筷,说,我不吃了。母亲说,去洗浴啦,别想些有的没的。
阿丽打开行李箱,取出内衣裤,躲进浴室,痛痛快快地冲了个热水澡。雾气弥漫,浴室中水汽蓬蓬。阿丽狠狠搓洗身体,从脸,到脖子,再到大腿,恨不得将身上那股大巴车厢的特有的腐酸味清理掉。如果不是因为临近春节车票紧张,阿丽打死也不会坐卧铺,不坐卧铺,说不定就不会碰上这倒霉的爆炸。
昨夜入睡前,阿丽躲在被窝刷微博,想看看有没有关于高速路爆炸的新闻,奇怪的是,翻遍几个新闻媒体的微博,也未见相关报道。这桩事故,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阿丽分明听得耳边传来轰隆一声响,双眼眨一眨,那阵响动就没了,火光也消失了,房间重新遁入阒寂里。阿丽累得睁不开眼,黑暗中,手机屏幕的光亮照在她脸上,她揉揉酸涩的眼,竟迷迷糊糊睡着了。
母亲从外面回来,人未进门,先在抱怨。阿丽听见母亲开门,听见母亲说,哎呀廿四刚过,神上天了,求不到符水啦。阿丽在厨房里吃早饭,见母亲进来,头也不抬,说,求不到就算了,又不是真的灵。母亲一听,来气了,谁说不灵的?你小时候哪次不是靠它压惊的?阿丽搁下筷子,语气服软道,好,好,我没事了。阿丽在外头时,曾和同事聊起各自乡里习俗,同事是粤西的,她讲,粤西人也迷信,他们用柚子叶压惊。阿丽说,我们那边是石榴叶,也叫红花仙草,我被灌过好几次符水,差点噎死。两个远离了老家的人,念起各自家乡,又爱又恨。阿丽见到母亲,心想,求不到更好。
阿丽想起返乡前几日,约同事吃饭,几个人去吃猪肚鸡。阿丽一开心,就嚷着要喝酒。同事中有男有女,男的表示同意,女的摇摇头,怕喝多了不方便。阿丽说,你们不喝,我喝,反正醉了你们送我。吃猪肚鸡的小店在城中村,天冷,店家搭了个大棚,风呼呼拍在塑料布上,像鼓声,砰砰作响。阿丽倒半杯白酒,逐个敬同事,敬了男的,再敬女的。那时同事尚不知,阿丽已经辞了工。这一顿,在阿丽的计划中,类似于散伙饭。阿丽心想,过完年,我大概就不回来了。只有他们都还蒙在鼓里,以为阿丽高兴呢,要喝个痛快。男同事喝高了,搂着阿丽肩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你阿丽的事就是我的事。阿丽抹一抹泪,吸吸鼻子说,滚你妹的!饭桌上爆发出一阵大笑。阿丽喝多了,趴桌上,眼泪鼻涕一大把。她从未想过,到了真要告别时,告别会那么难。
那天晚上送阿丽回去的,是其中一个男同事。阿丽其实没醉,她清醒着呢,她趴在车窗上,半个头靠着,望向窗外。车灯一闪而过,深夜城市像个醉酒的人。男同事满嘴酒气,倚在车座上打嗝。阿丽不知为什么会允诺让男同事送她,明知他对自己有意思。阿丽想,就当作还个人情吧,喜欢便喜欢,过了这天,他想喜欢,也没机会了。男同事脑袋晃来晃去,阿丽侧过身子,推一推他肩膀,问,你喝醉了?男同事沉默片刻,不开口,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说,阿丽,我知道你辞工了,你别骗我……
阿丽惊愕,这事她只和部门主管说过,以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了,他怎么会知道?阿丽搂住自己双臂,苦笑起来,来来去去,还不是一样。车里收音机在播齐秦的歌,阿丽跟着哼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男同事说,不一样的,怎么会一样呢?
阿丽不忍再听下去,仰起头,闭上眼,一阵难过。
现在想起这件事,阿丽心底还是隐隐作痛。如果没有告别,或者说,没有人知道她离去就不再回来,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但一切毕竟不同了。阿丽习惯默默做一件事,不将心底最真实的想法讲出来,包括最亲近的人,她通常都守口如瓶,她不是善于表露情感的人,即使那晚喝了酒难受,她也只会将笑当哭。
阿丽父母其实也被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阿丽辞工了。阿丽告诉他们,公司放年假,可以在家待到年后。对他们来说,女儿回来,一如前几年她读大学放假一样,表面上并无多大差别。这是阿丽毕业后第一个寒假,从七月份入职到现在,也就是大半年而已。至于为什么辞工,阿丽自己也说不清。大概迟早要回来,所以,长痛不如短痛,辞了,无牵无挂,正好遂了母亲意愿。父母的意思,是要阿丽回乡工作,尤其是母亲,三天两头打电话,不是讲外面压力大,就是催促阿丽相个好男人。这两样事情是重中之重,它们在母亲的观念中是等同的:因为压力大,所以要嫁个好男人,说到底,都是一回事。
从小到大,母亲要阿丽向东,就不会给她任何向西的机会。母亲是个占有欲太强的人,或者说,她对阿丽的保护欲念太强了,想将女儿牢牢抓住,套牢在这个小地方,不让她跑。阿丽早习惯了母亲的强势,上大学,选专业,毕业实习,几乎都让母亲一手包办。这个过程,父亲并无发言权,他成了母亲的“帮凶”。因为这事,阿丽没少和父母起争执,好几次讲完电话,阿丽一个人待在出租屋,止不住落泪。
她时常觉得生活是个巨大的磁力场,逃不开的,终究逃不开。
吃完早饭,阿丽闲坐没事,给初中同学阿婷打电话。
阿婷初中毕业那年嫁人,如今已有了两个小孩。阿丽和她是初中同桌,那时两人关系甚好,进进出出都一起,连上个洗手间也要结伴。阿婷挺着大肚子参加中考,在当时可是件轰动的事。监考官看到大肚子的阿婷进考场,他俯下身子嘱咐阿婷,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举手。阿婷吐吐舌头说,没事的,死不了。考完试,阿丽和阿婷手挽手走出考场。阿婷问阿丽,考得不错吧?阿丽说,还好。阿婷低头,摸一摸凸起的肚子,笑着说,我是没戏了。阿婷说着,抬头看天边晚霞,那种红得淌血的艳,映得阿婷的脸也红润起来。直到现在,阿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记得阿婷说的那句话。当时她没问阿婷,“没戏”指的是考试,还是其他?
电话里阿婷的声音听起来很累。阿丽听见孩子在哭。阿婷说,没什么事过来喝茶吧。说完,匆匆挂了电话。
阿丽收拾一下,提了前几日商场买的一双雪地靴,走路去阿婷家。
阿婷老公在镇上的编织袋厂上班,这栋建在公路边的平房,是他们结婚时的新厝。阿丽每年放假都来看阿婷。印象中,阿婷老公话不多,他和阿婷的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阿婷不肯打掉孩子,阿婷老公(那时高中都没毕业)顶着压力,在乡里办了喜酒。两人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不能领证。阿丽记得,大概三年前,她和阿婷见面,阿婷刚和老公领完证回来,拿着小红本给阿丽看。阿婷叹气说,才几年啊,都老了,拍照不好看啊。阿丽仔仔细细打量阿婷道,哪里老了,还是很美啦。
一晃几年过去,阿丽和阿婷见面越来越少。有时阿丽会在心底抗拒,不跟阿婷见面。她们之间的话题,也不似以前那么多了。阿婷的世界,和阿丽越来越远。阿丽看到阿婷柴米油盐地过日子,会恐慌。她觉得,阿婷过早地耗掉了自己的生命。和她一样年纪的,大多读了大学,毕业留在外面工作,过几年才会回来。压力大归大,天地终究还是阔的,不似阿婷,一辈子注定要在这个小地方熬下去。
阿丽推开阿婷家的铁门,想到这些,一阵心酸。她其实只是比阿婷多走几步路罢了,到头来,还是一样绕回去;她没有什么资格说阿婷,到最后,她们都是一路的。
走进阿婷家门,阿丽瞥见她圆滚滚的肚子,怔了一怔。阿婷脸上掠过一阵尴尬的笑,这次是男的了。阿丽记得,因为生孩子的事,阿婷没少受罪。阿婷的公公和婆婆,死命要她生出个男丁。阿丽想,都什么年代了,养孩子成本那么高。然而在小镇上,这可是件大事,生不出男丁,就矮人一截。阿婷头两胎都是女的。大女儿读小学了,小女儿在读幼儿园。阿婷说,九月她(小女儿)也要读小学了,一个赶一个。阿丽感慨道,真快啊。她着实无法想象,年纪这么轻的阿婷,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怎么就熬到了现在这般模样?
阿婷和阿丽坐在沙发上,电视在播当地新闻。阿婷这几年确实“老”了,本是年轻女孩的模样,烫了头发,平日也无心思打扮,皮肤粗糙,乍一看,要比实际年龄大不少。阿婷的大女儿趴在一张矮凳上做作业,见到阿丽,抬起头,小声喊了句“丽姨”;小女儿大概刚哭过,眼红红的,见了人也不打招呼,坐在地板上,脸色沉沉,生闷气。阿婷大声呵斥她,怎么不叫人?阿丽拍拍阿婷的肩说,好了好了,不要吓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