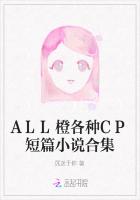季宁的老家季家庄到县城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路程的样子,但季宁要从县城回到庄子里,所用的气力和时间可不像走十几里直路那么轻松。后来季宁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在听同学和朋友们议论起中国农村到城市的距离的时候,他就常常想起他回家乡的这条悠长而令人惆怅的道路来。
出县城,是一条还算平整的约五里长的柏油路,路两旁列兵一样挺立着两排傲岸的高矮不齐的白杨。走过这一段,虽说接下来的还是柏油路,但路面就像被硫酸侵蚀过一样,凹凸不平,豆腐渣似的小石块散落得到处都是,一副想抱成团而又抱不起来的无辜模样;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塌陷,行人车辆经过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
路越往前延伸,路面越不平坦,路两边的排水渠中堆积的杂物越多,散发出的呛鼻的气味越浓烈。
等到这种气味渐渐稀薄、消散,仿佛生怕你的鼻子轻松了似的,尘灰却慢慢浓厚起来,你会蓦然发现,脚下装模作样的柏油路已经变成了一条敦实的上坡土路。比起刚才走过的那段柏油路,这条土路虽然要本色、朴实得多,但也要狭窄得多、寒酸得多、凹凸不平得多。走着走着,即使你使出吃奶的力气,也甭想骑着自行车了;农人们从路两边的高塄上赶下来的高粱秆子、玉米茬子等杂物几乎把你脚下的路填塞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还好,还能让你下脚。
小心翼翼地、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这段一不小心就会崴折脚脖子的上坡路,就到了羊头岭上,仿佛为弥补你刚才走那段路时产生的气恼心情似的,别样的一番风景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清爽的风调皮地扯扯你的衣袖,跑过了高高的山岭。在你身后,县城早已消失了踪影。岭下是一片绵延的绿色田畴,高高低低,浓淡相依,就像林风眠一幅铺展开来的山水画。往前看,是一片绵延的群山。群山中,两座山峰像昂起的狼头一样,伸长脖颈,不怀好意地盯着羊头岭。
每当走到这里,眼看家乡在望,季宁心中就像揣了只小鹿一样,一阵雀跃。他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跑下岭去,很快就踏上了一条当地人称之为“扁担路”的路。
“扁担路”,以意揣测,原先做“路”的时候,也许的确很窄,但经不住岁月和自然之河的磨砺与冲刷,路面变得越来越宽了,最后,竟然无可奈何地变作了一条宽阔的河滩。
也许因为前些天暴风雨的作用,如今的河道里,嶙峋的石头、圆圆的鹅卵石、七长八短的树根树杈等杂物比平常多出了好几倍。季宁几乎是扛着自行车走过了这条所谓的路。
走过这条路,拐上一道青石铺砌的小坡,便到了季家庄村的村口。
一座依山势而建的山门,像高峻的险道神一样突然站立在了他眼前。这座山门重檐歇山顶,琉璃脊饰,红砖碧瓦,一副历经沧桑、已经衰老了下来的神圣庄严相。
季家庄村就苦涩地掩在这座山门后面;它,牛脊形状,依山傍河,但如今既没有山的绿趣,也没有水的灵性;这些年,人们乱砍乱伐、毫无秩序地开山,早已把山体毁坏得丑陋不堪,原先山坡上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也几乎被砍伐殆尽。山上没有了树,山下的那条“厚河”也就干涸了。只有夏日里,裸露的岩石间那一簇簇茅草,还约略透出几分生动。
但现在,就连这几分生动都看不见了。
大山对人们肆无忌惮的破坏,终于起了报复之心。从山腰上冲下来的泥石流,冲进村子,不仅冲过街道,而且撞倒围墙,毫不客气地侵占了一些人家的院坝。村头那株三人合抱的老柏树竟然也躺倒了,正倒在季家祠堂的山墙上,裂痕斑斑的山墙气喘吁吁地力挺着,总算没被压趴下,但墙檐上的兽头却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厚河的河道,就像猪八戒用巨耙耙过一样,条条深痕,遍体鳞伤。越过河道,走进村子,只见村巷旁的那些杨树、槐树、椿树,有的弯下了腰,有的侧歪着身子,有的缺枝断条,总之,没有一棵如往昔般精神抖擞、直挺挺站立的样子。
季宁怀着恐惧,沿着被清理出来的巷道,推着自行车急惶惶朝家里走。
“宁宁回来了!”迎面碰上的几个乡亲异常亲热地同他打招呼。
“回来了!”季宁随口应声道。
尽管乡亲们跟他打招呼时的表情很自然,但季宁总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像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加快脚步往家赶。自行车哐当哐当地发出很大的声响。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一条在路边寻食的大黄狗,面目狰狞地朝他吠了几声,忽然醒悟到是熟人,低下头舔着舌头惭愧地哼哼了两声,摇头摆尾地跑远了。季宁认出这是邻居季瑞泰家的狗。果然,一转眼,季瑞泰拉着满满一平板车泥沙从院子里出来了,看见季宁,他停住脚步。
“孩子,你回来了?”
“大伯好!”季宁招呼道。
“孩子,你等等,大伯有话跟你说!”老头把胳膊肘靠在车辕上,苍黄的脸庞上现出痛苦的表情,迟迟疑疑地说,“孩子,你爸……好孩子,大伯告诉你,你可别着急啊!……”
季宁停下自行车,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爸怎么了?……”
“你爸……你爸的腿……”
“我爸的腿怎么了?!快说呀!大伯!”
季宁盯着瑞泰的脸庞,急得直跺脚。
“你爸……嗐……前些天下暴雨,咱村发生了泥石流,你爸在抢险的时候,被山坡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伤了腿……现在正在乡卫生院治疗呢!不过,别担心,医生说了,不碍事,躺几天就好了!……昨天,我还去看过你爸呢……”
季宁直觉得头发晕,心跳加快。
他推起自行车就往家跑,拐过街角,只见他家的街门大开着,一扇涂满泥浆的门板躺在地上;院子里,满是沙砾和断裂的树枝杈;一段墙垣倒塌了,把墙前的一只大缸砸得粉碎。
季宁惶惶地叫了几声“爸妈”,没有人应声;当他看到房门上挂着的铁锁时,才想起季瑞泰才刚对他说过的话。
季宁浑身起了一阵颤栗;他撂下自行车,就往街门外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