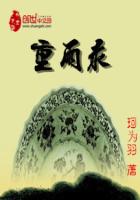九州大陆分九州,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
在中州与火州的交界处,有一小村,叫罗庄。罗庄内,大都姓罗,同属一个宗族。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是外来户,他姓。
新历一千四百一十三年。大旱。民不聊生。
自入夏以来,已经连着将近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庄稼人一个个愁容满面的盯着整日里晴空万里的老天,连哭都怕浪费了水。
罗庄生家旁边的那条小溪早已经干得连溪底的淤泥都张大了嘴。旁边那个小池塘里曾经的惬意也没了,只剩下灰白的淤泥。
九月的某天,按照日子算,已经算是入秋了。可这太阳,却是一点也没温柔下来,反而比之前更加的火爆,正午的日头下,烤的人感觉皮肤都要焦了。
庄生眯着眼抬头看了看头顶的烈阳,紧了紧身上的背篓,加快了脚下的步子,往家里走。自从七年前他出生后,庄生的父亲罗清河就不再教书,而且开始酗酒。一喝醉,就闹,刚开始乡里乡亲还同情他,时间一长,同情就成了厌恶。七年下来,罗清河早已没了往昔温雅书生的形象,浑身邋遢,浑身酒气,走哪都能引来别人的指指点点。没了罗清河的夫子身份,家里的生计开始成问题。刚开始罗牛大还能干点活,可近两年,身体也渐渐不太好了,罗牛大虽然疼庄生,却也不得不让他也开始帮忙分担家里的生计。这不,今天他一大早就出门,走了好几里路,到山上去挖了点野菜回来,中午回家配粥。这会,都快正午了,也不知道爷爷是不是等得焦急了。
又走了一段,已经能看到村里的房子了。庄生步子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脚下步子又快了几分。
忽然,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男孩子迎面而来,看到他,便停住了。庄生认得他,也是村里人,乳名叫大猛子。大猛子比他小一岁,却长得比他要壮实几分。
平日里,大猛子总是带着村里其他的几个小孩,开心了欺负他一顿,不开心了揍他一顿。庄生也反抗过,往往最后的结果,会更严重。久而久之,庄生养成了看到他们,就躲远点走的习惯。
庄生看到他,一如既往地往另一边拐了个弯,准备绕远点走。这时,忽听得大猛子朝他喊:“罗妖怪,你还不赶紧回家,你爹让人给打死啦!”
庄生一懵,烈日的光芒在眼前晕了开来,一圈一圈,五彩的颜色。
“你刚才说什么?”庄生茫然地问他。
“我说你爹被人打死啦!”男孩子凑近了一点,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吼。这一回,庄生听清了。
他死了。
庄生说不出高兴,也谈不上悲伤。他无意识地抬手去摸自己右臂上的那些疤痕,新的旧的,一条条满布在上面,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撕心裂肺的故事。
庄生在原地愣了有好一会儿,才拉了拉背篓的带子,重新启步往家里走。步子不算快,也不算慢。
说他是庄生的爹,还不如说是仇人更加贴切。自庄生会走路起,大大小小的打便没少挨过,最重的一次,庄生躺在躺了半个月才下来床。那一次,罗牛大和罗清河大吵了一架,罗清河被罗牛大从家里赶了出去。从那以后,罗清河就不太回来了,村里人经常会在村中央的那颗大榕树下看到他。他就像是一个流浪汉,蜷缩在那些拱出地面的树根处,看着好像很可怜。可没人会可怜他。
庄生懂事后,隐约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事,也就明白了为何罗清河看他时,总像是有着血海深仇一般。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不介意他施加他身上的痛苦。
不知不觉已走到村口。正好看到罗牛大佝偻着身体从村里走出来,他身后跟着几个男人,手里都拿了几根一人多高的竹竿子往外走。
罗牛大先看到了庄生,站在原地,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会后,对他说到:“你先回家。锅里有粥,先吃吧!”
庄生沉默着。罗牛大背后的男人看他的目光,比往常更加的厌恶。
回到家,锅子里是一锅稀得能看到底的粥。庄生捞了一碗,放在了桌上,然后自己坐在凳子上,看着那碗已经冷了的粥,开始发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罗牛大和那几个男人回来了。他们先前手里拿着的那几根竹竿,现在成了担架,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或者说乞丐。
庄生站在堂屋门口,愣愣地看着他们将人抬进屋里,然后与罗牛大说了几句,又一个个快步离开。
屋里,就剩下了一老一小,还有一具已经冷了的尸体。
“庄生,过来给你爹磕头!”罗牛大的声音,有些冷,还有点颤抖。
庄生像是个牵线木偶,木然地进屋,走到那具已经盖上白布的尸体前,跪下,磕头。
“再磕!”罗牛大的声音很冷。
庄生不记得自己磕了几个头,因为他数到三十以后就不会数了。终于,罗牛大不再让他再磕,抬头时,他的头有些晕,跪在那里,瘦得似乎之后骨头的身子忍不住晃。
还没等他从这种眩晕中清醒过来,他就听到罗牛大在那说:“你先出去,不叫你就别进来了。”
庄生看了眼罗牛大,他脸上面无表情,眼睛也没看他。他坐在旁边的小木头椅子上,目光直愣愣地盯着那具盖了白布的尸体,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
外面依旧是热浪滚滚,庄生躲在廊檐下的阴影中,脑袋里是一片空白。
不知何时起,家里那个比以前更破的院子里的多了许多人,大多都是女人。有些已经挤进了堂屋里,有些还站在廊檐下。她们对着庄生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偶尔传到庄生耳朵里几个词语,都是什么妖孽,报应,克亲之类的词语。
庄生对有些词语的意思不太明白,但也明白大概的意思。从他记事起,这罗庄里大大小小的人,都对他不欢迎。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四岁的时候,村西边有个小姑娘,跟他比较要好。两人那时候经常在一起玩。一天小姑娘来叫他,神秘兮兮的,说是让他去她家吃好吃的。他天真的跟着去了,在这之前,除了自己家里,他从未去过别人家里。
姑娘口中的好东西,是一小杯蜂蜜,姑娘拿了根筷子,小心翼翼地沾了一点,往他舌头上放。
筷子刚沾到舌头,一根棍子也落到了身上。
小姑娘的爷爷瞪着眼睛,看他时就好像在看一只穷凶极恶的野兽,眼睛里那股拼命的意味,让那时的庄生除了恐慌之外,还有更多的委屈。
他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对待他。难道仅仅只是因为筷子尖上的那一点蜂蜜?那一次之后,姑娘再也没找他一起玩过,而他渐渐也明白了,那根棍子不是因为筷子尖上的那一点蜂蜜,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妖孽!
他是妖孽吗?
庄生伸出手来,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地端详了很多遍,又将自己身上能看到的地方都细细打量了一遍,他确认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要说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他眉心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有一个很浅很浅的纹路,但不仔细看的,并不容易发现。至今,除了他自己外,连爷爷罗牛大都不知道这个纹路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不是妖孽,可他知道,村里除了爷爷罗牛大之外,就连他自己的父亲罗清河看他,也是用看妖孽一样的眼光在看他。
尽管他小。
罗清河在三天后出殡了。听村上的人说,罗清河是在金家村喝酒的时候,被金家村的村霸给打死的。
罗清河出殡后,罗牛大就变得少言寡语起来,他经常会一个人坐在厨房土灶后面的那个矮条凳上,抽着他那已经戒了有些年的旱烟杆子,啪嗒啪嗒地吸着。
他对庄生也冷漠起来,经常一天也难得跟他说一句话。很多时候,庄生喊他,他都像是没听到一样,或者冷漠的瞧他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
他的沉默,和看他时那种冷漠,让庄生感觉很受伤。
很快,夏天过去,一转眼,就入了冬。没多久,这鹅毛大雪便随着凛冽的西北风呼啸而来,一夜之间,就将整个罗庄变成了冰雪之地。庄生家堂屋旁边的小屋子被雪压塌了一个角,风呜呜地往里面吹,本就不怎么御寒的屋子瞬间就变得跟个冰窟窿一样。
罗牛大病了。
村长罗大家知道了,让他儿子过来将罗牛大背到自己家去了,临走前,他恶狠狠地朝着庄生说:“你爷爷是我们罗家人,你不是!你别跟过来!我们家不欢迎你这个妖孽!”
庄生停住跟着走的脚步,看着他背着罗牛大出了门走远。
雪下得更大,晚上风刮得呜呜响时,这堂屋的柱子也跟着嘎吱嘎吱地响。庄生躺在床上,听着这声音,倒也没觉得害怕。
或许,就这么被压死了,也挺好。
他没被压死,罗牛大的病也好了。
开春,每年的十五,村里会祭祖。往年生的没入族谱的孩子,会在这一天写进族谱。那一天,罗牛大要祖祠。祖祠就在村的最北面。
罗牛大大病刚愈,身体虚。出门前,叫上了庄生帮忙搬东西。一路过去,庄生出了一身的汗,身上那件已经短了不止一寸的薄棉袄几乎都湿透了。
眼见着,就到了祖祠门口。庄生还没来得及松口气,突然一声呵斥传了过来:“谁让你过来的!”
说话的是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叫罗长庚。庄生还没来得及解释,长得人高马大的罗长庚手里那根用来挑东西的扁担就甩了过来,一下就砸在了他的背上。他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张薄纸片一样,顿时就踉跄着往前飘去,然后砸在地上,手里抱着的那个竹篓子滚到了一旁,里面的那些贡品撒了满地。
罗长庚一下得手却还不罢休,上前一步,操着那根扁担发了疯一样往庄生背上腿上打,那呲牙咧嘴的模样,仿佛庄生是他的杀父仇人。他边打边骂:“我打死你个妖孽!害人精!还敢到宗祠来!你还想害死我们全村人是不是!”
罗牛大站在不远处,神情复杂地看着这一幕,双脚像是生了根一样,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