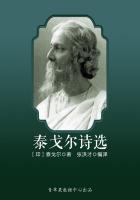2002年,我读了几本书,霍金的和牛顿的。我无意告诉你我“博览群书”,因为这不时尚不时髦,相反是不识时务。而且实话实说,我懒于读书,要读,也只读感兴趣的,不仅不会过目成诵,相反用不了多久便忘得精光。我读霍金和牛顿的目的,是试图了解“宇宙起源”和“第一推动力”的问题。很遗憾,终于没有找到,或者是我自己没弄明白。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愚钝,学力不够,相关知识贫乏。客观上也怪他们没能把那些东西表述得像1+1=2那样清晰。我于是想,也许根本就找不到把宇宙人生表述得清晰如“1+1”般的著作吧?2002年,我已经40岁了,应该是把人生过掉一半了吧?我承认我也曾挥霍浪费了一些时光。通常的说法是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任务过没过半,我找不到标准的参照系,因而无法评估。但是,某种无端的紧迫感总在催促我,从人类知识和生命自身的体会中去找一个悬而未决的答案。这个寻找又不可避免地同那个神秘夜晚相糅合。
多年以来,被我送到西山来的亲人、朋友,已经好多位了,其中还有相当年轻的。于沉重于肃穆之中,朋友们都会忍不住叹息一下:“人真是没意思,迟早都是这么个结局。”
那一刻确实思绪良多,确实也似乎能“放得下”,确实似乎“顿悟”,甚至希望从此做个纯粹的人。但是,很快,又会忘掉这儿的一切,继续去拼杀、搏击,干些灰暗的甚至不光明的营生。
我常会想,我的寻找答案,我的压抑与低调,与单向流动的时间,与这些经历一定有着联系。“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犹豫着,是因为他要寻找高贵的活法,我却更信奉“宁在世上挨,不在土中埋”的通俗论调。因此,那个无奈的无可更改的结局,使我看到了人生的软弱,进而也是生命的软弱,并不得不选择低调。
如果我要说“西山永恒”,也请你别笑这个幼稚的口号。想想,100年后,西山应该还在,而我们早已扬尘空中,进而尘埃落定于虚空。但是,还会有上山锻炼的人,经过露水潮湿的草径。太阳照样升起,丧钟为谁而鸣!不是有人建议把这些坟把这个火葬场迁走吗?这是个好主意吗?是的,都迁走了,眼不见为净。应该是搬掉了我们眼中的死亡吧,但是,谁知道呢,你走在西山上时,你走在树木丛生、杂树生花的幽静山径时,你的心一定会想到那些旧日的坟茔,想到它们昔日高低错杂、层出不穷的身影。它们的影子、它们的压抑无处不在,恰如死亡作为匿名的权威无处不在。
而假如我只是一只蝴蝶,现在我在梦中成为一个人,写这篇关于西山的略显沉重的文字。梦醒时分,我仍旧翻飞于西山小径的灌木丛中,追寻伴侣,何等从容。然后,我再入梦,为人,循环往复。这难道不是大智慧吗?它比孜孜以求、不得其解的生死苦思高明多少?
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为人之时,面对西山,面对形而下的高低错杂的坟茔,我必须作形而上的思考。从来不思考的人生何其苍白!我不能辜负当前。倘若再度化蝶,我想起上个梦中未曾思考人生与生死,会为这个大梦的虚掷而后悔。
这样看来,做一个大梦,思一个形而上,西山也不算太沉重吧?
立春
雷声——那令人振奋的“春雷”,不一定会在这一天听到,更不太可能在日历标注的这一个时刻听到。“立舂”会在日历上标有几时几分,我农民的父亲每年都会看上一看,他说:“睡着的春天和醒来的春天不一样。”他的意思是,立春这个时刻是在大白天还是在人们理当睡觉的时候出现,会对全年的收成产生影响。
其后,那些天气晴朗的上午,我村子的小河里会有许多的婶子、嫂子或者姐妹们来到,在闪着阳光的河水里,洗衣洗菜,清冽的河水流过她们的手、有些泛红的小臂,她们的笑声会流淌在蓝色的天空之下,和这河水的流动一样,清澈而欢快。
沿着河岸,会有一些孩子们,嬉笑追逐,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身形与声音,就像是从冬天、从弥漫的风雪地里刚刚飞来的小鸟。
牛在我们的村庄,高亢地叫,它们一定是听到了青草萌发的声音,动物们有着超常的能力,“春江水暖鸭先知”,那可不一定是用浸在水中的蹼与喙感知的。
那些在田埂上长出的“地心菜”,青色的或是略显暗红色的叶片,呈放射状,像开放的菊花形状,叶片上毛茸茸的,在潮湿的田埂边,到处都是。
我对它如此熟悉,是因为少年时代,几乎每年春天都要挖很多地心菜作为猪食。现在的餐桌上,人们用它作价格不菲的一道菜,是想用来“糟”掉肚子和肠子里多余的脂肪。
它的学名叫荠菜。
还有一种草值得说说,叫“小鸡草”(嗨,我可不知道它的学名)。
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是嫩嫩的几片叶,与漫地丛生的野草并无区别,只不过,它一般不长在田埂地头,它长在没有撒花草(紫云英)的田里,成片地长着,待到春渐深的时候,它会显出自己作为“小鸡草”的与众不同来一它会长出一支嫩嫩的穗,像小米的穗一样。但它始终都是谦卑的植物,贴地而生,不会超出三寸来高。待家里的小鸡出壳数日,妈妈会让我到田里割来些“小鸡草”,洗洗,切细,那些绒绒的小精灵们,在箩筐的小窝里,兴奋地叽叽叫着,争抢跟它们同名的亲切的草。它们对这种亲切的草的喜爱超过了对米粒或者饭粒的兴趣,如此说来,天生万物,皆有缘分不同。人吃的是饭粒,而小鸡却更感兴趣于这种草。当然,不仅仅是小鸡,把小鹅呀小鸭呀,放在长着这草的田里,它们也会极其兴奋地争食呢。看来这种草,是站在立春这道门檻儿上,迎接这些小鸡小鸭来到世界。
立春的时候,寒冬会数到五九六九,谚语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可以看,应该看,值得看啦,这些羞涩但坚定的眼睛,向着明媚的春天,表达着内心的喜悦和盼望,它这时候还不算是细叶呢,在等待着二月春风,那温柔美丽的剪刀,那情意脉脉的剪刀,那以天之气韵和地之气脉作为材料的剪刀。柳是这样值得人看和想的树,“吹面不寒杨柳风”,那似乎是说柳发动了春风,发动了温暧,而风中摆动的它,更引人想起种种的婀娜柔媚。这种平常的树,怎么就成了春天的表征呢,怎么就对应了曼丽腰肢呢?在古人的眼里,无论是著名如西施杨玉环,还是如一枝出水芙蓉的村姑,用柳来加以描述、暗示,都再好不过了。看来贺知章是在带着无以名状的乡近情怯之意回乡,却被相见不识的儿童问及何人何来,有了一种失落与惆怅,而后,又看到了河边熟识的柳树。那时,微风拂面亦拂着内心,老泪欲落,感叹二月春风的剪刀,时光的剪刀,剪出了柳叶,也剪去了韶华、剪出了美丽的季节,也剪去了人生中的冗余……
1990年的某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闻到了一秒特别的气味,是淡淡的香与淡淡的暧,让人着迷,也让人振奋。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了,问是不是村里种了些什么特别的植物。父亲找出了他的老花镜,翻了下日历,说,今天是立春的日子,你闻到的就是立春的气味。我说,怎么可能,立春还能有什么气味?我父亲说,天有天气,地有地气,季节有季节的气。有了这种气味,今年的收成就会好啦!
我其实也是一条快乐的小鱼
房子里住着我的父母。如今他们老啦,70多岁啦。30年前,夏天的暴雨之后,我父亲带我们在那些田埂头冲水的地方,会捉到很多鱼。现在他老啦,说话走路变慢了一个节拍,也不会带我们去抓鱼了。
我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在这水里捉那些小鱼,他把那些小洼地用沙土独立开来,弄干水,就捉到了那些小鱼。那些小鱼是不能吃的,那么小,连塞牙缝都不够。但他还是非常开心地笑。他不是为了吃鱼而笑,我知道不是。因为那个孩子就是我。接着我在这样的夏天,突然想到,如果有一个冬天,河上冰封了,结着一些薄冰,水在冰下的流淌甚至可以看到,那我一定要坐在这里看,看那些小鱼们是否还在,在冰封的水里游。我一定喝得醉醉的,在河边,等着太阳落山。天空慢慢变成冬夜里明亮闪着寒冷的星光,慢慢有点冷了,我还坐在那里。水流中有光亮泛起,醉醉的我,一定更想剖开这河中的石头,然后,用一个醉意的声音问自己:
“这些石头,是光明的事物还是黑暗的事物呢?”
注定一无所有
突然厌恶了一切的一切,厌恶了生活本身,厌恶了别人和自己的假面具。当然是从白头发开始的,它们居然明目张胆、冠冕堂皇,而那些染发剂成了骗子。体会了“两鬓斑白”的寒凉感觉,体会了悲从心起的不甘。
这就叫做——老去。上天为什么非得要一个人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清明节那天晴好,侄女穿着一件十分显眼的红色上衣,这个14岁的小女孩走在绿意初生的田野和山冈上,我眼里的这片红色幻成了对生活的判断。我想据此认为这就是青春和生命的蓬勃的意义,然后在我曾祖父的坟前,我父亲说再过几十年,到我们这代人结束的时候,我的孩子如果在外地工作,很可能就不能回来作这样的清明祭扫了。父亲是笑着说的,我却听出了其中的沉重,难怪杜牧会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算天气如此晴好,人生和世事的雨纷纷,仍旧在内心无法脱逃。我们祭扫祖先之墓的时候,已经确切知道再过若干年,我们会同样成为“祖先”。因此,杏花村到底在哪儿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杏花村所指向的酒家,一定都可以让我们微醉在清明这心底的微雨中。
母亲时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的那棵大树之下,樟树叶会落下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天光之下,眼前这片田野,或青或黄的面孔,仿佛与生倶来。我只要看一次就知道她永久的样子。她的目光是安静的,仿佛这熟悉的田园与她无关。70岁当然算不上特别的老,何况她还从事着农活与家务。我母亲的内心无比宁静,这与樟树静静的落叶无关,也与这与生倶来的田园无关。当樟树和田园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变成了她皱纹里一部分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衰老的母亲满头白发也应该是与生倶来的。换言之,我已经有意地忽略了母亲的许多经历,而确认了眼前这个衰老的满头白发的母亲,年轻时中年时的母亲的容颜已经被岁月之风刮走,或是只被留在岁月之河的某一段了,河水早已流逝或者溢出。若干年前我的小妹病重,我母亲就是以这样的姿势和眼神守候的,当小妹走出众人内心业已确认的绝望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是奇迹,而我现在明白,一个母亲那坚定的目光与守望,其实表达着生命最深处的韧性。
一个人告诉我,我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会说几句酸话的人,百无一用的人。我居然相信他说的。这个人几乎举出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我居然会生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而放弃了忠君的义务;我竟然会不在我祖父出生之前出生而让他们为养育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吃尽苦头;我竟然会在夏天拍死蚊子,竟然不能与住在污浊的桥洞里的乞者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我也曾经相信这个人所说的——当然,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人,我的意思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在某种“集体无意识”时期可能出现的。但在某个时间段我居然会相信。
另外一个可能的事件是:有三只年轻的猴子,用了三种不同的睡姿,蹲着、半蹲着、骑在树杈上。醒来的时候,它们互相指责,互相讥笑对方睡姿丑陋愚蠢。这时有一只老猴子过来,它用柔软的声音说,不要指责不要讥笑,那是三个很好的睡姿,这并非我的经验,乃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觉得舒适的睡姿。
有一个关于“思想”的言论,认为赵本山的某些小品与“小沈阳”的搞笑与黄梅戏“打猪草”(照此理解应该包括《夫妻观灯》一类)一样,属于“没有思想”。其实这个言论中的“思想”前要加一个定语“伟大”。人性中需要某种轻快某种调侃某种并不高尚高雅的东西,但它属于“性情”一类,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天气有阴有晴也需要多云一样,而我在说过那三只猴子的事件之后再谈到这个话题,显然我认为人远比猴子聪明、明智、宽容。
我一个同事的3岁多的孩子,上了一天幼儿园后不想去,他在该去的这个早晨告诉大人说他已经把幼儿园“扔掉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显然这也属于“愿望达成”之类的梦呓。可我觉得他表达了两极中的一极,就像我们也成为祖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自己是适时地把这个世界给“扔棹了”。照此现解,尼采说“他入即地狱”也并非强调“他人”的可怕,而只是从我这一端来加以强调——就算人人都是天堂,但针对自我来说,“他人”也是地狱。
我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兵书兵法窥探黑藉黑箱,学习设计与权谋,被人算计、打击、忽略轻视蔑视,并且获得心得获得见识,自以为日渐成熟、日渐羽翼丰满,却在这样一次不经意的寒凉面前,想到清明之雨、想到母亲的安静、想到一个孩子把幼儿园扔掉。那些柔软的东西,让我感觉到了现实的冷硬如铁,而我们自以为成熟的过程就是学习这些本末倒置的人生经验,在自然的法则面前,那些小打小闹小家子气的谋略一文不值。而造化的宽容在于它从来一言不发不置可否,无论你是安静地注视着世界,还是在进行着那些小打小闹的学习。三只猴子对睡姿的争论没有像谈赵本山、“小沈阳”、黄梅戏一样被做成文化访谈,显然有失公允。头发不可逆转地渐白其实让我知道自己也正在被这个世界扔掉,只不过不是像一只被用过的易拉罐,一次性地被扔掉。不是那样的,真实的感觉应该是,一列火车正在离去,我跟在它后面跑着,原本是乘车人,现在被它落下了,它渐行渐远……总有一天,最后,成为完全被后代忘却的祖先——这一切都是注定的,结局注定是一无所有。
腊月二十四亦即2月11日
时间本身是不可记忆的。它流逝如水,行走如风,冷静如冰。你无法判断,是流水与落花、是漫散的尘埃覆盖了时间,还是时间覆盖了它们,但我知道,凄风冷雨之后那个早晨,落花遍地,残叶满目,许多伤感与痛楚刺伤我的眼睛与心灵,一些语言一些词,漫过我的心田。我其实更知道,那些伤痛来自时间本身,是时间刺痛了我,我真的可以读懂它核心内无法接近的热以及这热的四散,当我可以隐约感觉到它存在时,语言、词汇,一起痛苦无奈,心灵与痛其实没有出口,语言与词汇只能以极小的孔供它泄露,这使得出口与出口者一样痛苦。
现在,我在农历犬年的腊月二十四,也就是公历2007年2月11日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在想上面的这些话。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人类的刻度——2007,其实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笨拙的绳结。但其实又是非常重要的绳结。没有这些绳结,我们将无法在时间里留下任何一点痕迹,恰如我们可以借以泄漏的那个“语言”的出口,它总算可以记录我们脆弱的心灵、我们的一些“思考”(我想说,在人、自然、规律之间,人类的思考,那种脑细胞的化学反应其实只是一点微光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