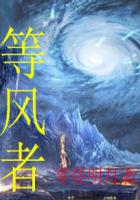几年后。可心和母亲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也不多与人交往,任凭这周围的世界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像与她们两个突然就断了关系。可心总觉得,这日子过得真慢呀,这一天天的数都数的过来,她也不觉得难熬,也不觉得兴奋,就是漫长。蕙兰却说,长什么长,这日子过得多快呀,一眨眼,这么几十年的。那么多人,一个个就离开了,你的爷爷奶奶,你梅姑,金花呀,哎呀我呀,怕是不能活着见到你父亲了。可心问,你为了一个承诺等了快一辈子,值得吗?蕙兰笑笑,开始是为了一个承诺,后来呢,是为了我自己。
“你自己?” “对,你外婆和你外公,住在一个屋里,可他们的心离的很远很远,我和你父亲,一直分离着,可我觉得,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从小就下决心不要像你外婆那样过一生,所以,我等你父亲,一辈子,也是愿意的,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懂,我只觉得相爱的人就该在一起,分分秒秒都是美妙的,要是分开了,就只能把它当作回忆,母亲应该去找寻下一个相爱的人,这么多年杳无音尘,您却还只是在原地徘徊等待,不值得。” 蕙兰不置可否: “也许你永远都不会懂得我和你父亲之间的感情,就像我不明白你对那个姑娘。”仿佛意识到自己碰了禁忌,惠兰突然闭口不言了。
可心沉默了,她从来也没有向卿衣明明白白表达过自己的情感,连她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无法自拔的纠葛中,回想起来,让她真正愤怒的人不是易升,不是卿衣,而是她自己。她放纵的任由自己在乱七八糟的生活中不断下沉,陷入泥潭,差点连喊救命的力气也没有了。她自觉没有颜面再去见易升或是卿衣。可是一想起来,心里竟然还有些牵挂呢,文GE这么几年的浩劫,他们都还好吗?想到这里,可心脱口而出:“这么多年了,不知他们怎样了?” 蕙兰蹙了蹙眉头,叹了口气: “孩子,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现在还记得你刚出生时候那个样,小小的粉红的,我就对自己说,我要保护你,爱你一辈子。我想这个母爱,就是不管你这么做合不合情理,对还是错,我都敞开心去接受你,虽然这对我来说很难。我只能告诉你可心,如果你心里真放不下,就按你的心意去做吧!”
可心不是没有犹豫,她记得易升曾经说过,他们三人是相见不如不见,可这一次,她还真去了易家。易家和她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到处一片狼藉萧条,竟然找不出一件完好的家具。几间厢房积满灰尘,好似久无人烟。院内杂草丛生,早没了从前的热闹光景。可心想着难道他们全家搬走了吗?这个屋子就这样被废弃了吗?正暗自落寞着,忽然看到墙角蜷着个人,半躺半坐地倚在门旁。脸上尽是灰尘泥垢,头发长长,遮着大半个脸,头还偶尔摇晃两下。这人的旁边还坐着个小男孩,三四岁的样子,全身上下也是脏兮兮的。可心又回过头去看那人,无奈还是看不清楚他的脸,就问他:“你是谁呀,你知道这里还有人住吗?”那人突然跳了起来,傻笑起来:“没人了没人了。”又四下张望了一会儿,紧张的说: “嘘,跑了,跑了,不能说,不能说。”又咯咯笑出声来:“他们不让我说,不让说。” 可心听了,心里咯噔一下,这才发现这人的脸庞竟然长得有几分像易升,只是瘦了很多,变了很多。她扶住他:“你是易升吗?你怎么了?你说话呀!”旁边的小男孩拉了拉她的衣角: “他是疯子,什么都不知道。”可心还不死心,摇晃着易升的身体: “你说话呀,说话呀,这是怎么啦? 谁跑啦?”心里酸酸的。易升始终没能回答可心。看来,他是真的疯了。
可心和蕙兰商量了,就担起了照顾易升的责任,时常往返于两家之间,也不觉得累。那个小男孩原来是个小乞丐,可心见他无父无母,就收留了他当儿子。蕙兰也高兴家里多了个孩子,还重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家望。有了家望,又要照顾易远,可心觉得责任重了,开始寻思去哪里找一份工了,日子好像也没那么漫长了。
蕙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还经常受到病痛的折磨,时常做噩梦,梦见自己的新婚之夜和他拜堂的男人突然就找不到了,可她也不记得男人的那张脸,茫茫人海中到底嫁给了谁,到哪里去找那个男人,蕙兰自己又糊涂又着急。有时候她又会梦见自己被囚禁在密室里的一个角落,可是忽然就长了两只翅膀,她使劲扇动着自己的翅膀想要飞走,发现密室里竟有一个小窗,她高兴地飞向小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开那个小窗,却发现窗外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密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陈设,她还想试着再冲破小窗,一飞到窗口,猛然发现父亲的眼睛,变得硕大无比的眼睛,正从窗外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蕙兰吓坏了,身体开始急速坠落,发现自己的翅膀也折了。蕙兰在心里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一着急醒了过来,手脚冰冷,胸口发闷,额头和后背却完全被汗水浸湿了。
有一日,可心要带家望去易家,忘了拿东西,折身回屋的时候,忽然见到母亲闭了眼,斜靠在旧椅上,想是不好了,一边摸着她的脸,一边急急地唤着母亲。蕙兰却慢慢睁开眼,笑笑:“人老了,就这一会儿就困了。”可心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把母亲扶到床上躺下,让家望自己出门。蕙兰苍老的脸上布满沟壑,可心感叹:“母亲,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您,您就已经老了。”蕙兰听了,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张相片,递给可心:“来看看我年轻的样子,老照片了,这辈子我就拍过这么一张。”可心接过,仔细端详起来:谁能想到这曾经如此姣好的面容会是今天这样写满沧桑?岁月呀还真是无情。母亲的生命里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她所寻找的美好在可心的泪水中变得支离破碎起来。蕙兰努力伸手去擦可心脸上的泪珠:“我怕是再没有机会见到你父亲了,我就想,给他在我的坟头上也立个碑,等我走了,兴许能和他在地底下又遇到了呢?”可心劝道:“您扯远啦,父亲在台湾,听说现在政策放宽了,没准哪天父亲就能回来了呢?所以呀,您也要自己保重,不然父亲来了没见到您,一定会伤心的。”惠兰听可心如此安慰,高兴地点点头。可心心里却十分明白,当年的文GE运动中确有人报告说张自成去了台湾当了叛徒,她也暗地打听过,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只能说是有人想趁机邀功,信口开河呢。蕙兰接着说: “我还有个心事,那支被抄家抄走的兰花簪,我做梦老是看到。要是能再寻回来就好了。是你外婆留给我的,好东西呀,真是可惜了。” 说着说着,老人家又觉得困了。天开始下起小雨来,滴滴答答,淅淅沥沥,让人心烦意乱。可心见母亲又睡了,便把她的照片夹到一张折起的年画里,放到床头的那个小柜中。
母亲过世的时候,可心按母亲嘱咐的,在墓碑上加刻了父亲的名字,还刻了一行铭文: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可心觉得那是对母亲一生最好的写照了。埋葬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依山傍水。可心后来也曾经找过李书记,想打听兰花簪的下落,李书记已经不是书记了,但他的嘴还像以前一样刻薄。可心什么也没打听出来。
为了家望,可心成了丝绸厂的一名女工,养蚕剥丝,靠着一份微薄的薪水养着一家。好在家望懂事乖巧,也很好学。易升还是认不出人来,常常无缘由地咧着嘴笑,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有就是卿衣。文GE期间可心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她的相片,可是,是她吗?相片里那个人,有个不一样的名字,叫林英。那篇文章是批判林英的,说是她唱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建剧,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路线。可心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只是一想到她,心就会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