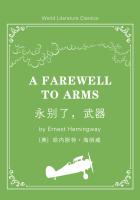若我爱你,我可以将我的骨肉、经络,和同灵魂、尊严,片片削尽,散入泥土,养出芬芳明艳的花朵,点缀在你的必经之路上。
你大可不必停留。
因我这样对你,只是我的事情。
可是后来,大约,我已不再爱你。
词人说,钿车罗帕,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
当初一个是不得不娶,一个是不得不嫁。
如今一个铁了心要离开,一个铁了心不放。
两人之间陷入漫长的争吵期。
争吵过后,便冷战。又争吵,反反复复。彼此都疲惫不堪。
杜嘉烈说,欢喜似乎是患上了产前抑郁症,又斟酌能否开药,欢喜却一把拽住他的手,语带哽咽:“杜医生,你给我开一张流产证明好不好,求你。”
他对她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灯光下看起来格外动人,像是油画里英俊的年轻天使,他用他那把像是温泉般柔软的磁性嗓音说:“欢喜,我是一名医生,做这种事是违反职业道德的。”然后站起身,准备走出办公室。
却听到身后“咚”的一声响,像是裸露的膝盖和地板碰撞的声音。
他诧异的转身,看见欢喜跪在地上,眼泪啪嗒啪嗒的往地板上砸,像是身体里装进了一个哭泣机,巨大的悲伤和痛苦为它输入充足的马力,她泪流成河。
然后,他听到她说:“于佑和对唐家做的事,你肯定也知道内情吧,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难道就是你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作为补偿,是不是也该帮我一把。”
杜嘉烈眼睛里的光唰的一下就熄灭了,仿佛被吹熄了的蜡烛。他看着欢喜冰冷的一双瞳孔,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后悔。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只是冷冰冰对峙着。
和于佑和最后一次争吵的第二天晚上,欢喜亲自下厨做饭,开了一瓶珍藏的红酒,她跟他碰杯,对他说:“我们不要再伤害彼此了好不好?”
他微笑,说:“好。”
仰头喝尽。她又给他倒了一杯。
一杯接一杯,很快那瓶酒便见底。桌上的菜倒没怎么动。
最后,于佑和趴在桌子上醉过去。
欢喜坐在他对面,坐了许久,而后起身,上楼。很快,她拖着箱子下楼,走到玄关处,停下,回头,望了他最后一眼。
再见,于冰山。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了。
再见,这些年的爱。
她觉得累,好累,真的好累。
她出门,上了那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往机场去。
可是他不放过她。
他在机场将他截住,脸色铁青。
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终究被他识破。红酒里的安眠药,早就被他换成普通的维生素。
她咬牙切齿:“于佑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离开你,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下次,哪怕死,我都要离开你!”
“唐欢喜,你也给我听清楚了,你最好死了这条心,除非我愿意,否则你永远都被别想……”
她抬头,看着眼前的于佑和。机场的灯光耀眼,把他锋利的脸庞笼罩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准备收割人灵魂的天使般头顶光环。他的目光静静地看向她,像在阅读一本书。她无法从他的眼神里读懂他在想什么,准确的说,她从来没有弄懂过他在想什么,他全身上下每一寸血管里流淌着的,都是谜。
“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别走,行么?”他语气低低的近乎哀求,他从没有哀求过谁,他曾是那样挥斥方遒的模样,此刻,他心里却像是小时候弄丢了一个玩具般的失落。
她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和他对视着,她感觉自己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都在用力,然后,是她冷漠平静却一针见血的声音:“孩子打掉了。”
——————————————————
(作者PS:嗖嗖嗖~好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