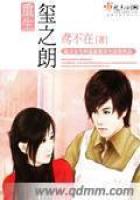之前就听底下人说过,变徵手下的人差不多和他一个德性,不光贪得无厌,且好大喜功睚眦必报,仗着有文桢撑腰更是侍宠称骄,很多人见到他们都躲得远远的。听说有一次,廉隼军中有一个城门领不小心将汤碗打翻,洒到了变徵手下人的身上,本不是多大的事,那人既没伤着也没烫着,索南却以为廉隼暗中使坏,变徵亦觉得廉隼仗着自己军功在身有些目中无人,加上索南一番挑唆,索南就在变徵的授意下硬是带了几十个人砸碎了人家的膝盖骨,廉隼见变徵的人目无军纪,在军中就敢如此放肆实在气不过,便带人前去讨要说法,结果不但说法没要成,反而被变徵反咬一口,说廉隼管教不善,变徵仗着文桢不喜欢廉隼而将他羞辱一番,廉隼一怒,告到了文桢那里,结果不难想象,文桢有心偏袒,就给了廉隼寻衅滋事的罪名,罚了他半年的军饷不说还要他向变徵道歉,廉隼骨子里就有股老将的傲气,如此被冤本就不快,还要他去道歉根本就不可能。结果变徵反过来提请文桢免了廉隼致歉,说不过是件小事,他大人不计小人过,事情到最后廉隼不仅没得到任何结果,反而让变徵得了个大人有大量的评价,廉隼一气之下在帐中病了大半个月。曾经有段时间,变徵良好的名声的确博得了不少人的夸赞,只是跟在他身边时日久了都会发现他的臭毛病,很多跟过他的人都吃了亏,要么被他算计了要么成了替罪羊,久而久之也就没什么人再愿意和他有任何牵扯了。
谁曾想我一个阴差阳错居然把他救了,当日凤凰镇屠镇之仇未报,今时今日又不能让他血溅三尺白绫来祭奠死去的亡魂,我只能一忍再忍,今天居然叫我碰到这样好的机会,是时候打压他嚣张的气焰了,又怎会轻易放过?
我直接将索南押到了文桢的帐中,这会,文桢不在。
“江将军,当初你于梁王手中救了我,我白某人一直感恩在心,眼下不过是小事一桩,回去我自会军规处置,又何必闹到二王子这。你就高抬贵手放过他,这个索南平常就有些心浮气躁,做事是毛躁了些,有些事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吧!”白付坐到我身边抿了口茶道。
“白将军此言怕是差矣,老鸨自己已经亲口说了,他索南已经打伤了她三个姑娘,足见白将军你手下的人是多么英明神武了,这样的奇将良才我们应该推荐给文桢,不是吗?先前你还说文桢手下缺人,我正好顺水推舟,给你白将军个人情,把他推荐上去,怎么说也是从你手中出来的人,你应该高兴才是!”我一阵讥讽。
“将军这么说,就是不肯卖我白某这个面子了?”白付用茶盖漂开了杯中茶叶,道:“江河,你因何故总于我作对?抢了我的凤凰镇守镇一职不说,现在又抓着我的人不放,我究竟是哪里得罪你了?”
“白将军这话江某怎么听不懂了?”我咳嗽了一声,“第一,凤凰镇不是我抢你的,是夏王封赏的,你要是有意见,大可找夏王理论,与我无关!第二,长街上的事是你手下人闹的,我不过是要按军规处置,这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啪地一声重重的摔上了茶杯盖,重的几乎要将茶杯盖碎。
“姓江的,你有种!我们走着瞧!”他丢下这么一句话后就出了帐。
我一直目送他离开,索南眼见白付不管他了就要追出去,却被我一个灰麻老老实实地捆了起来。
“公子,因这么个人和白将军闹翻,您可是占不到半点便宜的啊!”一旁的范仲忧心道,“白将军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他之所以这样跋扈就是因为有二王子撑腰,你公然和白将军叫板等于和二王子过不去,不值得啊!”
“你觉得我错了么?”我斜过头去问站在右后方的范仲。
范仲头略微低下,小声道:“没错,可是……”
“既然没错那就无需多言!”
我话音刚落,恰巧文桢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司空朔,当然还有又有些得意洋洋的白付。
看白付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就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他出帐去一定是找文桢去了,由文桢出面他自认为我一定会放人。
司空朔走过索南时,看到灰麻眼神一个定格,我忽地想起在东鹤楼的时候我也是用了相同的神术,灰麻和别的神术不太一样,每个使用者的姿态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开启的灰麻绳是两股绳子相互编交的,而别人用起灰麻就可能是环节状连接或者三股绳子,也有可能颜色有所改变。司空朔看到这个灰麻必然是想到了和我在东鹤楼使用的一样。果不其然,他抬眼望向我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尖锐的目光,似要穿破我的面具看看我的真容。鉴于所有人都在,索南也不敢跑,我一挥手,散掉了灰麻。
白付见我解了灰麻,更加的昂首挺胸了,以为我惧怕文桢才不敢对他的人有所苛待。
“这是怎么回事?”文桢问这话的时候脸虽然是朝着我的方向,但是眼睛却看着白付那边。
自然是白付回了话。
“殿下,是这样的,我方才陪同江将军去长街置办用品,却意外撞见索南和软香小筑的人起了点误会,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想着就算了,却不知江将军小题大做,硬抓着白某这个把柄不放,非要压着白某的人来见你,白某想着殿下日夜操劳军务没必要增加这些蝇头之扰了,而且这样折腾甚是影响军心,但江将军不依不饶,一定要军规处置,所以……”
这事这话从白付的嘴里出来完全变了一个味道,他的巧舌如簧让我都有些佩服他了,那些说客真应该让他去做,不然简直是埋没人才。
文桢瞟了一眼白付,白付立刻了然于心,又给索南递了个眼色。
“白将军说的是啊,属下听说最近强盗闹的凶,未防止软香小筑窝藏匪贼就进去例行查检,却不想出了点小误会,江将军就污蔑下官寻衅滋事硬是给下官抓了回来!”索南说着,满脸的委屈。
文桢看向了我,“可是这样?”
“我彷佛听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很精彩,江某人为你们主仆二人鼓掌,”我拍着巴掌,然后一掌甩在桌上,厉声道:“一个整天如地痞流寇一样走街串巷,三天两头往青楼跑的人居然能说出例行检查四个字,怎么,例行检查去青楼检查人家穿了多少肚兜吗?检查人家被你踹伤了多少个吗,检查你打烂了人家多少东西吗,检查人家店铺多大够不够你砸是吗?如果这样都可以说成是例行检查,那哪天你们一把火烧了整座军营是不是还要说只是检查军帐?”
文桢的茶杯沾着唇边,自我怒立而起的时候就没有喝下一口。
一旁的范仲更是吓的大气都不敢出,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敢在文桢面前这样疾言厉色的斥责他手下的人。
帐中静的有些可怕,每个人都心怀鬼胎不动声色的站在那,尤其是白付,时不时地望两眼文桢,然后又和索南交换眼色,这一切自没有躲过我的眼睛。
我亦要看你还能演出什么戏码来!
文桢放下手中茶杯,低眉道:“江将军何必如此动怒,你同白将军同在我深国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至于此?”文桢言语间已经有所倾斜,“今日本就是青楼小事,没必要为了几个风尘女子而伤了和气。”
“风尘女子亦是人,也是要赚钱吃饭的,倘若军中每个人都像索南这样为所欲为,等于把军规军纪视作无物,倘若一纸约束成了空头白话试问谁还会把它当一回事?”
我针锋相对毫不相让,且不论文桢日后会怎样对付我,今日之事我是绝对不会就此放过的,眼下是对付不了白付,但也得给他手下人一个教训,总得让他们知道收敛。
“白某已说了,索南只是去还银子,并未做什么出格的事,江将军不知是在哪听到的这些闲言碎语,硬是要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降到我白某手下人的身上?”
这个白付说谎丝毫不会脸红,明明是他的人有错在先,却被他硬生生说成是我故意找茬,再和他争辩下去毫无意义,只是浪费唇舌而已,我越过白付看着文桢,等他下达处置命令。
“这事到此为止,二位将军也不要置气了,钱银着索南双倍还上就是!”
白付听后蔑了我一眼,躬身谢过文桢。
我咬着牙,狠狠地握紧了拳头,积聚在心的怒气一把火烧了上来,要不是为了梁王,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待,杀了他都会脏了自己的手,看到跟在白付后面,拍着身上灰得意要走的索南,我脑袋一蒙,竖起二指欲催动神术拦住他,却被一个身影忽闪而过挡在了我的眼前。
“殿下,”司空朔礼敬道:“殿下,这次的确是索南惹事在先,若这样姑息,传出去怕事无所宜。”
我有些错愕,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一向觉得对我敌意甚大的司空朔居然会帮我说话?
文桢则多了比我更多的诧异,一脸奇怪地回头盯着他,“司空朔,你说什么?”
司空朔把刚才那番话又恭敬地重复了一边。
文桢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后,缓缓转过身,挨个扫过帐内所有人,最后将目光停留在我身上,那种眼神如锋刀般,似要将我刺到体无完肤,他沉寂了好一会,唇启道:“索南,擅自带兵出营扰乱民生,目无军纲纪律,扣三月军饷,罚五十军棍,由江将军监督,有他做例子,我看以后谁还敢再犯!”
索南听后一下瘫倒在地,白付的脸亦是一白。
其实在动手前我也是想过的,之前那番言论文桢虽没说什么,可心里终究是不快的,论身份我比他不及却还公然抵意他的决定,摆明了和他过不去,换句话说,在他心里捏死我比捏死一直蚂蚁还要简单,只是他不屑动手罢了。
至于司空朔,我却不懂他的用意,到底是真心帮我,还是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