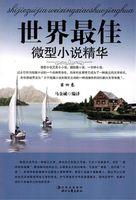郭一中的父亲郭象山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皱巴巴的。一清早他就起了床。他上完厕所,到孙子郭合华房间里看了看。可是昨晚孙子一晚没有回家。他不知道孙子近来老是不回家不知道在干什么?郭象山在心里说:不要学坏啊!但他止不住地又咳嗽起来。而且咳嗽得满脸通红。
这时他老婆董春愚也起床了。她的背更加的驼了,头几乎到了地下,背像一张弯弓,手背在背后。董春愚起床后,郭象山扛起锄头就进山了。当郭象山走在杂草丛生、杂草上积满露水的山道上,不一会,打着补丁的裤子的下节便被露水打湿了。路两边是参差不齐的茶油树和杉木。鸟儿在绿叶中跳上跳下,叽叽喳喳叫过不停。他房屋下面的左前方是郭刚的木屋,瓦屋上已经冒起了炊烟。他的屋下方是郭强的红砖楼房。郭强现在是村支书,家里自然比别人殷实。而且,简易公路也修到了他的家里。可是,郭象山的房屋还是八十年代自己被政府举为万元户的时候修的。唉。什么万元户啊?当时自己手里其实存了不到五千块钱,也是自己家里养了五、六头大公猪,每天赶着公猪进西家串东家,让公猪跟母猪配种,每一次收五元,那是赚的畜生的钱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才赚下那么些钱。结果自己修房子、郭一中结婚,花得所剩无几。渐渐地,养公猪的多了,生意就不好做了,自己的财路也就断了。可是自己也老了动不了了,孩子、媳妇出去了十多年,把孙子丢在家里,从来没看到寄一分钱回来,只有媳妇以前还偶尔来一个电话问一问孩子的情况,孩子没有钱上学,他们也不管不探。唉,我这几根老骨头入土后,孙子怎么办啊?
他走进自己的地里,地里长满了杂草,周围的地绿油油的,有豌豆、麦豌菜、马铃薯、莴笋;豌豆、麦豌菜都开着蓝白色花儿,露珠沾在绿色的叶片上晶莹透亮;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油茶树,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但他坐在锄把上咳嗽了很大一会,才站起来挖土。他挖了一会儿土,就听到从矮老倌家的别墅里传来了长长的“噼哩啪啦”的鞭炮声。而且,从别墅的方向升起了一缕漫长的黑烟。他想:一定是矮老倌过世了!矮老倌已经病了有半年多,他的儿子,现在的市委书记郭玉红带着他到处治病:省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但无论你郭玉红怎么有钱,无论带矮老倌到什么样的高级医院,治得好病治不了命。得了癌症没有哪个能够治好了的。何况他已经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了,阎王都等得不耐烦了。
想到矮老倌,郭象山心里不自然地生出许多感叹。想:为什么矮老倌的命运就那么好?儿子那么孝顺,那么有出息。他当年最看不起的是矮老倌,觉得他傻乎乎的,无论队里吃什么东西,矮老倌从来不去跟别人抢,他总是在后面慢腾腾的,有一点就吃了,没有就算了。而且,有女人和孩子的时候,他总要把自己的那一份分给他们。他的老婆俞瑞芳长得那么高大漂亮,可是,把自己的老公看得宝一样。每次出门总是走在老公后面哈哈大笑地对羡慕她的人说:
“今天我和我老公矮老倌走亲戚去呢。”好像世界上就只有她有一个老公。有垂涎她的人跟她开玩笑,想得她的便宜,她都会讥笑别人,拿她老公来说事:
“你长你高不是空高的?吃饭比我老公吃得多,穿衣比我老公要多那么多布,做事笨手笨脚没有我老公手脚快。你哪一点比得过我老公矮老倌呢?”而且,俞瑞芳比别人就是有远见。她家里非常穷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都不送书,都把他们箍到队里做工。可是她把她的儿子送学校读书,而且一直送完高中直到参加工作。矮老倌是哪里修来的福啊?
太阳突破云雾,将明媚的阳光潵向大地。不一会,大地蒸腾起氤氲雾气。气温也在不断上升。清早有些寒气逼人的气温,开始暖和起来。郭象山挖一会土,咳嗽一会。但到底感觉得肚子饿了,他到油茶树林里捡了一把柴火,背在背后,扛了锄头回家吃饭。
家里弯弓老婆董春愚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桌子上又是一大碗没有油的腌菜。孙子郭合华还是没有回来。她老婆念叨着:
“这孩子又做什么去了?两天没有回来了,千万要学好啊!唉,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孽啊,一个个都不听话。大的在外面出去了十多年没有回来过一分钱。这一个又别学坏啊!”说着,她用衣袖擦了一把鼻涕和眼里流出的泪。她的眼里含着眼屎,好像老是睁不开一样。而且鼻孔里老是煮粥一样响过不停。头上花白稀桸的头发也在头上纠结起来了。她从黑黑的碗柜里拿出一只黑黑的碗盛满饭开始大口大口地吃,吃声很响。郭象山越来越心痛他的女人了,他觉得自己的女人这个样子,都是因为生活的重压使她变成这样。是啊,年轻时候不懂事,在外面受了气总是回家拿她出气,动不动就打。其实,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无论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或许是默默地流泪,或许寻找事情做来化解心中的痛苦。她十七岁就跟了自己,她没有生育,后来捡养了郭一中,她便当宝一样捧着、护着。风风雨雨几十年,可她到底得到了什么?
当老婆吃完一碗饭,他立马接过她的碗给她添了一碗。外面的爆竹在不断地响着。哀乐声也在耳边悠悠扬扬在飘荡。郭象山对着董春愚自言自语地说:
“矮老倌死了,我也要去探一探。唉,肯定他们家里要办丧事的,别人家都去,我们也要去啊,可是这礼钱到哪里去想方啊?我们家做什么事,他们都是来了的啊。”
董春愚默默地吃着饭,因为,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操过心。郭象山吃过饭,便从家里走了出来,向矮老倌家里走去。
非常气派的别墅大门前两边摆着两尊大石狮子,大石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对着所有来来去去的人们。开阔的堂屋里摆着一副黑漆油亮的大棺材,披麻戴孝的一大群孝子们站在棺材的一边,对所有来探望死者的人跪跪拜拜;矮老倌的女儿在大声喉哭,诉说着矮老倌的苦难经历。孙辈们听了姑姑的哭诉,也在嘤嘤缀泣;两个点鞭炮的用一辆面包车拉了一车爆竹放在水泥地坪上,不停地放着,黑烟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淡淡的在天空飘荡。矮老倌的尸体就摆在大棺材旁边地下的棉被上,头用薄皮纸盖着。金刚们在往棺材里倒灰、扎皮纸。看来矮老倌马上就要入棺了。很快,矮老倌的尸体就被金刚们抬进了棺材里。郭象山笔直走到矮老倌扎着松柏和百花的、棺材前面的祭桌旁,并没有顾及跪地迎接他的郭玉红和孝子们,他从放香的铁筒里取出一菊香,毕恭毕敬地将香举过头顶,双膝跪在棂前拜了三拜,便将香擦在桌上供着的米筒里。站起来又对死者三鞠躬后,才面对孝子们大喊一声:“发起!”孝子们才依次起来。郭象山拉着眼睛红红的,披着孝服脸色更显白净的郭玉红的手,说了几句:死者不能复生,请节哀的安慰话。郭玉红说着感激不尽的话,并留郭象山在家吃饭。后来周管安排郭象山在灶下烧火蒸饭。管账的郭强又给了他一个孝。他便跟所有帮忙的一样折成一条带歪斜着背在身上。
不一会,县领导、市领导、镇政府官员、以及一些省领导络绎不绝地来到郭玉红家里来探望死者。镇政府领导有的干脆就住下来给孝家帮忙。
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人,小车来来往往,爆竹整天煮粥一样的响着。放哀乐的广播开开停停,从喇叭里不时报出某某省领导来祭奠亡者的消息。还播出了中央某领导来祭奠亡者的消息。于是,所有人都挤向堂屋,大家都想一睹中央领导的风采。但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带着一群人,送来了几个花圈,他们也和常人一样向亡者三鞠躬,之后老者只是对孝子们没有喊那声“发起,”而是用手牵起郭玉红安抚了几句。同时,旁边的人递给老者一沓钱,老者将钱塞到了郭玉红手里。当人们喊留饭时,老者带着那群人,开着几辆小车,一溜烟地走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感叹郭玉红的了不得。做道观的先生们更加卖力了,他们在灵堂一闹就是很长的时间。
到开追掉会的那天晚上,更是人山人海,偌大的地坪里、堂屋里,挤得水泄不通,致掉词的是省电视台的某播音员,掉词播颂得抑扬顿挫,哀怨沉痛,令所有在场者无不唏嘘感叹!
郭象山没有送礼的钱,只好打了一张条子。亡者上山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人,公路上举匾举花圈的人都挤不下,自然,田坎上、山边小道上都拥挤着。队里几乎所有人都为亡者披麻戴孝,等亡者上山后,仿佛山村沉寂了下来。
几天后,郭玉红带着满满的几车东西以及他的母亲回到了城里。郭象山仍然要上山挖土,下田里干活。这一天他正准备出门的时候,乡政府来了几个人笔直进了他的家。当他看到乡政府的人,仿佛老鼠见了猫,吓得康康颤。一个高大肥胖的干部严肃地对郭象山说:
“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按理说,你早年是附近的名人,万元户,不应该拖欠上交款啊,能有几个钱?今天该交了吧?”郭象山支支吾吾了半天,说:
“我真的没有钱啊。”说着他便蹲到了地下。于是,那个干部对跟来的几个彪形大汉一使眼色,几个彪形大汉便冲进堂屋里把郭象山老两口的棺木抬着就往外面走。这时,郭象山驼背的老婆气急了,跑出来就拦,但她被一个年轻人推倒在地,他们抬了棺木扬长而去。此时,郭象山蹲在地下一言不发,他老婆董春愚不声不响地跑到房间里拿起一瓶农药像喝水一样咕咕地喝了下去,不一会,她便倒在自己黑黑的房间里一命呜呼。郭象山见老婆到房间里去后,没有了一点动静,便起身去房间里一看,老婆已经躺在地下命归黄泉了!于是,他对着苍天就喊:
“我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他老泪纵横,呼天抢地。坐在屋里的郭强,听到郭象山呼天抢地的声音十分地凄惨,估计可能他家里发生了变故,便跑上来一看,董春愚竟气绝身亡!而且家里弥漫着浓烈的农药味。郭强立即便将队里的人喊拢来。大家凑了一些钱,准备给董春愚办丧。这时,郭合华也从外面回来了,他看到奶奶死了,而且是被人逼死的,他怒气冲天地拿起一把砍刀就往乡政府奔,后来他手里的砍刀被郭强夺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