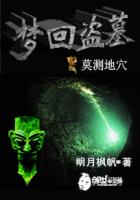农家里有个词来形容足不出户却在家里飞扬跋扈的人:洞里狗;那些呵腰替人跑腿的,叫做狗腿子;自家孩子皮或者不听话,叫狗崽子;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叫狗鼻子狗耳朵;那些跟屁虫,叫狗尾巴。所以凡是涉及到狗的词,都不时什么好词。
那畜生呢?
自然也是很脏的词汇。
但人类爱说。
人类也脏!哈哈。
我时常和舅舅讨论关于人类的事儿,尤其是说词,以前不知道哪些是骂你的,现在知道了,我想起人类小孩叫我畜生,之前没啥,现在却是气愤至极。不过转念想,当时自己扑倒他,他这么说也是应该。
主人家每天会来些人,舅舅指着他们,跟我说哪些是狗尾巴,哪些是狗腿子。狗尾巴天天往主人家跑,狗腿子随叫随到。我问,狗崽子呢?
你看那不是么?他指了指小主人。我笑仰着躺倒在地上。
那洞里狗呢?
他嫌弃的不愿意说话,只是指了指老主人。
我没见过狗鼻子和狗耳朵,只听说,这两类人最狡猾,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斯文禽兽。他们不像狗尾巴溜须拍马,也不像狗腿子随叫随到,他们一出现,往往便是有事要发生了。
舅舅把这类人说的越是邪乎,我越是不信。
某天深夜,舅舅推搡我叫我起来,说狗鼻子和狗耳朵来了。我睁眼一看,是两个衣着得体,体面大方的文化人。洞里狗亲自出来迎接,居然连狗腿子和狗尾巴也来了,他们还是哈着腰一往如常。
都来了,估计这村里要出事!舅舅笃定的说到。
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自信可以这般断定,我看着门关上,然后就坐,开始讨论起来,约么凌晨2点离开,我继续睡觉,把未完的梦进行下去。
九月初,小主人又开始去上学,狗咬人事件也过去快两个月了。他牵着我出去溜达,我便跟着,不声不响;期间碰到被我咬伤的孩子,看见我就往家里跑。香樟树下坐着老头又在那议论着啥,吵吵闹闹,似是真有啥事发生了,总觉怪怪的。
舅舅跟我说,洞里狗和狗腿子狗尾巴把村里的地卖了,他说,没经过别人同意,就把别人的饭碗给砸了,哎,这村子要不太平了。
他说话老气横秋,越来越像那些老头,可却莫名的让人相信我现在相信,至少他说对了会有事情发生。我呐问到:然后呢?
然后就是分钱呗,还能有啥。
他大口吃完盆里的饭,最近胃口又大涨了,不知是被我的崇拜膨胀的,还是跟这秋一样,空气里是丰收的喜悦。
多吃点,长点膘,好熬过寒冬!他充满预见性的说着,然后又低头吃他的食物。
虽然入了秋,但天气却没有凉下来,秋老虎得持续到十一月份,在那之前只是名义上的秋天。鸟儿确实南飞了,不在此处停留,树叶变得枯燥,夜晚蛙停蝉歇,之后就再也没想起来。一场秋雨一场凉,一股秋风声声悲,不知觉间,晚上多了丝萧瑟。
舅舅积储了厚厚的膘,身上有浓密的毛盖着,晚上睡觉就像加了层羽绒被;而母亲却在墙角冻得哆嗦。
她自入秋以来吃的很少,就像得了厌食症一般。每天看着院里的香樟树,看树叶是否绿着,看树叶是否飘落,听秋风是否起了。她在数日子,眼睛里透着哀凉。
母亲,你怎么不吃东西了?舅舅说今年冬天会很冷。
她说自己不饿。从她稀松没有光泽的皮毛上,我知道她是故意的。
母亲,您还是吃点吧,您都饿成这样了,扛不过冬天的。
有时候,吃太多了,反而扛不过冬天……她喃喃道。
我实在是不明白大人的世界,一个吃的这么凶,一个却宁愿自己饿着,明明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两不相同。母亲看着舅舅叹口气,舅舅理都不理净顾着吃。香樟树叶落了又落,似是没有尽头。
舅舅说对了,分钱。这绝对是一件盛事。村里乃至乡里镇里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村委门把卖地的钱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一个人头两三万,村子里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多了十几万的存款,自然是欢喜的,这可能是他们几年的收入,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家里人少的分的少,免不了唉唉怨怨,可总是白拿白不拿,有一分算一分,比没的强。就连之前对卖地反对的人现在脸上也堆满了笑脸。村子里气氛变得比以前活跃,邻家乡里都在讨论家里分了多少钱,其实一看家里几口人就知道,可还是要聊,因为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小主人下午带我去遛弯,时常看见大人对着这孩子点头哈腰的,我突然想起小祖宗这个词,敬意油然而生。村子里还多了几辆轿车,大体都是因为分钱了买的。也多了很多漂亮的狗,有泰迪,有比熊,都是娇小而美丽的,看得我春心荡漾。
这个时候狗鼻子和狗耳朵成了香饽饽,邻村的人开始寻他们,也想照着同样的模式赚上一比钱。那些人给主人家塞了不少好东西,只为了知道这两个人,主人没说,最后是狗腿子说漏了话,那些人便不再来村里晃悠。
来村里晃悠的还有嫁到城里镇里去的人,他们没想到破磁碗变成了聚宝盆,这一块没落地竟能够结出金子来。他们回家看看,虽分不到半瓢羹,却也可以饱饱眼福,也就够了。话这么说,也免不了说几句酸溜溜的话。
之后的一段时间,许多村子都以开发为由贱卖土地,为了短暂的利息,把祖上积下来的福报卖个精光。有个别执拗的老人出来制止,但都被自家孩子哄回去了,于是这大开发便风风火火的干起来了。
我并不关注卖出去的土地开发的怎么样,我关注的是,这一切竟然都被舅舅猜中了。他还是自在的活,吃饭时会拽疼铁链子,我发现他在安静之余总是在观察人,他说人类的行为是有际可寻的,这世界的一切应该都有章法吧,他并不确定,就和他的预言一样,这是未来可能性的一种,他只不过猜中了概率最大的。
舅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问到。
关于狗鼻子和狗耳朵?他们?
他似乎也看得懂我的想法,我极力点头。
他们……应该会在某个深夜,来家里分钱吧。可不是村民们拿到的那么一点,会很多……吧。
于是我便等着那个深夜,夜不能寐。睡不着的不只我一个,还有舅舅。他赶着秋风瑟瑟,不住的对着铁链子抓狂,铁链子不止一次被绷紧,又精疲力竭的松开,又再次绷紧。他积攒的脂肪给他提供足够的力量。我寻思他是在干什么,他很冷漠的看着我,意味深长的说:有一天,你也会这么做的!
入冬后第一场雪来的很晚,快到过年的时候了。但毕竟还没过年,人们都还没有歇下准备春节。小主人迎来了寒假,也在香樟树下堆了个雪人,香樟树也没了枯叶如蝶飘舞,只剩下秃秃的枝桠兀自斜横。女主人穿着貂裘,露着如雪白花的大腿。老主人窝在躺椅里,喝着几上的小茶。似是没有比这更加惬意的时光了。
还未入夜,一辆黑色吉普车停在院子门口,在白色的雪地上显得尤其醒目。四道深深的压痕昭示着来的方向,即使是烙在雪地里的车轱辘痕迹也似乎在张显其价值不菲。女主人媚眼如丝看着门外的车,又看看自己老公,只听到“嘶”的一声,他已起身走出屋外。
舅舅仍旧是卯足了劲扯着铁链子,看他的样子已不像是玩耍这么简单了,以至于把刚进门的狗鼻子和狗耳朵吓了一跳,但他像是仍不知情,继续发疯一般的扯着链子,如痴如魔。
畜生,去墙角待着,安静点!老主人飞起一脚便把舅舅踹到了墙根处,毕竟曾经是练家子,否则就凭舅舅那一身膘,脚踢到也如碰到秤砣一般,寻常人不嗷嗷几下怕是止不住的。
好腿法!狗鼻子忍不住说道。
老主人迎上去,笑脸呵呵:哪里,雕虫小技,莫让这畜生搅恼了二位,还是先行进屋去吧。此时的他看着像个店小二,哪有踢那一脚时的威风,他领二位进了屋,女主人也下来招待,小主人被撂在一旁显得有些不开心了,确是没辙忸怩着回到自己的房间。
喂!没事儿吧!我问道。
你让他踹一脚试试!舅舅不无好气的说道。他在墙角咳咳了几声,母亲看过去,说了句何必呢。舅舅的眼睛里冲了血丝,踉跄了几步,总算晃晃悠悠站了起来,在原地喘了好一会儿,小走几步,然后躺下。他显然是累了,跟个风烛残年的老头一般。那一脚踹的还真是疼啊!他想着,早知道就不这么着急了,无非多待几天,又何妨。这下又不知道要安生多久了。
我过去打断了他的思绪:舅舅,狗鼻子和狗耳朵来了。
看见了,我又没瞎。过会儿狗腿子和狗尾巴也会来,你等着看...
确实没过多久,两人便像雪人一般出现在家门口,相互寒暄了几句,也进了屋。
屋里好不热闹,杯盏相碰。女主人被吩咐去做了几道小菜,虽不是饭点,但这股悠悠香味总勾的人气断回肠。
你说,他们是来干嘛的?我好奇的问着舅舅。
没听过一句话么?人为财死。这大雪天的难道还来走亲访友?无非就是钱么。
哦。我应了一声。顺着在舅舅身边躺下,不小心碰到被老主人踹的地方,他咬着牙嘶了一声,恶狠狠的看了我一眼。我到母亲身边躺下,挨着母亲身上也逐渐暖和。这真是个寒冷的下雪天,舅舅就这般孤身躺在墙角。之前他折腾的脚印被新下的雪重新覆盖。黑色铁链无精打采的横在地上,一端连在舅舅的脖子上。我知道那冰冷的触感,因为我脖子上也拴着一条。
那是舅舅的最后一天——如果再给他几天时间,或许它就自由了——他没熬过那个晚上,没熬过那场雪。他很痛苦的挣扎,绝望的呼喊,最后绝望了,连什么话都不说了,只是向我看来。原来表面上如此洒脱的他也有这般婉转留恋的眼神。他最后说了一句话,留着泪,却笑着:哈哈,他们饿了!
我记得他以前说,小主人馋狗肉,老主人又惯着他,便吃了他们...只是因为馋了!却不曾想到这种事儿会落到自己身上吧!只是这回不是小主人说的,是狗耳朵说的——这大冷天若是来碗热腾腾的狗汤,便是此生再惬意不过的事儿了——那个西装笔挺的斯文人啊,竟是如此冷血的刽子手!
我记得他们商量完事情,老主人话不多说便在自家院内架起炉子烧热水,只一大木棍便把舅舅打晕了,然后架起。待他醒来只能痛苦的挣扎,绝望的呼喊,最后绝望了,连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向我看来。
我记得那些人啊,就站在院子里,雪下,看着老主人杀狗,也不顾他歇斯底里的叫着,我大声吼着。最后直到热滚滚的血流出,舅舅停止了呼吸,放弃了,解脱了,他们仍旧拍手叫好——狗耳朵和狗眼睛一心想着美餐呢;狗腿子和狗尾巴负责烧水呢;那狗崽子,表现的异常活跃开心啊,就连女主人的那只猫也如好事者一般喵喵叫着。——这些人呐!
后来母亲把我拉回窝里,我看着她双眼含恨,不住的流泪,却不哭一声,只是一个劲的把我往回拉,让我住嘴,想把我按在身下,想让我不再看这血腥的场面。可是,可是任这天肃杀寒冷也扼不住我怒火中烧的心啊!我知道即使对面是狮子猛兽我也会奋不顾身冲进去浴血厮杀,无非就是一条命而已!可不能,铁链被我拽的生疼生疼,像是要脱臼要滴出血来,却依旧禁锢着我,任由我精疲力竭。
血染的嫣红,像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染红了一大片,从香樟树的的树根处慢慢的染到我们窝着的地方,如骄阳一般灼眼;雪也融了些,在血的温热下,新下的雪盖不住这嫣红,没有什么能够盖住,死灵魂,伤心人,和嘲笑的人。
舅舅说,要么自由,要么死。我想,这或许不是什么遗憾的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