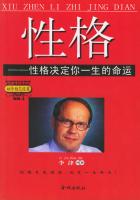不懂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有一种飘落的感觉,好像一片羽毛,在山壑之间,永无休止地漂浮,忽而又沉沉欲坠。或许是从结婚之后,或许···
这时有一道阳光射进来,我转过头,Summy对我行个军礼,说声对不起。我们办公室的窗帘很特别,三个窗户,三种帘,而Summy这边的窗帘不够宽,他就早上往前拉,下午往后拉,早上八点的阳光就很足了,这道阳光不偏不倚地照在我的电脑上。
“我叫朝光,早晨的阳光。”我耳边又响起了这句话,这是我初恋男友的话。
对了,或许就是在我认识他之后,才有这种飘落的感觉。
我偷偷地掐了自己一下,十年多了,自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我还是常常想起他,每次告诫自己忘记他,似乎又多一层记忆,难道初恋真的这样根深蒂固吗?
车间里“雷声轰轰”,是人造雷。MrChua在车间里骂工人,具体讲什么听不清楚,但那声音足够制造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MrChua的声量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以前的邻居张大哥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去树林里吊嗓,就这样苦练也没达到MrChua的声量。
办公室里格外的静,走廊里的脚步声就显得特别清晰了。
“哒啦,哒啦···”是管工阿发的走路声,他个子不矮,脚却比别人小两号。没有他那号的工作鞋,他就每天“哒啦,哒啦”地到处制造噪音。他一进办公室就直奔MrChua的座位,一叠一叠的图纸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会功夫,桌子上的图纸就堆有一尺多高了。
办公室里的人写的写,画的画,其实每个人的耳朵都放在车间里。
MrChua的骂声停止了,估计他正往办公室里走。“蹬·蹬·蹬···”就像侦探片里的警长走在长长漆黑的走廊里,。“蹬蹬蹬”声音越来越响亮,一步一步地走到你屏住呼吸。
脚步声没了,喊声出来了:“阿发,我正在找你。”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阿发面前,瞪着眼睛,歪着头:“阿发你有没有去看工人做工,全部错到完。”他用卷起的图纸敲打着桌子,桌上的图纸噼里啪啦地往下掉。“那个Mulali,不知道是在做工,还是在睡觉,我要杀掉他···明天客户来,我怎么办?我还得用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啊?”
我不禁偷笑起来,“热脸贴冷屁股”虽然粗鲁了一点,但比喻得还恰到好处,我私下里对这句话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
“异艳,你过来,我是在讲你的project。”MrChua的这句话把我从如火如荼的审评中拉出来,抛到了冰雪覆盖的北极。
糟了,我怎么就没想到是我的项目呢?是我麻木了,还是太自信了?我连抽屉都没关,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乖乖地来到老师面前。
“异艳”MrChua的声音如同童话世界里的恶魔:“工人做工,你要跟着看,你的图纸上什么平行度,垂直度的,工人根本看不懂。”
“因为···”
“不用解释”MrChua举起双手喊道,好像我再说一个字天会塌下来似的。这是他的第二句口头禅,虽然只有四个字,却能把你憋到撞南墙。
“唉!”MrChua叹了一口气,然后一屁股坐在他宽大的椅子上:“今天不能买马票了,大清早就骂人”他右手在脑袋上趟来趟去。
“哼!你每天都不应该买,天天那张放高利贷的脸,好像全天下的人都欠你似的。”我这样讲他,是在心里。
MrChua突然想起什么,转向阿财:“阿财,你的客户拜五来,你知道吗?好像材料用的都不对,你最好去看看,”
阿财马上站起来:“Summy鸡蛋糕,去车间。”
Summy气得脸都变型了。
Summy永远是Summy,阿财永远是阿财。
这些都不管我的事。我急匆匆地奔去车间。几个印度人像僵尸似地立在那里,好像MrChua的骂声里带有麻醉剂直接注射到他们的大脑。
我没有骂印度人,我从来不欺负弱者,从这一点出发,我也是一个英雄好女。但我却总是被强者欺负,我的朋友讲我没有回归大自然。
“什么意思?”
“动物的本性就是凌弱强食,人是高级动物,当然保留动物的基本特性。阿财欺负你,你欺负工人,这样心里就平衡喽!”
可我首先不甘被人欺负,因为我是狮子座的女人,我已经这样活了···活了三十五岁了。说真的,说到年龄,我得先算一下,总觉得少活了几年。想到女儿十一岁了,儿子三岁了,还没少活。外婆说的那句话有道理:“一天天地忙来忙去,回过头来,就剩下孩子。”是啊,一个人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地,泣鬼魂的事,事业上没有任何成就,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就是他们唯一的收获。
还是说回狮子座,其实我是不相信洋人那套理论的,中国式的算命是根据你的生辰八字,从时间上看,准确度就超过洋人的几十倍。可惜我出生的时间被搞乱了。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姐姐出世的时候,全家欢腾,父母升级了,做爸爸妈妈了。生我的时候,万众祈祷,希望是个男孩。结果我太让他们失望了,以至于他们竟忘了我出生的时间,后来由于忘记了上户口,也说不准我的出生日期。于是全世界的人向我保证,我的星座绝对没有错,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是富有同情心的,所以我对印度人说:“Donotworry.“
我仔细地检查了印度人加工的这些零件,记录下来,认为可以补救。“Stop,ok?”我用最简单的英文对他们讲,他们全都摇摇头。我急了:“Stop,ok?”
“ok,ok”他们边说边摇头。
“唉!”我敲敲自己的脑袋,联合国也没规定摇头一定表示否定呀(在印度摇头表示肯定)。
为此,我感谢我的老祖先,点头只需一个动作,摇头至少要两次,更何况我总是担心脑袋这样晃来晃去,好不容易学的那点东西,会被甩出去。
我很沉着,我认为一个好的技术人员不只是具有高水准的设计水平,更重要的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一想起MrChua那张冰山似的脸,就赌气了,一定把它做好,我要证明给他看,中国人无所不能。这话是讲大了,就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就可以证明中国人怎样怎样?更何况我算什么呢?怎么能代表中国人呢?只是争一口气而已。
据说上帝是这样造人的:先用泥土做个人,然后吹一口气,人就有了“灵”。这样讲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不是就在这口气呀?“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是不是就指这口气呀?你一定觉得很乱,其实,我就是在胡说八道。
我全神贯注地画着那些被印度人歪曲的零件,电脑对着我,我注视着电脑,越来越近,似乎整个世界只有我和电脑,画,写。管工阿发很给力,我画完一张图,他马上让工人做,我负责画,他负责做,我们双管齐下。
“异艳,你要变机器人呀?不吃饭呀?”汇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门口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午餐的铃声响的。
当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印度的咖喱味扑面而来,我捏住鼻子,说真的,很多人认为印度的咖喱是很纯正的,但我永远享受不了这个味道。
“看,人家都快吃完了”汇云指着那一群印度人,他们在地上围坐一圈,一人前面一张纸,纸上是白饭加咖喱汁,无菜无肉,他们不用筷子,也不用汤匙,只是用右手使劲地捏,捏成一个小饭团,然后放到嘴里,我从没有认认真真地看他们怎样吃饭,据说用哪根手指是有讲就的。
汇云用手背轻轻地碰碰我胳膊:“喂喂,你知道吗?”她压低了声音。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用左手吃饭吗?他们的左手是用来搽屁股的。”
“啊?”我大叫一声“不要乱讲了”
“你不信就不信喽”汇云右手在空中一扫,好像把刚才的话全部搽掉。
我们快到大门口时,看到一群中国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饭。工作的时候,很难找人。吃饭的时候就很清晰了,印度人,马来人,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一群一群分得清清楚楚。
“等我一下”我对汇云说完就跑过去。
“家兴”我冲那群中国人一喊,一个二十左右岁的男孩跑过来。
“家兴,你又和Guto打架了?MrChua说要把你们全部开除,Guto去求情了,你要不要向MrChua求情?”
“不要”家兴回答得很坚决。
“家兴,说真的,我们北方人是有点倔强,我前两天也和阿财骂过架,也不懂会怎样。”
我们彼此沉默。
“回家就回家,反正不加班也剩不了多少钱,这个印度人,他妈的···”家兴又来劲了。
“家兴,你不要胡来,这是新加坡”
“异艳,有完没?”汇云等不及了。
“好了,家兴,你要三思。汇云在叫我,bye-bye。”我冲家兴摆摆手,匆匆向汇云这边跑来。
汇云双手拉着铁门框,十拿九稳地说:“异艳,今天你应该请我吃。”言外之意我今天耽误她太多的时间了。
“可以,我请你吃大···”我学新加坡人,把这个大字拉得长长的,正理是“大餐”,开玩笑就说“大便”。
我们又走在这“绿色小路”上了。
其实我喜欢绿色是有历史的,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去看花展。人家赏花,我看叶。妈妈很生气:“这花展的门票不便宜呦!”;每次登山,我都採一袋子各种形状的叶子,然后夹在一个本子里,这个本子就成了我的宝贝。
我认为在所有颜色之中,绿色是老大,是它拉开了春天的序幕。
正午的阳光把墙壁上常青藤的叶片照得亮晶晶的,光线从叶片抹过,那绿蠢蠢欲滴,晶莹剔透,楚楚动人。使得常青藤比那一排排树木多了几分珍贵。不知什么时候,常青藤开始往这堵墙上爬的,它们的根是属于泥土的,它们的藤不愿被埋在泥土里,借助着这堵墙,努力地往上爬,为了得到更多的阳光与氧气。
“Hi,Hi”汇云边跑边喊。“异艳,飞到你那边去了,黑色的飞虫。”
我还没看清是什么,就拔腿跟着汇云跑。
那个飞虫穷追不舍,好像我们欠它万座金山。
我们两个跑得噼里啪啦的,过路的人有的吃惊地看着我们,有的憋不住地笑···
“没了,没了。”我们终于停下来了,喘着粗气,然后就是笑。
一个小小的飞虫,一根手指就能把它捏死。有些东西,我们怕它,并不是因为它强大,而是因为它太倒胃口。
外面是个有颜色的世界,办公室里是一个被捆绑的世界。
在新加坡你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死心塌地把自己卖给这个公司。我回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了。
第二天,当我正全神贯注地计算材料时,MrChua不懂什么时候串到我面前:“异艳,那些part都可以装进去了,不错呀!”
来这个公司半年了,才知道他会笑。
于是乎我总结出一个哲理:人要学会制造错误,然后自己去弥补,弥补得越完美,就越能体现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