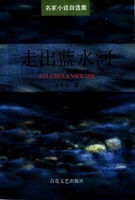要捉獾,只有一种可靠机会。獾最喜食玉米,不但每日剥吃,还要向洞里运输,多多益善,不知餍足。玉米收获时节,半夜时分,獾无分长幼,必全体出洞,来搬抢玉米,与人争食。玉米地在山下,獾洞都在半山,农民们就牵了狗,待狗与獾撕咬时,獾施展一双利爪,锋利无比,常把狗头、狗身挖得鲜血淋漓。农民也惧怕獾爪凌利,用长棍头上套铁圈,圈上有绳网兜,待狗和獾斗得乏了,就用铁圈罩住獾,带回家去;在铁笼里饿上三五天,待它肚腹空空,塞进一个小口大肚的瓷坛子里,封口严实了,深埋在自家院中。三五年过去,打开封口,捞出骨头,皮毛与血肉尽化做油膏,这便是上好的药。山里农民但有跌打损伤、烫伤冻伤、生发脓肿、关节炎症,便抹此油膏,能止痛消炎,祛毒败火,几乎是包治百病了。
老米才走片刻,那药就发出奇效,那只肿得发亮的脚背,止住了疼痛,淡化了火烧火燎的滋味。“老二”知道这药珍贵,把玻璃瓶打开,嗅到一股奇香,就压紧了盖子,如获至宝似的把药收藏起来。
脚背疼痛,思乡之情袭上心头:不知父母弟妹,在家可好;鲁菲远去广州,渺无音讯,似乎完全忘了自己。同来女生二十二人,若与鲁菲相比,没有一个能让他多看两眼,牵动情感。到这泾川县来,已经一个多月,金城尚不能让他留恋,这穷乡僻壤,让人怎能安心。国家大局如此,几百万知识青年都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己是沧海一粟,只能暂时随波逐流,等待时机。
想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百思不得其解。七连三个排,一共八十九户人家,四百零二个人,只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号称初中毕业;指导员和连长,都只念完小学;还有二三十人,五八年参加扫盲,晚上听课,验收成果时,说是脱了盲,还有证书相佐,可这些人都不会写信,不能读书看报;还有一大群小学生,都要去六连上学。
全连四百零二人,只有不到二百个劳动力。许多人才活了三四十岁,患上严重的关节肿大疾病,一瘸一拐地,摇摇晃晃,走路都勉强,完全不能参加生产劳动。
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建二师的战士,真实的身份却完全是山沟里的农民。他们只有种地收粮的经验,教育城里的学生们实在别无长处。再教育关键是一个“再”字,“老二”换了几种想法,都不能自圆自释。但是他仅凭直觉,凭他对城市和农村那种巨大差异的对比,就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自己和其他的学生们,早晚都得离开。他们回金城,自己可是必须回到北京。
吃晚饭时,男女同学都来看望,“老二”拿出那瓶药来,吹嘘了一阵,又当众涂抹了一回,肿胀已经消退许多,开始出现了一丝瘙痒。
年忠义的象棋下得不错,只有“老二”是他的半个对手。山沟里没有电,点的煤油灯,鬼火似的,看一盘棋都费劲。两个人斗了一个多小时,三盘两败,已经比满盘皆输有了进步。“老二”知道,再下一个月,他就可以掌握年忠义的全部棋路,走出胜局来。
五月初,玉米苗出齐了,长到一尺多高。学生们都拿起长锄,学了农民手段,在地里间苗。这种活很轻松,大伙排着队,说说笑笑,手脚不停,向前走动。
这个时节,正是植物疯长的时候,恰好天公作美,下了几场透雨,树木新叶已经长成,新鲜碧绿,微风吹过,哗哗作响;新修的道路两旁栽的榆树和柳树,也都伸展出细嫩的枝条,繁衍出浓密的叶子。农民说这些树只要今年成活了,长大一些,明年开春,便开始疯长,碰到大旱,根扎得深沉,再也不会渴死。山坡上,闲花野草,蓬蓬勃勃;地里的麦子正在抽穗,长得有半人多高。山沟里到处梨花盛开,一片雪白。农民说梨树太多,每年各家各户去拣好的摘些回来,绝大部分落在树下,烂在地里。泾川县本是梨的故乡,“文化大革命”前种的树,现在早已经挂果,只是没人管理,任它自然生长,起点绿化作用。
山里野兔极多,并不怕人,常常人到了跟前,才飞跑出去,中途停下,站直了身子,回头观望。狗儿最讨厌兔子回头,穷追不舍,兔子跑上山坡,狗后腿短,追赶不上,站在山坡下吠叫。
六月下旬,麦子成熟了,连部给每个学生配发陇东农民特有的镰刀。山上的麦子耐旱,根系扎得深,全是冬小麦,不能用手去拔,必须用镰刀收割。这种镰刀很特别:一把长柄略有弯曲,柄头有块横木,横木下面有两个铁夹子,一把二十五公分长短的刀片,磨得锋利,几乎能吹毛断发,插定在横木铁夹子下。割麦人左手拢住麦子,右手用镰刀在麦子根部一寸高的地方迅速切断,再向前推进,如此反复三四次,前面的人用麦杆拧出一根绳来,平放在地上,把自己割的麦子放上去;后面的人跟上来,把自己割的麦子也放上去,再勒紧麦秆绳,把麦子拦腰捆扎结实,放在一边;尔后又是左手拢压麦子,右手挥动镰刀切割,几十个人排着队,把麦子一根不少的收割捆绑整齐。收工时,每人背三五个麦捆,顺便放到打麦场上晒干。
收麦的活,太阳越毒越好,那时麦子成熟了,麦壳闭了嘴,麦粒包得严实,不能脱落。此时若在两天里收割干净,损失就少;如果两天不收割,麦壳就松开了口,一碰麦秆,麦粒就从壳里跳出来,掉到土里。农民说的虎口里夺食,指的就是这两天的宝贵时光。
多亏麦子是个极为灵敏的活物,受了地形、山势、水土、种子、肥料、风向、阳光的影响,从来不肯同一天成熟。总是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东一垄地、西一块地分别泛黄,让农民们憋足了劲儿,跟定了麦子的行情,拼命苦干,把一年的劳动果实抢收抢割干净。
“老二”早就听说收麦子十分辛苦,怕晒坏了皮肤,特意穿着长衣长裤,戴上草帽,跟在农民身后,挥动镰刀,学农民一样收割。镰刀在农民手里,轻巧灵活,挥洒自如,一捆捆麦子摆在前头。“老二”虽然努力追赶,可是镰刀不听使唤,麦子割不干净,地上留槎,长短不齐,十分难看。他便运足了劲儿,割了捆,捆了又割,向前一看,已落后头镰百米之遥。头镰到了地头,又折回来,帮他割麦;身后老农也把他糟蹋的麦子,收拾干净。一天下来,已是腰酸背疼,衣服都湿透了,两只眼睛,受了额头上汗水浸润,蛰得发红,浑身辛苦,来不及清洗,回到窑洞里倒头便睡。晚上食堂改善伙食,半数学生卧床酣睡,不肯吃饭。
像这样劳动,连续十天,一个人蹲在地上,叠成三折,戴着草帽,遮蔽阳光,双手交替舞动,两脚挪移向前;汗水自头顶流下,麦芒从裤脚爬上,奇热难熬,奇痒难耐;不管是什么样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滔滔万言的人中骄子,在陇东的毒太阳下割三天麦子,保他思想呆滞、形容枯槁、行动迟缓、呐口无言。
“老二”坚持了七天,手臂和腿脚被麦芒刺得红肿,浑身力气都已耗尽,躺倒在窑洞里,一个星期都没有恢复过来。
最让他想不通的是,七个女同学,身躯娇小,形体瘦削,一个个弱不禁风一般,平时常要男同学呵护,在这麦收时刻,居然一个也不病倒,不耍赖,都好好地坚持了下来。他一个人躺在土炕上,把獾油膏抹在腿脚和手臂上,感到非常地孤独,为什么别人都能坚持下去,自己却爬不起来呢?也许,人真的是各有长处,像我这样身躯高大的男人,最不能容忍蹲在地下,长久地委曲求全。
第二天,冯子规和赵文军也累倒了,三个人守在窑洞里,长吁短叹,终于有了点生气,时间也飞快流逝。
参加了这唯一的一次麦收劳动,虽然不能坚持到底,但“老二”体验了“汗滴禾下土”的刻骨铭心般的辛苦。从此之后,他在任何条件下,不管什么场合,再也没浪费过一粒粮食。这是他农村生活中最直接、最贯彻始终、最让他获益匪浅的主要收获。
七月初,麦子收割完毕,全部运到打麦场上准备碾压。漫山遍野的杏都熟了,人少杏多,摘不完吃不尽。金城的学生们,生平不曾有机会任意地爬到树上去摘取丰收的果实,他们把杏一筐筐、一担担地运到窑洞里,玩了个尽兴;实在无法消耗,把几条大狗唤到窑洞里来,教它们吃水果尝鲜;狗儿们低头躲避,与学生周旋片刻,窜出院里静卧。
梨和苹果成熟的时候,已到八月中下旬,农民们把没有虫咬和碰伤的梨用麦草一个个分隔开,装在筐里,运回窑洞里存放;到了春节前后,这些硬梨就会变软,聚集出香味,糖分也充足了,特别爽口好吃。
苹果品种差一些,有点酸涩,“老二”不太喜欢。他的心思,全在窑洞外面那六棵核桃树上。他自小就喜欢吃核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核桃树,不知道核桃是怎样生长在树上的。从他第一天住在这儿的时候,就开始关心这六棵核桃树。它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有八九米高,整齐地排列着,树冠巨大,枝干伸展得宽敞舒畅。核桃树准备挂果时,“老二”开始练习爬树,仔细地观察这些深墨绿色的小小青果,为什么能长成外壳坚硬,色泽褐黄的核桃。
山里的鸟儿从来不在果树上做巢,它们知道果树是林中骄子,与人的心思贴得最近。人对果树的照料,是对鸟儿们的无穷骚扰,鸟儿们在远处的树巢中,望着果树们啼叫。核桃树木质极其坚硬,核桃树的叶子阔大而厚韧,核桃的果皮像马的臀部一样光洁而富有弹性。“老二”在这六棵树上攀爬得久了,发现核桃树上竟没有什么害虫,树干都是光洁的,树叶都是完整的,核桃在微风吹动时,幽光暗淡。他在两棵树上找到了可以坐下读书的、宽大的树杈,又在树枝上拴牢一根绳圈,松松地套在两腋之下,手里捧着一本书,伸展开两条腿,搭在两股枝干上,一页一页地翻书阅读。微风驰来,万叶婆娑,浮想联翩,睡意朦胧,书本离手,随风翻动;时间若黄河流水,缓缓逝去。眼看那核桃疯长,乒乓球已经比核桃小了。
“老二”摘下一个核桃,寻来菜刀,从正中劈开,仔细分辨:墨绿色的果皮包着核桃硬壳,白色的果肉,正在灌浆,用舌尖轻挑,又苦又涩。农民在旁看了,哈哈大笑,告诉他:“柿子和核桃在水果里是最晚成熟的,这两种果子,一软一硬,一甜一香,摘得早了,苦涩不能下口,九月中旬,才是收获时节。”
“老二”听罢,记在心里,耐着性子,坐在树上读书。冯子规在树下聒噪,要摘核桃尝鲜,他便委婉说明,温言劝止;别人看见,还以为他在刻意守卫,严禁他人染指呢。冯子规眯着眼,要看“老二”在树上能熬坐到几时!
山上果树繁多,都是五十年代栽种,到了挂果时,交通不方便,也无人收购,只是各家各户,随意摘采。人能吃多少?果子绝大部分掉在树下,烂在土里,来年仍然滋养土地,孕育着一种无人期望的丰收。也有些人家,把杏、桃、梨、苹果抬回家里,混合在一起,煮熟了喂猪。猪儿们虽然外形笨拙,一张大嘴,却极为灵巧,不但吃掉果肉,还能嗑开果核,吃掉杏仁桃仁。
山里人珍惜的水果,只有柿子、枣、核桃。
农妇们待柿子熟透时,剥挤掉皮核,把白面和柿肉混拌得均匀,烙出饼来,软糯香甜,是乡村里的待客佳品。枣可以晒干,留着过年时招待客人;碰到婚庆喜事,红枣又是吉祥食品,与花生相配,含“早生花生”之祝福。至于核桃,农民们晒干后珍藏,逢年过节,或是贵客临门,不管是什么样的饺子馅里,加上剁碎了的核桃仁,那才能显出隆重待客的诚意。
这三种果树,受地气土壤影响,农民们种了又种,养了又养,只是很难成活。韩家嘴学生窑洞前的这六棵核桃树,还是郭连长二十岁时,请来了一位果树种植专家,选出上等树苗种下,精心呵护了二十多年,才有了今天这等繁茂景象。这些往事,学生们哪里晓得,大伙盼的,只是核桃成熟,上树摘采,尽兴玩耍一回罢了。
九月上旬播种完冬小麦之后,农忙基本过去,十几个学生放了假,结伴回家探亲。留下的学生,郭连长召开会议,让大家安心,分期分批,都可以回去看望父母。大会结束时,郭连长又专门讲了柿子和核桃,让同学们珍惜,不要糟蹋了,连领导要统一组织收摘,按人分配,大家都能吃得到。
转眼间已到秋风送爽季节,“老二”在树上读书疲倦,昏昏欲睡,阵风袭来,凉意侵人,打了个激灵,伸展腰肢,跳下树来。人尚未站稳,树上便有核桃落下。他拾起来细看,褐黄色的外壳已经坚硬,表面坑坑洼洼,沟渠密布,似那天外来客一般,与在城市里花钱买的完全一样。他又爬上树,凑到核桃面前细看,原来是有些核桃早熟,墨绿色的外皮咧开口子,要把核桃丢弃。“老二”在树上四处寻找,多数核桃还不曾开口,只摘到六七个,拿到窑洞里,与冯子规、赵文军分吃。
冯子规是个鬼机灵,拿来一把螺丝刀,向核桃蒂缝中插入,左右一扭,分成两半。几个核桃,微甜清香,吊起大伙胃口,都到树下坐着,仰首盼望,直看得心痒难熬,冯子规便去摇树,六棵参天大树,哪里摇撼得动?自己大笑着念叨:“蚍蜉撼树谈何易。”农民们在旁边殷殷告诫:“当心郭连长看见,熟了你们的皮。”
晚上十点钟,风完全停了,冯子规睡不着,叫起“老二”和赵文军,要到树上再寻些能吃的核桃。这时节正在朔望之间,虽然晴空万里,群星闪烁,但白日里稠密的核桃,都隐身于暗影浓荫之中,一双锐眼,无法搜寻,若盲目一般。“老二”因在树上攀爬坐卧得久了,对这六棵大核桃树,熟若自家婴孩,只摸那咧开口子、将要成熟的摘,一个小时,也不过拿到一二十只,揣在口袋里。冯子规和赵文军人在树上,却不知核桃长在哪里,一双手伸出去搜寻,不分好歹,只要碰到,便掠进口袋。
天黑时,郭连长到老米家喝酒,品尝老米白天套住的野兔,吃着很有滋味。几个人喝了两斤散装高粱酒,又饮了十几盅酽茶,都透着浑身精神;郭连长要老米和老贾陪他出去走走,看看学生们都在干些什么。
出院门时,郭连长让老米把枪带上。老米背着枪,又提了根长棍,三个人都带上手电筒,便向韩家嘴走去。
风完全停了,小半个月亮挂在空中,道路依稀可辨,路旁的玉米地里,有动物跑窜的沙沙声。酒劲慢慢涌上来,身体都有些燥热。郭连长解开衣扣,大笑着说:“小时候听我爸说,人到五十,自己给自己下绊子,我说啥也不相信,老米,看你脚下,当心绊倒了!”话音未落,老米脚下一软,就势跌坐在地上。郭连长拉起老米,让他走在前面,自己跟随在后,叫老米两腿叉开二十公分,不要互相碰撞,保证走得稳。老贾在后面,看郭连长已有点东倒西歪,便知道他们两个都有些醉意,自己便多加了小心,背了老米的枪,在后面跟着走。
三里盘山土路,转眼间走完。郭连长直奔那六棵大核桃树,用他那布满老茧子的手,亲热地把每一棵树拍了又拍,想起了二十岁时种树的情形,每天给树苗浇水,眼巴巴地看它们长大。农谚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核桃十八年。真到了核桃挂果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生产大队派出基干民兵守护着,家家户户来树下分核桃时,小孩子们不准到跟前来,都远远地看着。那个时候的庄重、珍惜、企盼,让郭连长激动不已;是他,用自己的劳动,造福一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