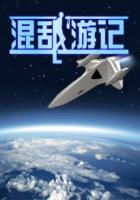横戈儿走得很急,连盏里最后一口茶也来不及喝下。
若在平日里,他绝对不会浪费付钱买到的一切,就算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馒头,也一定会把碗里最后一丝碎屑吃完。
今日,他为何如此急着离开?
横戈儿走路的姿势很奇特,双手拢在袖里,微微弓着脊背,就像一个已有些年纪的小老头,又像寺庙里修行有成的僧侣。他的脚步缓而轻,每一步的间隙几乎完全一样,每一步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每一步的呼吸也近乎相同,似乎不愿意多浪费一分力气在走路上。
这样的脚步,使他在凄清的夜色下有如“隐形”。
一个人又怎会“隐形”?一个人又为什么要“隐形”?
一个人只有在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存在的时候才会“隐形”,从他认出那两个人开始,已决定“隐形”。
——两个早已销声匿迹多时,如今又出现在这里的人。
其中一人赤发虬髯,豹环虎目,貌似恶鬼,身似罗汉。身后斜背六尺布帛包裹的利器,形似长枪。这张脸无疑严肃到了极点,丑陋到了极点。此人若是白天走出去,一定会把孩童吓得哇哇大哭。若是行在夜晚小路上,恐怕连最凶恶的恶鬼也会骇得逃回地狱去,乖乖等待转世投胎,再也不敢出来作恶。
人们看到丑人时,总会不自觉去想,这人笑起来的时候或许没那么难看。如果你看见过这么样一张脸,一定不愿去联想他笑起来的模样。这张脸好像天生不会笑,仿佛从出生开始已失去了笑的能力。
另一人身材消瘦,书生模样,白衣宽袍,玉冠束发。小小的眉毛下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小小的耳朵下挂着两团大大的耳垂;小小的鼻子下嵌着一张大大的嘴巴。他的五官生得奇怪至极,不是很小就是很大,眼耳口鼻似乎没有一处是正常的。
这两个人无疑都长的很丑,或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朋友。
——正因为这样,横戈儿才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们。
这两个人从行出酒肆开始,一路走得很疾。其实也不算太疾,若说他们走得很快,较走得快的人还要慢上一些。若说他们走得很慢,较走得慢的人又要快上一些。
只不过,他们的脚步出奇一致。虬髯汉子迈左脚,书生绝不会迈右脚。书生迈右脚,虬髯汉子绝不会迈左脚。他们看上去一个高,一个矮,一个魁梧,一个消瘦,脚下却像前世已约定,今生一定要一起走。所以,看上去他们走得才会那样快,那么疾。
无论他们走得多快,多疾。横戈儿都在他们身后十丈开外的地方,“隐形”紧跟。他已跟了一个时辰,穿过了十八条街,从京城的外城一直跟到了内城。
他与那二人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十丈。
不是八丈,也不是十一丈,正好十丈,不会多一分,不会少一厘。
今夜,乌云霭霭,无星有月。
乌云霭霭又怎会有月?
圆月已被乌云完全遮住,只露出残月似的一角,有如害羞的处子,虽然用双手捂住脸,却还是不禁从指缝间偷望出来,想要去看情郎温柔的眼波。
因为不舍所以留恋,因为不弃所以窥看。
最后,乌云还是将月光据为己有。就像师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地主,强娶了十七八岁的姑娘,不管人家是否愿意,已等不急要去尝那一抹胭脂香红。
正当“姑娘”被“老地主”完全推上香榻的时候,那虬髯汉子和书生忽然停了下来。
他们一起走,一起停。
横戈儿也停下来。
三个人静静的站着,静静的谁也没有动一下,静静的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这么静静的静静的过了许久静静的又静静的时光。
这一刻,仿佛静静的天上地下只剩下他们三个静静的又静静的人。
虬髯汉子抬起头,他的表情原有七八分严肃,现在,已足足有十分,脸色显得愈发难看。
书生抬起头,小小的眉毛皱在一起,大大的眼睛直勾勾的盯住他所看见的事物。小小的耳朵已被初冬的夜风冻至微红,大大的耳垂在风中微弱的颤动。小小的鼻子不时抽动,大大的嘴巴微微张开,露出一条小小的舌头,两排大大的牙齿,脸色也显得愈发难看。
横戈儿也抬起头,炯炯有神的眼睛依旧灼然有光,平平无奇的脸上已露出了一抹笑意。
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庞,两张其丑无比的面孔,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向了同一个地方。
一座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算不得豪华,也不至寒酸的宅子。
现在,三人所处的地方正是京城的内城。这里多为朝廷重臣,富人商贾的府邸所在,和鱼龙混杂,走卒商贩满街,客栈酒肆林立的外城相比,简直有地壤之较,天渊之别。
住在外城的人每天都会望着内城出神,想着他朝飞黄腾达时,定要在内城修葺一座属于自己的府邸。
他们又怎会知道,拥有这么样一座府邸的背后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任何形式的努力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获得不同层面上的成功。
成功之后,人们会不会后悔为之付出的一切?
如果给他们再选一次的机会,他们会选择继续义无反顾的努力跻身内城?还是选择庸庸碌碌的窝在外城,做些不太起眼的小营生呢?
无星有月静静的夜。
皓月星辰不知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才能在浩瀚夜穹中露出那一点微末的亮。
当黎明到来之际,曙色终将吞噬一切,否定一切努力,抹去一切夜穹存在过的痕迹。
——任何努力岂非付之一炬,转瞬之间已成了梦幻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