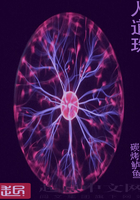接回自己的堡子,接回自己的山神土地,接回自己的亲戚和远嫁的女儿,杨林村的社火在大年初八晚八时正式开演。山神爷一般要坐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家庭里,村民敬山神也是敬那家人。而堡子梁要请进德才双馨的家庭里,这样的人家亦是村民的楷模。杨林村的社火开始时,鞭炮齐鸣,噼哩哗啦的声音里,暗含着请天请地的诚意,在一片与天地融汇的浓烟中,社火开场。与此同时,河对面的固城村也鸣响大戏开演的炮声。
有几年时间,杨林村人认为,邻村的庄稼长势好,是沾了他们村老堡子的光。于是,每年大年初一清晨,第一个重要仪式,就是在老堡子里放炮轰炸,轰炸邻村土地的魂。谁也没想到,大炮反倒将自己村里的元气炸没了,庄稼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还每年过世一位最能干的男人,三年过世了三个。杨林村人才慌了急了,才明白老堡子散发的光芒是无限的。他们请来阴阳先生,阴阳先生借来天碗天水,在水碗里画堡子的像,借来天手把堡子的脉,借来天心叫堡子的魂,叫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叫回来。老堡子生气那天,梁上的土地也生气了,麦子扬一半花停下不扬了,荞麦闭上眼睛不长了,野兽成群结队地出山了。有人看见老堡子手提杨林村到固城村去了,夜里和固城村的老堡子下棋对弈哩!两座老堡子相对而坐,棋子是各自的山梁,棋盘是各自的村庄。杨林村的老堡子拿起鸡公山点将,固城村的老堡子提起秀女峰,占领了对方的将位,那盘棋下了四十九天也没个输贏。
退耕还林那一年,固城村的村民们在山坡上挖坑栽树,对面杨林村人吹唢呐,设神堂香案,数百人匍匐坡上念大经。阴阳先生捏好四十九个面人灯盏,灯芯穿过面人身体,一盏灯里装一斤金黄透明的胡麻油,油里渗透白盐颗粒,摆在半坡点燃。一盏灯就是一双眼睛,四十九盏灯就是四十九双眼睛。四十九双眼睛一起看,纵使看黑夜也能看出白天一样的光明,这是古老秦人叫堡子魂的方法。念了四十九天经叫不来堡子的魂,还可以再念四十九天。“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是对土地的首句叮咛,那可是肺腑之言啊!阴阳先生含泪念完两个七七四十九天的经,眼泪变成甘露的那一天,堡子的魂才啼嘘着应声了。老堡子回村那天,从早晨到太阳落山,固城河里一直浮现老堡子左手提村庄右手提山梁的清晰身影,所到之处光华四射,众鸟飞翔,万物萌动。阴阳先生却看到一道白光飞过苟家阳山,神态似条白龙,飞到堡子梁就隐身了。
从那以后,老堡子上的洋芋个大了,胡麻开花早了,庄稼产量高了,村里还考上一个大学生。大年初一,杨林村人依旧在河边放响第一炮,将新年的第一缕吉祥抢去,再高高兴兴吃早饭迎喜神。这天他们走路的姿势很有派头,要跟固城村的人打架似的,过了正月十五,村戏唱毕忙农活,又都随和得跟亲戚一样。
苟家沟的坟地高处,是我家的九亩山地。当年分土地时,生产队斟酌再三,觉得山大路陡产量低的山地,分给我们家最合适。山地净长些茂盛的铁萝卜,野黄蜂绕花朵飞旋,密密的兔子窝边长满羊胡子草,松鼠们嘴衔粮食跑过崖坡,攀上野杏树。成群的野鸡、野兔、野羊、野猪,悠闲地吃我家的麦子,将庄稼糟蹋得七倒八歪。母亲常说苟家阳山能成熟收获到家里的粮食,都是金木水火土滋养佑护的粮食,能养活人的粮食都是命里没有克星的粮食。山地退耕还林后,我曾去过一次,杨槐树将土地改变得崖不是崖,地不是地,站在地边心里惶惶地害怕。政府每年给每亩土地补助300斤小麦,20元钱。按市场价算,每市斤小麦7毛钱,每亩地补210元钱另加20元钱,共230元钱。要求每棵树都要活着,死掉的必须当年补栽,补不上的按树的棵数扣钱扣粮食。我家的杨槐树一年要死掉两千多棵,领树苗要另交钱,即使这样二嫂还是觉得沾了政府的光,比种庄稼要划算。杨槐树似乎不适合固城土壤栽种。现在,村民念叨最多的是杨槐树长势慢,带来众多鼠类,破坏周边庄稼,如果到拔杨槐树的那一天,怎么样才能将杨槐树从地里拔出去,拔干净呢?
三
仍然以大柳树为中心,过河往南,有条门洞,门洞姓陈,滑向西侧进人田家沟。
几百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了坐落在沟里的田姓人家。大雨过后,沟里三年寸草不生,鸟不飞翔。沟里石头比土地多,斜坡种荞麦,胆子大的长到中秋成熟,被主人用破麻袋包起来背回家,打碾晒干装进麻袋放在炕头准备过冬,胆小的开几朵花靓一靓就凋谢了,人便骂那些荞麦没良心,骂土地更没有良心。
扁食阿婆去世后,有人建议将她埋进田家沟,让她睡在沟里沾染田家人的福气,转世成儿女成群的人家。入棺时,田家辈分最高的男主人,口喷酒水洗干净双手,在扁食阿婆大红绸布的衣袖里,放了两个满月似的白面发饼,饼中央点红彤彤的太阳似的圆点,名日犒犬饼。饼是给路上的拦路狗的,狗不认得扁食阿婆,却认得自家的白面发饼。送葬那天,唢呐声声,黄白纸钱飞舞,不愿跟着阿婆走的锣声、鼓声,跑到后头崖上的崖娃娃堆里藏起来,不愿养活阿婆的圆孔纸钱统统飘进了河流。阿婆新垒起的坟堆插一根雪白孝杆。村人都说扁食阿婆的坟墓像皇宫,从凸起的那一刻起,就引来田家沟的蜜蜂鸟儿,在坟墓四周筑巢皇窝。扁食阿婆的三间破瓦房归公后,分给为她拄孝杆的光棍李福子。李福子30多岁也没有找到媳妇,领养了一个分水岭上的女子,本想女儿长大后招上门女婿,可女儿偏偏看上王家庄的一小伙子,嫁过去先后生下两个白生生大眼睛高鼻梁的儿子,全然不像他们灰头灰脑的父母。都说扁食阿婆终于沾上田家人的光,给李福子带来老来福。扁食阿婆埋进田家沟,命毕竟变得越来越大,三间破瓦房顶覆盖的是一层一层的福气,贫贱的小光芒上面日渐建立起一座座富贵含蓄的小灯塔,这让田家人为之自豪。
在村庄,富贵常常是凹陷的石头,贫穷往往是凸起的山峰。当富贵有一斤时,贫穷早就有了一斤二两的重量。
我想起大妹小时候在田家沟经历过的一件奇事。
秋天,天蓝的像湖水。我和大妹等几个小伙伴,在田家沟的大荞地里拾荞叶。大妹拾了几片就不愿意了,我让她去小溪边玩耍。一会儿,听见大妹惊恐瘆人地哭叫,我们跑过去,问她咋了?她脸色青紫,嘴唇发颤,哽哽咽咽地说一大帮穿红裹肚、身上都发光的白娃娃围住我,摸我的脸,拉我的手哩。”瑞心儿说大妹看花了眼,自己吓着自己了,掰了块随身带的馒头揉成细末,在大妹头上绕两圈,嘴里一遍遍叫:“回来!回来吃奶奶来!”傍晚回家后,大妹仍魂不守舍,战战兢兢地将此事告知母亲,母亲听后脸色很暗,一言不发地煮熟鸡蛋,在鸡蛋上缠了根红丝线,领大妹去田家沟叫魂。返回来时,母亲一路拉紧大妹的手,一路叫:“回来,回来吃奶奶来……”到家时,大妹拿出熟鸡蛋,母亲笑笑说红丝线没断,你的魂叫回来了。”
这事传出去后,王明月便常来我家,极为认真地问大妹,在田家沟看见穿红裹肚的白娃娃是不是真的?大妹就心有余悸地给他讲一遍。他问了几十遍,大妹就有些烦了,他还是诚诚恳恳地问,甚至大妹一看见他进门就躲了。经他这么问来问去,大家才明白,大妹可能就是许多年来第一个看见他家银子的人。王明月坚信,他父亲临死前没有哄他,他的祖先也没有哄他。王明月知道家里这个最大的秘密的时候,才十二岁。这是他父亲临死前告诉他的秘密。父亲死后,母亲就另嫁了人。家中还有一位老人,是他的祖母。那时,他常年在田家沟给生产队里放牛,想起父亲临死前贴着他的耳朵一字一句说的话,就心头热热的满沟满坡找白砚石,找白砚石崖坎旁边的六棵木龙头树,六棵木龙头树对面的地里,埋着他家的六罐银子。王明月找来找去只找到白砚石崖旁边的三棵木龙头树,他无法准确判断方位。一次,他找到一块像银子的白砚石,揣在怀里带回家,放在堂桌中央。邻里亲朋对他说白砚石是鬼变的,夜里能招来鬼魂,不能放在家里。”他听后摸着细瓷般的白砚石,心想,但愿白砚石是他父亲变的,父亲就能领他找到埋在田家沟里的银子。
他结过婚,媳妇是下河里亲戚家的女子,新媳妇偶尔从后门出去到河边淘菜洗衣。一日早晨,到水井去担水的人围在王明月家门前,门前的土台阶上放一只红漆板箱,箱盖揭起,箱里放两双男式毛底布鞋,两顶红头巾,两双袜子和两套咔叽呢衣服,窗台架两床大花被。娘家人用麻绳捆扎了花被,背起板箱从村里走出去时,那女子低头跟随,不停地拨弄手腕上的蒜薹形银镯子。
王明月没打没骂媳妇,就是横竖不正眼看人家,白天到田家沟放牛晒太阳,夜里抱起铺盖卷睡在牛圈里,那女子也不言不语,捎话给娘家人来接她回去。他祖母去世后,王明月孤零零一人,倒活得有滋有味。农忙过后,他天天去田家沟挖崖坎,挖得满沟都像牛耕过的地一样。
歇息间隙,他蹲在地埂边,听沟里的风吹草动,盯住山涧两旁白花花亮闪闪的石头,像银子在上下跳跃,猛跑过去抓在手里,睁大眼睛细看,银子又变成石头。当他明白自己出现幻觉的时候,便扎扎姿势,提提精神,喊叫:“娃娃们,听着呵,听着!”一声嘶哑高亢的秦腔就在山谷中回响。他的演唱极认真极严肃,仿佛山沟有许多尊贵的听众。
唱完一折戏,他匍匐坡上,倾听地里有没有说话声和走动声。他将耳朵贴于石坎,贴在草丛,一会移到东,一会移到西。他完全忘记自己,听完又蹲在崖坎,如一尊雕塑般自言自语:“我家的银子娃娃,为啥不跟我耍呢?”慢慢地,他在前面走,总感觉身后跟着许多银子娃娃,像蚂蚁,排着长长的队例,叽里咕噜地说话,他扭头朝后看,竟隐藏的什么也没有了。
王明月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请银子回家的秘诀。他卖掉家里唯一的骡子,从天水文物贩子手里花800元,买来一个沉甸甸绣花鞋般的马蹄银,埋在木龙头树下,每月挖出来看引来银子娃娃没有。他在沟里埋过十几个地方,马蹄银覆了层铁诱红。又去杨家寺请来白须道人,在木龙头树梢插红白黄绿招魂幡,点蜡上香。道人眯眼睛,挥拂尘,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宽大衣袖风般飘动。时而踏地指山,怒视清泉,时而挥撒泥土,长晡几声,时而宰鸡弹血,口中吐火,把田家沟搞得妖妖娆娆,热闹非凡,折腾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叫出银子,道人分文未取闷头自个回去了。
王明月等了二十几年,开始怀疑他家的银子集体叛变了,或者跟沟里的金娃娃、铜娃娃打架,与敌人同归于尽了。他想到这些,悟到这些,已经老了,他再也不去田家沟了,田家沟毕竟是田家的,他祖先放羊挣的银子,埋进田家沟时,本想招来更多的银兄银弟,没想到连自己的也跟着跑光了。
沟深处宽敞明亮,野花朵大紫大红,野棉花蓬蓬勃勃,雾霭飘飘荡荡,虎狼长晡。沟里有红尖嘴,笔尖形长尾巴,两翅收拢胸部,脖间长黑白羽毛的鸟,鸟名叫写字鸟,写字鸟“嗲”地叫一声停顿一下,节奏极慢,众多写字鸟鸣叫如空谷滴水,飞翔时翅膀乘风,头颅弹琴般伸缩,从森林上空隐人密林深处。田家沟的狐狸叫银狐狸,能驾云彩去天宫,钻地层到地狱。有一年,突发暴雨,天被雷击了个洞,一朵云掉进沟里被水淋湿,化成银狐狸就再也飞不上天。银狐狸藏身沟中,不谙世事,只怀念天上的时光,与田家沟人在内心是隔山隔水的。田家沟人只认山神爷,再大的天神在他们看来都在山神爷之下。夜里骡马丢了,主人站在铺层灰尘的堂桌前,烧炷土香念道薄经让山神爷替他去山里寻找,自己却早早地睡了。后半夜,骡马回来踢柴门,男人嘴里念叨:山神爷打门哩,骡子回来了!打开门,只见骡子,不见山神爷。骡马看主人的目光是山神爷慈祥的目光,主人看骡马的眼神是对山神爷敬畏的眼神。
四
分水岭下来的三条沟走到大柳树所在的固城村就一起站住,汇成一条固城河。固城村是固城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上学、生活、劳动的地方。
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来往古羌道的商人骡队,形成固城街早期的商贸活动。当时固城烧馍大到十余斤,又香又酥,十天半月都不会变味,就着固城井水吃,松软如棉花,最适宜长途跋涉的旅人携带。他们买一两个烧镆,打一壶井水,翻越分水岭,进洛门,到甘谷,抵兰州。上世纪20年代初,礼县商会成立,实行民国新政,本地商人仿效外地商人创办商户的不断增加。固城街张家药铺“复成堂”,已有先生坐堂诊疗治病,远近非常有名,东城墙里的陈家请甘谷先生创立私塾学堂,让他们的子女学知识受教育,并影响乡里四邻,起到启发诱导的作用。
村里每家都有朝街的三间三檩马鞍架瓦房,朝西的土墙是这家人私有的,朝东的一面墙中间有一圆檩,檩中插根两头削尖的细竹棍,以竹棍为界两家各一半。朝北边的一排人家紧靠后头崖,朝南的人家以自家的房基为界到后院河边都是自己的地盘。这是土改时定下来的。每家都有张藏在女人针线包里,写明房屋间数与四至的土地证。屋墙用麦草泥罩面,门窗梁柱用原木原色。房面对面,门对门,一家可看到另一家的土炕、案板、菜坛、木柜。房顶铺清一色灰瓦,瓦缝生东摇西摆的细长蒿草,开几朵不起眼的小花儿。屋四角均已凹陷,雨水积于瓦苔根部,房顶生如西瓜蔓似的洋芋苗,洋芋有苦杏那么大。家家后院有两间茅草圈棚,年深日久,洋麦秆发黄发黑,远看如一朵朵黑蘑菇。村西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伸过街面的粮站,再往前是上街村的果园,卫生院从中街迁到果园,老梨树笼罩一排雪白房子,给果园增添了更深的幽静。卫生院旁侧是新修的初级中学,校园宽敞,终日读书声朗朗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