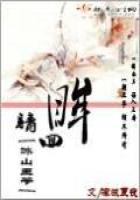丞相薛泽此番前来茂陵,不仅带来了皇帝治愈茂陵伤寒的决心,还送来了两味重要的药材。据说是未央宫廷议前,琅琊王氏锦绣在宫门前拦住了南越左相姬蕴的马车,并托他将一个锦盒转交给皇帝。
皇帝打开锦盒,里面竟然是凤隐先生的一封亲笔帛书。早朝之后刘彻便派人去了荥阳郑氏在京城的宅子,同时去椒房殿见了正在被皇后训话的霍去病。晌午时分,郑默白进宫,紧接着皇帝宣丞相薛泽进宫。之后,便是薛泽带了圣旨来茂陵。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只知道薛泽此行带来了两味重要的药材,而这两味药材正是琅琊王氏先前借姬蕴之手献上的那个古方所缺的那两味药。
那个古药方自到了太医丞袁黎手中,他便一直与松年堂在茂陵所有的医者一起配置药材,只可惜药方上提到的有两味药在这世上根本无从寻起。一味是产自西南夷之地的夜郎国,据说夜郎国深山之中有十里金竹林,里面养了一条金竹巨蟒,其胆可解世间百毒。这金竹巨蟒的胆便是那张古药方上所提到的其中一味药,之所以袁太医丞言其世间绝无,是因为那条金竹巨蟒多年前便被夜郎王下令斩杀了。
而药方上提到的另外一味药则是琅琊东蒙之巅、凤临崖上、琼花树下的一株生长了一百多年的五色灵芝草。只可惜那株灵芝草十几年前便被凤隐先生拿去救人了。故而世间再无第二株那样的灵芝草。
可如今,薛丞相带来的两味药真真切切,虽然已被制成了药丸,经过袁太医丞验证,的确是金竹巨蟒胆和五色灵芝草制成。一时间,众人大喜。
就在薛泽前脚刚进了茂陵,后脚便有一人悄然潜进了茂陵。此人一入茂陵,便直奔容玉所住的地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萧珩。他此行只是为霍去病带话。大抵是说,皇帝突然派飞将军李广前往右北平与驭北将军王锦书商议布防御敌之策,并指名要霍去病与刚刚从陇西祖宅回京的李敢以侍卫的身份随李广将军即刻启程,前往右北平。皇帝的原话是:军情紧急,不得耽搁,即刻启程。
霍去病昨日让容玉等他回来,如今皇命在身,不得已才让萧珩潜进茂陵给容玉带话。他将霍去病的原话一字不落地说给了容玉:“薛丞相已将伤寒所缺之药送往茂陵,想来九儿妹妹的病很快便会好起来!此去右北平,少则一月,多则两月,除夕之前定能赶回,望九儿妹妹多自珍重!来日方长,待我凯旋,等我归来!”由于容家一直严格保密,是以霍去病并不知道容玉的真实病情,一直以为她是感染了伤寒。
夜凉如水,月明星稀,容玉披着白狐大氅,独自立于廊下,目光远放,却又无所依托……
奴婢们远远儿跟着却又不贸然上前打扰。自从那位萧公子来过之后,姑娘便是一直这样不言不语,不喜不忧的样子,晚间的膳食也不曾动过。
远处的山峦在漆黑的夜色下看不分明,却无端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夜风寒凉,偶尔传来几声轻咳,这个夜晚注定是孤寂而寒冷的……
与此同时的同一片夜空下,霍去病一身戎装,立于萧关城头,望冷月寒霜,犹记上次随舅舅卫青出关,也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月色,当时还是豪情万丈,誓要将匈奴打回老家去。可是这一次走得却是如此牵肠挂肚,向来无所畏惧的霍小爷第一次有了离别的儿女情长。此时的他尚不可知,此去匈奴,关山重重,道阻且长,归来之时早已物是人非。他与容玉隔着的不仅仅是烽火连天,还有一个来不及锦绣却已枯槁的今生今世……
接下来的时日里,茂陵的守卫较先前更为森严。茂陵城中,诊寮分布密集,城中先前被程不识老将军围起来的空地如今依然是重兵把守,场中依然昼夜燃薪,火光通天。只是百姓们不再如先前那边妄加揣测,已经知道了那里昼夜焚烧的是因为伤寒去世的病人的尸体和病患用过的衣物。
百姓皆道皇恩浩荡,却不知这其间的凶险。对于茂陵来说,伤寒之症如今有了对症之药,城中百姓渐次好转,笼罩在茂陵上空的阴霾逐渐散去,这便已足够了!
京城各大酒楼茶肆都在盛传茂陵之事……
“此次茂陵伤寒,琅琊王氏算是立了一大功!”
“琅琊王氏再是厉害,能有容家在茂陵的功绩大?”
“你们可曾知晓姬相此番在未央宫与皇上当庭掐了起来。姬相对于茂陵之事主张从严,所有的伤寒重症必须送往九嵕山,九嵕山山高林密、若存心设伏,人进的去也未必出的来,你们说姬蕴他安的是什么心?”
“可是后来琅琊王氏凤隐先生送来了亲笔帛书《论天下苍生》令皇上一夜之间便改了主意,于是便有了姬相和皇上在未央宫廷议之时掐了起来,满朝文武无人敢劝!姬相当庭掷了执笏,甩袖而去。”
“姬蕴其人,手段太狠,到底是不留情面!”
“虽是不留情面了些,可却也是为了长安城的安危!”
……
人群的议论一字不落地传入了楼上雅间隔桌跽坐、默默对饮的两人耳中。
“司马贤弟如何看?”男子轻轻落下一颗黑子,漫不经心的话里似有隐忧。
司马迁状似举棋不定了半晌,终在面前男子的黑子旁边落下一颗白子,这才抬眼看向男子:素白地银线织绣墨兰花镶边长袍、同纹镶玉宽腰带垂挂石青色丙丁纹丝绦,末端系一块成色极好的青玉佩,端的是清隽雅致。荥阳郑氏长房嫡长孙郑默白,自入长安城便得到各方笼络,面对京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牵扯,郑默白一直应对自如、游刃有余,端的是清贵门庭、大家气度,从未有过半分有失偏颇之处,颇有郑氏家主之风。像如今这般在这酒楼上听了大半日市井流言的状况,还真是让司马迁有几分不明就里之困惑。
“默白兄问的是姬相,还是琅琊王氏,亦或是……”司马迁眸微抬、睫微动:“容家?”
郑默白唇角一勾,出口的两个字答得理所当然、问心无愧:“皆有!”
司马迁一愣,随即了然。郑默白与容家玉儿议亲的事情他早在父亲司马谈那里有所耳闻,也知是当今皇太后保的媒,虽然陛下将此事不动声色地压了下去,但是长安城里的世家又有哪个不知。陛下的态度已经极为明显,连远在荥阳的郑氏老家主也给这位长孙带了“静观其变”四个字。本以为这门亲事当就此打住了,如今看来却又未必尽然。
司马迁曾在老师董仲舒那里与郑默白以及冯唐之子冯遂、贾谊之孙贾嘉、田叔少子田仁有过数面之缘,几位志趣相投之人也算得倾盖如故。这些少年名士之中,尤以郑默白与司马迁最为投缘。郑默白虽未曾正式拜入董仲舒门下,却常得董仲舒指点,大抵因此与司马迁有了心照不宣的同门之谊。二人虽不亲近,却也是君子之交,对于彼此的为人心性皆有了解。也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才更觉郑默白此番言语明里像是什么都没说,实际上却是什么都说了。那模棱两可的“皆有”二字在司马迁看来无疑等同于“容家”二字。
心思婉转间,司马迁不再深究郑默白对于容家的态度,却是扫了一眼面前胜券在握的局面,打趣道:“默白兄心思不在棋局上,我胜之不武,不如就此打住,改日重新来过!”
郑默白心知瞒他不过,也不否认,轻笑着吩咐下人撤了棋局,又上了酒水、吃食。
看着郑默白一瞬,司马迁不禁莞尔:“先前听闻老家主请皇太后保媒,为你说容家玉儿这门亲事,我还当是郑老家主独断专行,让你娶一个名声不如意的女子,挫你的清高之气。如今看来,倒是未必!”
郑默白乍闻司马迁提及容玉的名声之言,面色一沉:“名声这种事情本就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坊间还曾传,你与冯遂有分桃之谊,我当信否?”
司马迁不曾想一向温和的郑默白竟然也会有如此疾言厉色的时候,面色一顿,半晌才“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然后煞有介事地将面前的郑默白从上到下细细地打量,似要看出个所以然来。
被司马迁如此打量,郑默白倒是丝毫未有心虚之态,随手执起一盏酒来,顷刻便已酒水入腹,一股回甘之气萦于胸间。
“冯王孙惊才绝绝,又气度非凡,是世间难得的真男儿,不过比之默白兄,却差一点温文清雅、玉树临风。若我真要有一段分桃之谊,那也得选默白兄才不辜负这美景流年!”司马迁说的云淡风轻,语带揶揄。冯遂,表字王孙,乃是汉文帝时的车骑都尉、汉景帝时曾出任过楚相的冯唐的老来子。据说冯唐年逾古稀得此子,极为宠爱,将毕生所学尽数传之。当今陛下刘彻即位后,广征贤良,冯唐也被举荐,只是冯唐已年逾九十,不能出仕,是以刘彻便启用了冯唐之幺子冯遂为郎官。这位冯王孙弱冠之年,身高七尺,才华惊人,颇得皇帝礼遇,因为常常向大儒董仲舒求教,故而与司马迁等人有交。少年才子、风华正茂,历来不缺风月传言,这传来传去不知怎的,就传出了冯遂与司马迁的“分桃之谊”来。
被司马迁这么一打趣,郑默白温和的面上出现了一丝龟裂,良久才嗤笑道:“与司马贤弟论长短,愚兄这是自讨没趣了!”
司马迁不置可否,从桌上的食盘中执起一块饼饵,仔细端详了一阵,这才放入口中,细嚼慢咽一番,还不忘赞这味道极佳。
享用完美食,司马迁这才又将目光转到正细细品酒的郑默白身上,沉吟一瞬,才又略带不解地问道:“以迁对默白兄的了解,实在想不明白兄是何时瞧上了那位的?”
郑默白握着酒杯的手一顿,他自然知道司马迁口中的“那位”是指谁。是啊,他是何时瞧上了容家玉儿的呢?或许是千菊宴上的无心一瞥,又或许是宝簪台的悠悠琴音……
司马迁不知道的是,郑默白当初初闻祖父要自己求取南宫家的女公子之时,并不赞成。郑氏这样的清贵门庭与南宫家那样的百年世家联姻,本来不妥,若再引得天子猜忌,总是弊大于利的。不过对于祖父的决定,郑默白从不置喙。自小到大,郑默白一直是温和有容的,没有同龄人该有的喜怒哀乐,仿佛这世间的一切纷扰到了他眼中都如那遇风而散的青烟,袅袅间便无影无踪了。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是如此,只因他从未将这世间的任何女子看进眼中。他知道,有朝一日,祖父会为他安排一门合适的亲事,然后与自己要娶的女子相敬如宾、直到老去、死去。对于这样早已预料的人生,郑默白甚至都懒得动心思去想,只是平静地等待与接受。
直到那一日,祖父说已经安排好了让他在千菊宴那天进入平阳长公主府里,暗中去瞧一瞧那个叫做南宫未央的女子。祖父说这是孙儿的终身大事,总是要孙儿自己心悦才好!
本来觉得这是件多此一举的事情,再则,暗中瞧一个女儿家,总觉得非君子所为。于是那日郑默白并未刻意去寻容玉,而是一个人在长公主府后院一座僻静的小花园里躲清闲。机缘巧合发现了一座假山内隐藏的棋室,便一个人下棋打发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很久,直到不小心掉了一颗棋子,随即听到外面有女子的声音道:“既然跟来了,又何必躲着?”
郑默白心下一惊,竟然有人发现了自己,正待要起身,却听见有男子的轻笑之声,心下一展,原来那女子并未发现自己……然而不等郑默白心下稍安,便又听见了外面那男子和女子接下来的对话。竟是平阳侯曹襄和祖父要自己前来瞧一瞧的南宫家小九妹。
鬼使神差的,郑默白透过假山的一个可以瞧见外面一隅的山洞瞧了出去,平生第一次当起了那听墙角的登徒子。
透过山洞看去的只是一个侧颜,一身锦绣荣华穿在这样一个颜色未展的少女身上,丝毫不觉突兀,也不给人浓艳媚俗之感。这样富贵张扬的穿着本是郑默白最不喜的样子,那时那刻却忽觉格外地好看,这世间竟有女子能将这样的锦绣富贵堆砌地如此高贵而热烈!
接下来,她与曹襄的对话断断续续地传入了郑默白的耳中,那样软糯娇俏的女子是郑默白二十余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的明艳。虽然未曾谋面,虽然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侧颜,却无端入了眼,或许……也入了心!
看那平阳侯曹襄与她熟稔的谈话,二人当是关系匪浅。后来又见她与祁王世子在小径相遇,她说:“无有筹谋、何谈自由?”这是郑默白第一次从一个女子的口中听到“自由”这样新鲜的词,那一刻郑默白心中掀起的浪涛澎湃汹涌、何止万丈!她说的自由是怎样的?是鳞潜羽翔的自由,还是车马驰骋的自由?亦或是于泱泱乱世之中的独善其身?于身处桎梏中的心之向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能不顾自己的名声也要那或许缥缈本就虚无的自由?
那一刻,郑默白第一次有了想要去了解一个女子的冲动,可那时那刻,那样的环境,他只能透过那个狭小的山洞看过去,目之所及,只看到一个女子远去的背影……
后来,千菊宴上传来的琴音让他惊为天人,本不喜那样热闹的场面,可他仍然循声过去,只是当他寻到千菊宴上之时,那弹琴之人早已离去,只听婢女说方才与平阳侯琴箫合奏的乃是容家女公子……
于是,一直对婚姻之事随缘随份的郑默白连夜给祖父去了书信表明心迹,素白绢帛上通篇只有四句:南有乔木兮不可休思,木有翠羽兮我愿求思。音信迢迢兮通达大父,我心悦羽兮此生未央。
未等到祖父的回信,郑默白便去了莫山之中的姬家温泉别院请姬蕴保媒。如果说一个平阳长公主还不够分量的话,那么加上贵为帝师的南越姬相,这门亲事是否就成了?
然,郑默白未曾算到的是,本来对荥阳郑氏存了拉拢之意的姬蕴此番面对他的这番请求竟然想也不想便回绝了。直到数年后,当郑默白在姬蕴的府邸再见到容玉之时,才明白当初去求姬蕴保媒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再后来,莫山大雪封山,郑默白暂住姬家温泉别院,一连几日都听到瑾瑜殿宝簪台上传来的琴声,几乎是在听到琴声的一刹那,郑默白便知道了宝簪台上弹琴的是何人。于是一连数日以箫相和。琴声时而低沉、时而悠扬,弹奏的皆是家国万里、沙场征伐,若不是曾在千菊宴上听过容玉的琴声,郑默白断然不会以为宝簪台上住着的是一位尚未及笄的闺中女裙钗……
此时,司马迁问他是何时瞧上那位的,郑默白一时之间思绪翻飞……末了才惊觉原来那个人竟不知不觉地住进了自己的心底,而自己尚未觉察已先失了心。更为荒唐的是,自己与那容家玉儿竟是连照面都未曾打过。
过了许久不曾见郑默白言语,司马迁知他不愿多谈,便也不多问。只是话音一转,提到姬蕴朝堂之上与皇帝的争执:“与陛下当庭争执,并不像姬相会做的事,但是他的确如此做了,事有反常必有妖,姬相摔了执笏而去,想来当是短期之内不会再上朝了!”
不知道司马迁说者是否有意,但是郑默白却听者有心。姬蕴虽未帝师,私下与陛下的关系且不论,对于朝堂之事,向来拿捏得当、从未逾矩,当庭摔执笏却还是头一遭。如此大张旗鼓地与皇帝闹翻、甩袖而去,以他的脾气,短期之内可不是不会再上朝了!而皇帝没了面子,如果摔执笏的换了任何一个其他人,估计早被摘了脑袋,可唯独姬蕴,皇帝再是着恼,也不会真的动他。然,天子的颜面总是挂不住的,最严重的莫过于削了他的爵,禁了他的足。但话又说回来,刘彻是何许人,虽大多时候武断了些,可天子的气度却是前无古人的。虽气度非凡,却怎奈天子到底是天子,自有他折不了傲气。姬蕴赌的,或许正是皇帝的那一份傲气!因此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皇帝晾着这位丞相帝师十天半月,不惩不戒,不理不睬。
想到这里,郑默白突然心中有什么一闪而过,快得让人抓不住。既然自己都能想到的结果,熟悉皇帝脾性的姬蕴又如何不知?茂陵之事已定,绝无转圜,他明知自己理亏,却仍然能选在此时与皇帝公然闹翻,为的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茂陵之事本身,而是……脱离皇帝视线的一段时间!
想到此处,郑默白眼睛一亮,对,一定是!姬蕴要的便是一段脱离皇帝视线的时日。那么,他要这样一段时日做什么?或者说,他在密谋什么?
郑默白思来想去不得其解,此时,却听司马迁道:“琅琊王氏下的一手妙棋,引起了陛下对姬家的猜测,又在关键时刻推出了一个王九郎。可姬蕴到底非常人,琅琊王氏的那几分算计,早就在这盘以退为进的棋局里被他算无遗策了。只是不知姬相谋的是什么?琅琊王氏算的又是什么?”
郑默白眸光沉沉,若有所思:“琅琊王氏自然是在对北地姬家的这位少年家主待价而沽,看他是否配得起琅琊东蒙之巅的那方锦绣!至于姬相,深不可测,不可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