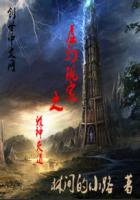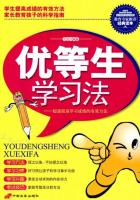长公主府的碧水湖在长安城可算得上一处盛景,碧波粼粼之间,九曲回廊跨湖而建,直通湖心的一座天然小岛。岛上花团锦簇、鸟鸣声脆,即便是入冬时节,也是生机盎然,中有一座木质亭阁样式的小筑,画梁雕栋,纱幔翻飞。亭中燃着暖炉子,还有婢女煮酒添盏,丝竹之乐、吟诵之声时有飘出,间或有女子笑语吟吟,空气中暗香浮动,虽有风花雪月之感却无半点靡靡之意,倒是为这冬日平添了几分风雅韵致来……
容玉一路行来,却是在小筑前堪堪住了脚,抬眸间见亭子的匾额上篆体“飞花”二字笔走龙蛇中却又透出几分稚气,笔力也少了三分气势,堪堪生出两分婉约来。容玉看着这两个字,瞳孔一缩……
“是何人在外头?”容玉凝眸间,却听得亭子里有女子轻软缱绻的声音传来。与此同时,里面的嬉笑声、丝竹声、吟诵声顷刻间全都停下了,四周静如止水。容玉隔着纱幔看不真切,却是觉得心中舒畅,有着如此声音的女子必定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如此想着,容玉嘴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浅笑:“南楚容氏玉儿前来拜见卫长公主!”这位卫长公主乃当今皇后卫子夫所生的长女,深得帝宠,刚一出生便赐了汤沐邑,又因其容貌美满、端庄柔仪而被世人推崇赞誉。
里面的女子似乎没有想到外面的人尚未谋面,仅凭声音便认出了自己的身份,颇为惊讶。不过到底是长于宫廷、见惯了世面的皇家公主,只是停顿了片刻便笑出声道:“听闻容家女公子当日在未央宫前当庭拒婚,可谓是女中豪杰,在这皇城根儿,天子脚下,敢这般顶撞祁王那对父子的,也就你一个容玉了!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快进来让我们大伙儿瞧瞧是个怎样钟灵毓秀的妹妹!”
卫长公主话音未落,便有婢女上前来撩起纱幔,轻纱缓缓被揭起,首先映入容玉眼帘的却是一双紫缎金绣青底男靴,大片金线织就而成的簇团牡丹花间一颗鸽子蛋大的北HN珠,映着那金绣的牡丹熠熠生辉,富贵非常,单是一双靴子便让人瞬间有贵不可言之感。容玉凝神间,那纱幔已经被婢女全部撩起,亭子里的情形尽皆入目。
金暖炉、梨木桌、碧玉壶、绕梁琴……七八位姿容出众的女子皆是绫罗加身,环佩叮当。而在这一众女子中间,正座的靠椅上慵懒地倚着一个黛色锦袍、青玉冠发的十三、四岁少年公子,而方才入得容玉之眼的靴子正是穿在这位少年公子的脚上。明明是懒散的公子哥样儿却偏生出一股子恣意张狂之气,而这恣意张狂之中偏生又透着浓浓的富贵尊荣。在一众莺莺燕燕中不仅丝毫不觉突兀,反而夺了百花的风头,一枝独秀,熠熠生辉。能养出这等气质少年郎的也绝非普通富贵人家,想必就连那未央宫、九重阙也未必养得出这等风华气度。几年不见,霍家的少年郎早已今非昔比、这世间的男儿恐怕没有几人可出其右。
在容玉打量着少年公子的时候,对方也同样打量着容玉。眼前的女子远山含黛眉、双瞳剪水眸,一身风华、如珠如玉,一看便是那钟鸣鼎食、簪缨门庭之家才能教养出的女子,纵然只是眉眼淡淡地站在那里,也是锦绣堆、阆苑林中的一朵仙葩,任你风吹雨打,我自欺霜赛雪、独领芳华。明明只是一眼,却仿若在心间绽放了千年万年……
“噗嗤”少年公子旁边坐着的一位红衣女子率先笑出了声:“倒是奇了,这世间竟也有人让你这混世魔王看傻了眼!”
听了这话,容玉这才看向那红衣女子,十三、四岁年纪,锦绣辉煌,蛾眉螓首,齿如瓠犀,一眼望去竟如那神仙妃子,一身大红锦绣蔷薇图案的长袍,端的是富贵锦绣,天家威仪,容玉心下了然,想必这位便是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卫长公主刘瑶了。
容玉让跟在身边的无忧和子衿侯在外面,自己上前一步,款款入了亭子,朝卫长公主礼数周全地福了一福:“容玉见过卫长公主!”亭中的其他人,容玉虽认不全,但如今当得起她一个大礼的恐怕也只有这位卫长公主一人而已。
卫长公主起身上前虚扶了一把,拉着容玉坐到自己身旁。容玉刚好与那少年公子一左一右围在卫长公主身边,不觉微微蹙眉,但是一想到此行的目的,便也压下心中不快。
“我们刚才还在说着这容家女公子是何等模样呢,”卫长公主左边下手位置的一位粉衣女子看了容玉一眼,笑道:“原来竟是这般美若天仙,也难怪霍小爷看直了眼!”
“就你是个多嘴的!”卫长公主知道霍去病一向不喜与女子有牵扯,她说或许不打紧,旁的人却是万不能拿此打趣他的。如此想着,赶紧瞪了一眼那粉衣女子,假斥道:“也不知道薛丞相是怎么教的?”
容玉心中了然,不禁看了一眼粉衣女子,原来是丞相薛泽的女儿。据闻丞相薛泽家中育有一子二女,庶出的大女儿已经出嫁,那么眼前这位应该便是嫡出的小女儿薛秀锦。
众位闺秀心下均是一凛,自然是知道这霍小爷的脾性,都在为薛秀锦捏了一把汗,却突然听见霍去病清亮的声音缓缓响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容玉闻言,猛然抬起头看向霍去病。众人也皆是一怔,就连卫长公主也眉心微拢地看向了霍去病。
“难道不对吗?你们何故这般眼神看我?”霍去病横扫了讶异的众人一眼,这才将目光盯在容玉身上,唯恐天下不乱地喊了一句:“九儿妹妹!”
这一下亭子里的闺秀们可真是坐不住了,纷纷交头接耳起来,卫长公主狠狠瞪了众人一眼,目光在霍去病笑得痞子似的脸上停了一瞬才最终满怀狐疑地看向容玉:“你们竟然相识?”
容玉心中辗转须臾,神色自若地回道:“容玉自幼便去了楚地,回京不过数日,除了上次未央宫面君,今日还是第一次出府……许是霍小爷认错了人!”言下之意便是不认识霍去病了,不仅不认识,还是素未谋面。
霍去病眸中一沉,不过片刻便哈哈大笑起来:“九儿妹妹记性可真是不好!”
卫长公主见容玉面色不虞,而霍去病却是一脸兴味,不禁揉了揉眉心,然后往霍去病眉间一戳,嗔道:“九儿岂是你胡乱叫的?虽说容家女公子便是南宫家的九儿姑娘,可到底如今是冠了容家的姓,你倒是叫得顺口!还有你倒是说说,何时与玉儿妹妹见过?”卫长公主这话说得可谓极有意思,容家乃商贾之家,虽为皇商,但在大汉朝士农工商,商居最末,其地位可见一斑,别说是皇家女儿,便是普通的官宦千金也是不喜与商家女结交的。可南宫家就另当一说了,南宫府世代簪缨、千年家底,细算起来,便是刘家的公主也是比不过的。卫长公主故意忽略容玉乃是南宫家女儿的身份,心思可见一斑。
霍去病眸子一沉,不过一瞬,便换了一副一脸不解的模样看着卫长公主,道:“长公主阿姊一会儿九儿,一会儿玉儿的叫着,听得去病我好不糊涂!还有就是,长公主阿姊方才的话说得可是不对的!什么叫冠了容家的姓?自古以来,女子出嫁随夫才能算是冠了夫家的姓。如今那容家不过是九儿妹妹的外祖家,即使姓了容那也是作不得数的。南宫将军在未央宫可曾言明九儿妹妹的宗籍尚在南宫山,如此说来容家女公子可不还是得拜南宫家的宗祠,姓南宫家的姓氏。再说了,当年皇上可是亲自赐了‘未央’二字的,自然是南宫未央,难不成还成了容未央?”说话间见容玉眉心蹙地越发深了,霍去病再从面前的桌上端起一个白玉杯,仰头便将里面的果酒一饮而尽,然后砸吧了几下嘴又接着说道:“至于什么时候见过九儿妹妹,这说来可就话长了!往远了说,九儿妹妹的满月宴上小爷我便见过她了,话说她还尿了我一身呢!曹襄可以作证!”
“嘶!”周围人群不禁倒抽一口凉气,这祖宗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再看看卫长公主身边的容玉,一张俏脸红白相交,凤目圆睁怒视着那一脸无所畏惧的霍去病。
“这说的是什么混账话?周围都是闺中千金,你倒是什么话都张口就来,到真应了母后的话,你就是一个浑不吝!”说着又转头歉意地看着容玉:“玉儿妹妹切莫生气!他呀就这个口无遮拦的性子,连父皇母后面前也是这般浑样子!”
容玉眸中一沉,不管霍去病口中所言是否属实,此时都不是一个合适讨论的时间,不过须臾便莞尔一笑:“长公主言重了!婴儿之事哪有什么可计较的?莫说容玉一人,就说在座的各位姑娘们,难道生来便会自己如厕吗?”
长公主面上一顿,这容家女公子看着是个性子好的,却也是不好招惹,有哪个大家闺秀将“如厕”二字毫不避讳得挂在嘴边说来。
闻言睨了一圈才发现,果然众位姑娘都是一副尴尬的样子,显然是不赞同容玉这般有失闺仪的言语,却又羞于出口辩驳。
霍去病却是“扑哧”一声将刚入口得茶水给笑喷了出来,平复了半晌才吐出了一句话:“九儿妹妹果然是深得我心!比起那些整天自命不凡、装模作样的大家闺秀要强的多!小爷喜欢!”
霍去病此言一出,众位姑娘神色各异,一位姿容上乘、银红色霞影纱曲裾的少女一边吃了一口果酒,一边看向容玉,看似柔顺无波的眸底却暗藏着几分凌人之势,出口的话虽是轻慢合度、柔和得宜却是绵里藏针、锋芒相对:“容家女公子虽是养在商贾之家,却也是将门之后,今日真真儿是见识到了!方才还听闻连修成君府的遗姬姑娘都被你推入了水中,这长安城恐怕日后终有降得住那纨绔的人了!也算是为姊妹们出了一口气!”
这话若是平日里说或许倒不会引人推敲,可此时说来,明眼的人一同便是明褒暗损,这个时代本身商人便地位低下,偏偏这霞影纱少女故意点出容家的商人身份,再说遗姬之事,便是暗指容玉虽有将门之后的出生却也是教养有失。再者将容玉同遗姬相提并论一番,自然是说容玉是和遗姬一类的纨绔女子了。
容玉焉能听不出这少女话中深意,只是不明白她眼中的敌意从何而来。虽是不甚在意这样不相干之人的话,却也由不得别人随意践踏家族的尊严,心思婉转间,清浅悦耳却又不疾不徐的话音带着少女特有的软糯之气响在众人耳边:“虽说容家是商贾之家,几百年来却也是钟鸣鼎食、诗礼传家。虽不曾入过朝堂,祖上也曾随过周天子征列国、平天下。即使到了这一代,子孙虽不才,仍蒙皇恩、赐‘百年皇商’名号,却原来在这位姑娘眼中也终不过是商贾之家而已!”说到此处容玉状似自怨自艾地叹了一声,她无意与一群毫无见识的井底之蛙讨论商业的重要性,却是知道什么能唬住她们,不等这一众闺秀反应,又接着道:“说到南宫家的教养,容玉是晚辈不敢置喙祖宗规矩,既然这位女公子感兴趣,何不改日登门与小女的祖父探讨一二?家族几百年来倒也出了十来位帝师,兴大学之事,也是教化了一方子弟,想必祖父还是有资格与这位女公子谈谈这教育之事的!”
在座众人越听越是心颤,这容家女公子果然不是个善茬,一出口便是两个百年世家,一会儿说到周天子,一会儿又是百年帝师、天下教化,这样的世家岂是在座的各位能够望其项背的。南宫家的门生遍天下,恐怕在座众位祖上都还是人家的学生呢,哪敢大言不惭去找南宫老太爷去讨论教育之事,普天之下,也唯有当今皇上敢如此了。
好个容玉,半点脸面都不给对方留,只见那霞影纱少女脸色一阵难堪,却是无从反驳,思索半晌正准备说话,不料容玉像是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补了一句:“还有,那位什么遗姬姑娘,可不是我推下水的!她自己不留神掉进水里,如今倒害的我平白被众位阿姊看笑话!”后半句说的是三分娇憨,七分玩笑,末了还嘴角一弯绽出了一个大大的天真笑脸,本就如珠如玉的双颊顿生两个倾倒众生的梨涡,娇俏的紧。本来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丫头,如此说话倒是让大多数姑娘们愣了一番,随即莞尔,不禁对霞影纱女子露出一丝鄙夷之色,做什么与人家一个小丫头计较,平白地失了身份!
“哈哈哈哈哈”一直在一旁浅酌着果酒看戏的霍去病突然大笑出声,对着那霞影纱少女便道:“夏侯明霜,现在可知道她不好招惹了?别以为自己那个翁主的身份有多清高,她还是皇帝姨父亲封的翁主呢!”说着不顾夏侯明霜越来越苍白的脸色,眸光一转,兴致盎然地看着容玉,眉峰一扬:“小爷早就说过了,当今这天下,也唯有你一人配与小爷站在一处!从今往后,在长安城便有小爷我罩着你,你想横着走便横着走!”
容玉不禁白了一眼霍去病:“我又不是螃蟹,为何要横着走?”
“噗嗤!”、“噗嗤!”这下子顾不得闺仪笑出声来的此起彼伏,小亭子里又恢复了先前活络的气氛。
卫长公主当先戳了一下霍去病的眉心,便笑道:“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霍去病面上却并无尴尬之色,仍旧一本正经地看着容玉:“你要是想做螃蟹,小爷我也由着你便是!小爷说要罩着你就会罩着你,你若不信,这个给你!”说着便要伸手去解腰间的佩玉,卫长公主当下就变了脸色,忙一把按住他的手阻道:“说你是个浑不吝,你还真是没边儿了!这玉岂是能儿戏的?”
“我可不是儿戏!”霍去病一脸认真,还要拂开卫长公主的手继续解玉。
“真是个祖宗!”卫长公主再次按住他的手:“这玉岂是能随意送人的?再说容妹妹乃闺阁千金,怎能平白受你的玉?你若真心护她,便要爱惜她的名声!”
霍去病握着玉佩的手一顿,许是默认了卫长公主的一席话,只见他抬头冲着容玉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改日等小爷寻了罕见的物什儿再送给九儿妹妹!”
容玉莞尔一笑:“其实眼下霍公子身上便有一件容玉感兴趣之物,只是不知道霍公子可愿割爱?”
霍去病眼睛一眯,默了默才笑道:“别说是割爱,便是割肉,为了九儿妹妹,小爷也是甘愿的!”本来是痞气十足的话,不管谁说出来都不免落得个猥琐之嫌,偏生由眼前这个粉妆玉琢的小公子说出来却不显一丝调戏之意,反倒多了三分真诚之感。
容玉眨了眨眼睛,突然间绽开的笑颜几乎晃花了面前这位霍小爷的眼,如清泉淙淙的声音透着些许细软:“适才听我家婢女说霍公子跟南宫府上的一位姑娘开了个玩笑,取走了她头上的一支碧玉簪,不知可有此事?”
霍去病嘴角微微上扬,少女的模样在他墨色的深眸中忽明忽暗,他看了面前的少女半晌,不开口承认却也并不否认。
似乎是心有灵犀般似的,容玉也并不急着追问,只是笑靥如花地望着面前的少年,一双凤眼里清波婉转,光芒乍现。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是一瞬,倒是霍去病先“呵”一声轻笑,身子越发慵懒地向后靠了靠,整个人流光艳艳地半倚着,一只修长白皙却又不失力道的大手随意往胸前衣襟处探去,片刻便摸出一个通体碧绿、流光灼灼的碧玉兰花簪,簪子的一头雕刻着三朵连枝的蕙兰花,碧色花瓣玲珑通透却不张扬,光华流泻间自有一派低调的奢华之气。无论是从雕工还是色泽均是上上之品,真正懂玉的人却是能看出此簪乃东海海底沉埋上万年的绝世寒玉雕刻而成,而这雕工也是出自隐世名家之手,又岂是简单的上上之品,这天下间恐怕也找不出第二支来。
霍去病握着这支碧玉簪,轻拢慢捻地细细把玩着,透过指尖传来的润泽清寒让人不禁爱不释手,抬眼间,看向容玉,轻轻一笑:“九儿妹妹说的可是这支簪子?”
容玉在刚看到簪子的时候便是瞳孔微缩,眸色一紧,再见霍去病如此把玩此簪,心中顿觉不悦,面上却不显分毫:“此簪乃女儿家的贴身之物,霍公子拿在身边也是无用的,不如将此簪交与容玉,由容玉转交给林姑娘?”
“我若是给了你,你当真会给那个林姑娘?”霍去病剑眉一挑问道。
“自然!”
“可是那位林姑娘已经将此簪赠与小爷我了!”霍去病一脸无辜道:“不信你找她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