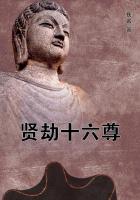“一物降一物啊!”老洪头甩动着空袖子,一边用一只手卷烟,一边嘿嘿乐着说道。然后又扭头对我,神态严肃,目光也冷峻:“鬼儿神儿的倒是小事,不过我可是提醒你们,谌场长也知道,1945年8月,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二百多人从北安去鹤岗煤矿上干活。
进了沟,至今也没有出来。快三十年了吧?那可是二百多人啊!还有1958年的冬天,汤原县吉祥乡四挂马车去大丰林业局倒套子,十七八个棒小伙子,还有十多头老牛,进了沟也没有出来!一匹大白马翻山跑到了咱们老鹤林,一道道的血口子,白毛都给染红啦!后面还有十多只狼在追着它,是你舅舅两枪打死了三条,其他狼群才返了回去!那匹白马第三天也完啦!……谌场长这个人,拉山头过窑工地,这不是故意给自己出难题嘛!我知道狼群都怵他,可是怵他归怵他,万一有不听邪的,你们两个也是个完啊!”老洪头说的是实话,老鹤林的炮手都知道,谌爷和狼群历来就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次前往,感情方面,彼此之间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告别了舅舅和老洪头他们,刚一出门,舅母就追了上来,忧心忡忡又非常难为情地说:“柱子哪!唉!你劝劝他,别去了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心哪,都让他一点点地揪碎啦!”嘴上说着,看我的目光可是有点儿那个!我不敢正视,低着头答道:“试试吧!他能听我的?在河图铺,狼群就救了他一命嘛!”猛抬起头来,舅母的目光火辣辣地看我,看得我全身都有些麻酥酥的。紧张、舒服、期待着,也渴望着。
渴望着品尝异性的那点儿感觉,可是又非常矛盾,扭头就走,两腿两脚都有点儿沉重……西亮子河返回,刚进窑工地,谌爷就哈哈地笑着大声说道:“三辈儿人都来啦!”我说:“谌爷,你给谁说话呢?”谌爷说:“没你的事,赶你的路吧!”听动静,草丛中始终有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就知道,远远近近的灌木丛中,肯定有庞大的狼群在默默地潜伏着。尽管有谌爷撑腰,心里头也仍然是紧张得不行。刚出来窑工地,身后就有声音紧跟了上来。因为天黑,暮色降临,是什么动物跟踪,根本就分不清楚,因为紧张和恐慌,就一声声地喊道:“谌爷,后面有动物跟踪咱们呢!”谌爷头也不回:“别管它,赶你的路!”因为谌爷多次提醒过我:“赶夜路,后面有动静也不要轻易回头,紧走,找到迎避物,然后再猛一转身!……记住了吗?豹子、秃雕、野狼,都单等着你一回头哩!你不回头,它们也不敢轻易就下嘴!”风吹大森林,涛声呜呜地轰鸣着,我一步不落,紧跟着谌爷。
谌爷边走边狠狠地说道:“真他妈的没脸!再跟着找死啊!还不回去,我可就不客气啦!”后面的声音仍然不紧不慢地跟着,我就知道,是十几只野狼在跟踪着我们!过分的恐怖,我的汗毛尖都一根根地直竖了起来。攥着大军刺的右手都有冰冷的汗水滴落了下来。气喘吁吁再一次地喊道:“谌爷,我、我害怕!怎么办啊?”谌爷斜背着大枪仍然是头也不回,气哼哼地吼道:“别嚷!我看见了!六只老狼,五公一母,石洞子跟过来的。这六个家伙成心找死啊!”天黑,风大,雪花飘飘,林子又茂密,谌爷竟然能清楚地看到后面鬼鬼祟祟跟踪我们的是六只老狼,而且是五公一母,不像我估计的那样是十多只。难道谌爷是火眼金睛?
即使是火眼金睛,不回头,身后的动物也辨不清楚啊!如果没有特异功能,谌爷的那一根神经肯定是跟窑工地的狼群密切地联系着吧?我正琢磨着,又听谌爷恼怒般地答道:“前面是乱石塘,这六个家伙都认错人了!别慌!你到前面走,我来对付它们!妈了个巴子的!一再提醒,两次警告,怎么就是不识抬举呢!”说着,脚步没停,仅侧了侧身子,我就三步两步地超越了过去。整个身心顿时也就安全了许多。蹲山沟的人都懂得,灰狼是世界上最狡猾的野生动物之一。袭击人类不是见面就扑,而是七米的距离上不紧不慢地跟着,七米远,也是灰狼最起码的跳远距离,轻轻一窜就是七米,它有把握你是逃不脱的,它不远不近地跟着,用无声的恐怖把你吓瘫,然后再撕碎了饱餐一顿。野狼的力气,一丝一毫它都算计着使用。胆大的人就会将计就计,沉着冷静地用智慧跟它相斗,不回头,不看不理,若无其事,如果吹着口哨,野狼就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弯腰划个圈,再扯根野草或树枝横在圈儿上,继续走人,回头看吧,狼群保证会在圈外聚精会神地研究呢!眯缝着眼睛还不时地交头接耳,非常认真又特别谨慎,直到都认为没有危险了,才悄悄绕开,愤怒地追来。
猎人呢?沉着冷静地再划圈儿,再放根横草,可是狼群呢?明知道是诈,也要停在那儿继续琢磨,继续研究,冒然通过,它们就不是狼了。我刚入伍那阵子,在连队当通讯员,去哨位传达命令,多次遇到狼群,都是用这种办法脱险的。在北大荒生活,仅有智慧和体力还不行,关键得有胆,要不北大荒人的统称都叫傻大胆呢!谌爷比一般人更高出一筹,不划圈,他的冷静就能把野狼给镇住。这六只老狼肯定也是想用恐吓的手段,把我们吓瘫再扑上来吃掉。谌爷早就看穿了它们的阴谋,再三提醒,但它们就是执迷不悟,没有办法才由警告升级为惩罚。没走几步,背后突然传来了“欧”的一声惨叫,伴随着惨叫,是紧张、激烈又稳中不乱的击打声……我本能地扭头一看,好家伙,老天爷,暮色下面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十步之外,谌爷用刀子和双脚,同六只老狼展开了闪电般的肉搏之战。
一比六,谌爷的左右两脚同时踢出,带着呜呜的风声,左手上的刀子也刺了出去,可是他的猎枪仍然在右边的膀子上悬挂着。一只老狼哀叫着向远处逃去,那是被刀子刺伤的、两脚踢倒的,其中有一只像闹着玩儿一样,后腿直立,前爪悬空,整个身体颤抖着划了两个弧圈,然后才极不情愿地趔趔趄趄地倒了下去,随着“欧”的一声惨叫,恰恰倒在了另一只的肚子上。其他三只见事不好,扭回头去撒丫子就跑。欧欧叫着,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啊!我不再害怕。非常开心也非常痛快,刚要为谌爷叫好,但没来得及张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谌爷的右臂猛地一抡,并同时雷鸣般地大声吼道:“站住——”住字吐口,枪声也响了:“咕咚——”从肉搏到枪响前后不超过二十秒钟,变戏法,也是玩儿杂技!眨眼之间战斗就结束了。干净利索,漂漂亮亮,于是我激动又佩服地大声说道:“嗬!谌爷,您可真行啊!快七十岁了,还这么厉害哪!”浓浓的暮色下面,谌爷喘息中略带愠怒地责备我道:“咋呼个嘛!大惊小怪的!”说着,左手上的刀子在大腿上蹭了两蹭,插入刀鞘,同时右手拇指轻轻地一推,猎枪无声中被撅开,枪膛中就有一股蓝烟袅袅娜娜地飘了开来。推上子弹又很重很重地叹息了一声:“逼良为娼,逼良为娼哪!”鼻腔带出来辛酸的滋味。
我知道,他是极不情愿才惩罚了它们的。黑暗中我突然发现他的手上有血。就提醒他道:“谌爷,您手上有血,是狼咬的吧?”见他无语又再次说道:“别动!我给您包上,天冷,可别伤了骨头啊!”他摇了摇头,苦涩、悔恨、痛心又无可奈何地舒了一口长长的闷气:“唉——咋回事儿啊这是?不仁不义,咋就这么不讲究了呢!”然后又命令般地催促我道:“柱子,去,到前边去看看!那只灰狼左面的前后腿肯定都断啦!唉!傻家伙,这不逼着我谌志平跟它们过不去嘛!逼良为娼,逼良为娼啊!”黑暗中听上去,谌爷的心情痛苦到了极点,见我扭头就走,又再次地提醒我道:“小心哪!别让它们把你给啃了……这帮家伙太没心没肺啦!我再三暗示,可就是不听,还以为我怕它们哩!哼!给鼻子上脸,这一下知道什么滋味了吧!”谌爷多次说过,开发北大荒,狼群都逼进山里来了,空间太小,加上人们的捕杀,个别狼群的家族已经变形变态了。
风停了,雪花却来了情绪,由星星点点变成了沸沸扬扬,周围山谷中的涛声呢?也没有因为风停了就跟着偷懒,继续低吼,更增加了一种别样的恐怖:“呜——”我右手拎刀,左手晃动着电筒,顺原路不到三十米,就发现一株低矮的风桦树下面,一只大个儿灰狼在腐枝败叶上苦苦地挣扎着,翻滚中又揪心地哀叫着:“哇儿——哇儿——哇儿——”凄切苍凉,也更让人恐怖。到了近前,电筒的光罩下面,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一只四岁左右的雄性野狼,左侧的前后两条腿都让锣旋纹的猎枪弹给齐刷刷地掐断了,全身是血,爬起来摔倒,摔到又爬起来。听见声音,扭回头用不屈不挠的目光狠狠地盯着我,根根鬃毛都直竖了起来。毫无疑问,它没有认输,想继续跟我再较量下去。它的牙齿像剑一样,咄咄逼人,毫不示弱。“妈的!你还不服气呀!”我几步冲上去,咬着牙根,毫不犹豫就把一尺多长的大军刺捅了过去,对准它的脖子。“嘿!”可是我万没有料到,它的速度比我还快、还要敏捷、还要迅速,闪电般猛一扭头,一口就把大军刺给牢牢地衔住了,咬着刀尖,牙齿嘎吱嘎吱地响,满嘴是血,眼睛通红。我心慌、胆战、恐惧。
使劲儿拽了两下,纹丝不动,它的牙齿更响,“嘎巴!嘎巴!嘎巴!”我不敢松手,松手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我又拽不出来,双方拔河,都用尽了力气,气急败坏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呼喊:“谌爷哪!快来,快来呀!这家伙不要命啦!……”谌爷没有过来,而是再一次鸣枪警告:“咕咚——”枪声在黑暗中的山谷里久久地回荡着。老狼一愣,我也趁机改变了主意,变拽为推,这一招,老狼肯定是没有预料到的,大军刺从它喉咙中穿了过去,牙齿断了,“喀吧!喀吧!”残忍的老狼到死也没有放弃反抗,就在它闭眼断气的一瞬间,伴着一声仇视般的哀吼,“欧”的一声惨叫,一口浓浓的、热乎乎的,特别是腥膻恶臭的黑血也“噗”的一口,顺胳膊喷到了我的胸膛上。与此同时,我的左脚也有点儿火辣辣的疼痛,低头一看,不知何时左脚面被它锋利的爪子给撕破了,大概骨头也露出来了吧?我顾不上疼痛,咬着牙根骂道:“奶奶的,畜牲!你真他妈的顽固啊!”我愤怒极了,一连在它肚子上捅了十几刀,“扑!扑!扑!……”捅累了,恶气也出了。可是用手电筒一晃,老狼的眼皮还痉挛般地跳动着呢!半睁半闭,目光幽蓝,迎着手电光似乎在恶狠狠地骂道:“尹石柱,你等着,变成了恶鬼我也跟你没完!”夜色漆黑,周围的气氛恐怖而又荒凉。
闭了电筒,老狼的目光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我感到心虚,感到胆怯,这是第一次跟野狼打交道,知道它狡猾,知道它残忍,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死狼也跟活狼一样,死不瞑目,阴森恐怖。死狼的目光还是这么咄咄逼人!面对事实我才不得不承认,狼群是个特殊的野生动物群体,个别老狼尸体腐烂其灵魂却不死,在空中悠荡,时时刻刻准备着报仇。夜黑风大,嗅着膻味我的全身好一阵子战栗。但我毕竟不是个小孩子了,单独狩猎,胆量、气魄、手段、力气、经验和本领使我变成一个勇敢又无畏的猎人,猎场是战场,你死我活,残酷的现实是不允许有丝毫犹豫和动摇的。只有以强凌弱,以牙还牙,你才有资格继续生存下去。捅死了那只老狼,我又提刀奔下一只寻找了过去。因为谌爷那一嗓子“站——住——”是不会白白喊出去的,他的一招一式,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和相当的效应,关键时刻,喊一嗓子也能把它们吓个半死。果不其然,离风桦树有二十多米远,我用手电筒搜索到了那只吓破了胆的野狼,灯光射去,我清楚地看到,在一块馒头般的大石头下面,它稀屎满腚,近乎瘫痪,嘴里头还可怜巴巴地哼哼着。没血没伤,与刚才的那只比较,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有点蔑视,用鼻子哼了一声,“操!这也叫狼!你真他妈的‘熊’啊!”又走了两步,凭经验我才辨认出来,这是一只母狼,两周岁左右,身材苗条,毛眼华丽。也可能是它天生就是狼群中的弱者吧,此刻全身像筛糠般地哆嗦着。屁股上是粪便,而尿液还在不停地滴答着。见我近前,它本能地龇了龇牙齿,阴森森的,锥子一样尖细。目光凶狠,可凶狠中又蓄满了更多的乞求。眼角上的泪花晶莹而又明亮。腹部较大,离分娩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吧!看上去自然地蠢笨和软弱。大概是为了体内的后代吧,喉咙中向我一声声地哀告着,“欧!欧!欧!……”也许被谌爷那一嗓子吓破了胆,也许是因为缺钙,四肢怎么挣扎也站立不起来。尽管它是弱者,但刚才那只野狼垂死挣扎中用爪子给我造成的创伤,使我怒不可遏,仇恨在胸,抓着大军刺毫不犹豫地直捅了过去,“妈的!都是狼啊你们!”我出手极快,带着一股风声,“嗖!”防备喷血,刀尖逼近才略有松缓。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我注意到母狼的目光转向别处,可怜巴巴又吼了一声:“欧哇——”似乎在呼喊:“快救我啊!你还等啥呢?”它没有抵抗,绝望中在喊谁?夜色浓浓,这儿毕竟是窑工地啊!我不由地一愣,本能中顺母狼的目光向前面找去,看到目标,极端的恐怖,我差一点儿就跌坐了地上。老天爷,好危险啊!电筒差点儿都滑落在地上了。二十多米远,有一只尖耳朵、红褐色、矮健凶猛又彪悍强壮的大号野狼,牛犊子一样,在另一块庞大的石头上跃跃欲试般地盯着我呢!鬃毛戗着,张着大嘴,目光死死盯着我手上的这把大军刺。
这是狼窝中的霸主,天然的领袖,主宰窑工地非它莫属啊!我知道,刀子再继续前探,这家伙就会毫不客气地扑下来,泰山压顶,我的脑袋轻轻松松就会被它给咬碎,太危险,太、太、太可怕啦!狼王、母狼和那只死狼恰好站成了三角形状。刚才我捅的那十几刀,狼王肯定是目睹了,容忍我放肆,肯定是有它自己的打算。狼群中绝对没有病残者,我不杀掉,它也不会放过。至于母狼,肯定是它的娇妻了,况且腹中正怀着它的后代,作为丈夫和父亲,它不可能,也绝对不会容忍我的目的达到。至于没及时扑来,是它知道谌爷的子弹是大睁着眼睛的。子弹的速度会比它的动作更快……
果然不错,我身后传来了谌爷的脚步声,每走一步,夜幕下的山谷都在轻轻地颤动。事情再清楚不过了,狼王护着母狼,谌爷也在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狼王不敢迅速进攻,是狼王知道谌爷的刀子和子弹,都在约束着它的残忍和血腥。狼王狡猾,但狼王也明智。谌爷过来,我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我晃动着军刺,军刺的刀尖又指向了母狼,母狼只有哆嗦,连欧欧的叫声也彻底消失了。可是狼王呢?若别妻弃子逃走又不忍心,营救吧,是明摆着的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它不敢营救又不忍心逃走,呆呆地愣着,残忍和暴戾迅速地收敛。当我左手上的手电筒再次对准了它的目光时,奇迹出现了。狼王合上大嘴,轻轻一滚就滑落了下来。两条粗腿很慢很慢地跪倒在了地上,“欧!欧!欧!”地哀叫着,脑袋低垂,目光偷偷地观察着我们。残忍之中更多的是无奈,仇恨之中又蕴含着它的苦恼。虽不后悔却流露出了它的悲痛,表情复杂,目光始终在躲躲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