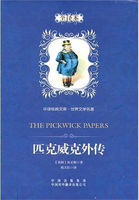宝瓶还听见他们对旁边的人群里说,他的大脑有点问题,他们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们还说他们是他的哥哥,他们要把他带回家,不能让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丢人现眼。彩蛋节,人人有责,人人都要做点贡献嘛!他们向人群讪笑着。宝瓶的嘴有点疼痛,估计也是刚才厮打的结果。他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是打了一个结。他想告诉人群,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根本不认识他们。可是他只听见自己的嘴里发出一连串模糊的声音,嘴角这儿还有点腥甜,无疑嘴角开始流血了。他疼得说不出话来。宝瓶意识到这两人的歹毒,他们无疑在刚才的厮打中就对他的嘴下了手。显然,打得不轻。
宝瓶疼得咧歪了嘴,他想给他们作揖,求他们饶了自己这个老实人,他可是真的没有什么过错,他可是一直真的待在家里的。然而他们的手紧紧地箝住他不放。宝瓶觉得自己完全被他们控制了。他听见耳朵里呼呼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的耳朵也受了伤。他想揉一揉面颊,那里火辣辣的。
观众人群里还有人望着他们三个人远去的影子,不过很快就随着欢庆的队伍向着另一个方向而去了。踩高跷的偶尔还会掉头看看,他惊讶地发现,那空下来的一节大街上,那三个人再次奔跑了起来,两个追一个,不过很快,前面一个便被追翻在地了。
宝瓶蜷缩在地上,不想从地上爬起来,他得赖在大街上,可是最终没有得逞。短须和眼镜几乎一边一个将他挟持着。他明显感到两肋疼得很厉害,刚才他不知道是谁跪在了上面。他几乎“啊”的大叫起来,停止了乱舞的双手。就这样他们再次擒住了他。
宝瓶被他们推搡着,他们已经消耗了不少体力,此刻有力地用手你一推他一推地敦促着宝瓶的步子。“你他妈的快点。”宝瓶听见他们骂骂咧咧的声音在耳朵的风声里忽来忽去。有时候还会用脚踢踢宝瓶的腿部,宝瓶无力辩解,现在大街上的人们已经将他看作了一个疯子。他现在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真的和一个疯子无异了。他开始呜啊呜啊地大叫起来。事实上,他们开始经过一家超市门口的水果摊跟前。
那些闪亮的水果码得很整齐,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芒。一阵强烈的饥饿感抓住了他。显然,那个馒头早就消耗光了。他三步并着两步跳上前,还没有等人们反应过来,他就毫不犹豫地抓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这显然要比刚才在小吃店门口吃馒头方便多了,他想。一个疯子,人们能拿他怎么办呢。果然,水果摊那个麻脸的老头只瞪了他一眼,那个手拿着布擦水果的中年妇女也就笑骂了一句:这个疯子,倒饿吼了啊。
旁边还有些人说,他倒流血了,真可怜之类的话,宝瓶听得很清楚,他觉得喉头一阵哽咽,于是他拼命地啃着苹果掩饰过去了。他觉得自己被别人怜悯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被他们又踢了一脚。他几乎打了一个趔趄,好在他极力稳住自己没有趴到地上去。
宝瓶想往南走,他将回到自己生活的那个街区里,尽管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条路是最抄近的直路。那样他一见到熟人就好办了,而这里于他是一个陌生地带。热闹的人群,谁会注意他宝瓶呢。他记得如美说过把你往人堆里一放眨眼就没有了,她的话是何其正确啊!自己很平常,宝瓶知道这一点。现在想这些,显然迟了。倘若他以前不把大块的时间浪费在家里和床上,他完全可以和这些街道上的人们熟稔起来的。偶尔去职介所,他也像是做了贼似的,来去匆匆。现在他周遭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宝瓶以为这大概就是隔绝于人们的好处吧。宝瓶自嘲地想。他感到自己的胳膊像车龙头把一样,转了一下继续向前了。
经过一所小学门口,宝瓶看见一个扎着马尾的年轻女教师正在要求小学生排队,女教师的马尾在空中跃动,她不停地做着手势。学生们都化了很浓的妆,较之他们穿着的蓝咔帆布校服的庄穆,显得格外艳丽。宝瓶盯着他们有点出神,他觉得他们像明媚的小鹿。不过很快,短须和眼镜又要求他向前走了,他们不停地催促着他。他只是以不停搡动自己的胳膊来抗议。吃了苹果,他感到自己的咽喉部分清凉多了,轻轻地咳嗽了几下。
往宝塔的路上人很少,不用说大部分人去看街上的文娱表演去了,这里只有几个行色匆匆的过路人,从他们的肤色和身上夹带的浓重的鱼腥味看来,他们大多从河西赶了摆渡过来的。这些人几乎看都没有看一眼与他们交肩而过的宝瓶他们。大概就是路静人稀的情况吧,宝瓶开始思忖着,他要忽然转身由此逃脱才对。他知道愈往后就愈没有办法了,他的牛鼻子就被牵牢了。宝瓶回头看了看,学校里的学生已排着队上街了,他们整齐地迈着步子甩着小手。
他们开始问他话。他们在僻静的地方倒显得有人情味了,在人稠热闹的地方却把他往死里打。宝瓶真想索性假戏真做,不去理睬他们,继续呜哇呜哇地叫个不停算了。可是他转念一想,他得稳住他们,让他们毫无防备,然后自己再来个漂亮转身。就像在小逗号咖啡厅那样,他随意地说些什么就从中拔脚逃之夭夭了。贡献一段与女邻居的艳史又算什么呢!于是,他告诉他们那学生队伍里有他的孩子。不过,这不是编造,宝瓶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有过一个女儿。
如果是几年前,他是切切实实有的,可是现在没有了,没有了。
一看到学校他就会想起来。他想起来,就难过。要知道他不上街不看见学校就意味着不与悲伤相遇。而现在,不期然就遇上了,宝瓶真的难过了起来,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牙根、眼眶这儿发酸,他不得不用袖管去擦拭泪水。他已经顾不得了。他的确想起来了他的孩子,那个小可爱。宝瓶眼前晃着女儿的影子,她全身湿漉漉的,脸孔发紫,一副好像在赌气的样子。然后是一匹狂奔的牛,它奔走在运河堤上。他的女儿躺在上面。那头牛把她驮走了,驮远了,驮进了云彩里。
宝瓶感觉到自己的肩膀被人用力地拍了拍。他们似乎很是理解和同情的样子。宝瓶一点要搡开他们手的愿望也没有了。他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止住步子。梧桐树几乎贴近了一道新刷过的围墙。他再次揉了揉眼睛,考虑该怎么脱身。现在的情形愈来愈不利了。巷子且不说愈来愈逼仄,他们的手此刻倒不离他的肩了。宝瓶知道他们表面上像是安慰他,实际上时刻在防范着他呢。这时候,迎面过来一个青年人,宝瓶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家伙,他的脸膛和手臂都发出剽悍的光。总之比他们三个人都壮实,宝瓶之所以放弃了向他求救,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手段。他们肯定会说他是一个疯子,脑袋瓜有问题,还会说他们是他的哥哥。他的辩白将一无用处,反而更会说成是疯言疯语,反被打一顿也说不定。现在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徒劳的。他们将他夹在中间走,一点机会也不给他。或许他要做的就是伺机而动吧。
他们等那个年轻人过去并且转弯向东去了。他们开始行动了。宝瓶看见短须和眼镜交换了一下眼色。宝瓶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交换眼色了。然后他听见眼镜说:“说实话,我们也不想搞成这样,这是迫不得已。我们开始只不过逗你玩而已,没有想到你一点也不好玩。搞成这样,要说过错你自己也有一份,再说,你也方便不少呀,可以随便拿人家东西吃,不要花一分钱,其实你要一直这样下去,何止是一个苹果呢。对不对?只是我们当时很担心你会随意地去骚扰人家妇女和小姑娘,看来你还是一个正派人啊。当然了,你和你的女邻居的故事,我们姑妄听之吧。你的情况其实我们清楚得很。”
“是的,我们事先调查过你的情况了。到你们公司一查就查到了。虽然你不上班了,但是你的情况还在那儿,就像树砍了还有根一样,我们查起来容易得很,”短须在旁边补充道。“其实你还是有点正义感的人,大伙对你的评价不赖啊。我们还知道你下岗百分之八十的原因呢。你或许还蒙在鼓里吧?”
宝瓶听了以后有点惊骇。他感到脖领这儿一阵阵发凉。他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可是短须和眼镜并不理会他的惊恐和他的问题,他们或许对现在的宝瓶还在问这个问题有点不屑吧。只是说,他们是上面的。果决的语气噎得宝瓶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上面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词在宝瓶的脑海里只意味着方向,而不是其他。他不解地重复了一句:“上面?什么上面?”
他们对宝瓶一时的糊涂有点意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他们很郑重其事地告诉一脸惘然的宝瓶说:“且不管这个吧,我们当时约你,包括等人都是真的。只不过,那人没有如期而至,只得劳你跟我们走一趟罢了。如果不是你节外生枝,四脚乱奔,我们或许已经往那里去了。”
“到底到哪儿去啊?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
无论宝瓶再怎么问,他们都不开口了。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催宝瓶走快点,他们劝宝瓶不要磨磨蹭蹭的。他们说:“这样不好。早点到,于谁都有好处。说实话,我们也巴不得早点交差呢。”宝瓶现在是真的无话可说了。他知道现在的谜面向他展开了:有重要的人物要找他,而且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宝瓶还感觉到这些事情好像还比较隐秘,单就从短须和眼镜领着他选僻静的路走就可以看出些端倪。当然,他们之所以不搭公交车,专拣少人的陋巷走,大概也有一刻没有放松防范他宝瓶的意思吧。
宝瓶的余光里他们两人脸上挂着汗珠的,看得出来他们对于他一直不敢大意。宝瓶慢慢地平静了下来,轻轻地搡了搡自己的胳膊。可是他们并没有领会宝瓶的意思,反而将他箍得更紧了。宝瓶于是对他们说:“算了吧,事已至此,我不会再为难你们了,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为难你们等于为难我自己,”他顿了顿又继续说,“看得出来你们也不容易,你们松手吧。”
“你们松手吧,我保证不跑,宝瓶感觉到他们的胳膊像两把镰刀一样还挂在自己的身上。”
他提高了嗓门,“我说不跑就不跑!松啊。我保证!”
两个人这才松了手,他们面面相觑,然后盯着不停甩着胳膊的宝瓶,事实上,他们把他夹疼了。他们中的眼镜脸露愧意地说:“兄弟,你要是早点这样我们就不会难为你了,俗话说,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啊。”
“是啊,是啊。早点这样,你我都少受罪了啊。”短须也在一旁附和道。
宝瓶忽然间觉得两个人有点可爱起来,他对他们只是笑了笑算是回答。此后,短须还递给他一个手帕让他揩一揩嘴角的血迹,血迹早已经干结了,但是宝瓶还是表示感激。他觉得他们应该好好地走下去,一直到达目的地,作些配合是他最佳的选择。
这样的情形短须和眼镜自然很是高兴,他们要比在小逗号咖啡厅里热情多了,开始邀请他一起用饭。因为中饭时间到了,宝瓶觉得肚子里空得很,是他力主找个小饭馆祭了五脏庙再说的。鉴于他们温和起来的关系,宝瓶觉得有此要求并不过分,再说,的确时已过午饥饿难耐。尽管短须坚持说再耐一会儿,到了地头之后,好吃的多得很,要比这街上的小饭馆高级不知多少倍。宝瓶也估摸到上面的人自然吃住不差的。眼镜未置可否,他只是盯着喉结翻动的宝瓶看。最后他们两个人还是听了宝瓶的劝:“我肚子饿得不行,先填饱了再说吧,再说腿酸了,也跑不动了,歇歇脚吧。”
于是他们不得不随地就简进入了一家小饭馆。小饭馆里热气腾腾,只有少数几张桌子上坐着人,用手里的筷子轻轻地敲着桌面等菜上来。小饭馆虽小,但是比较整洁,墙面粉刷一新,迎面正墙上贴着打印好的菜单。他们三人捡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短须说:“本来计划我们要到那儿吃的,如果我们路上没有费那么个周折的话”短须还有点耿耿于怀,眼镜要他不要再抱怨什么了,他说,他也的确饿了。
宝瓶靠着窗,看着窗外的一条内陆河,河水难得一见的清澈见底。河的对面是连屋的住家,满目的藤蔓植物蔓延在墙上。那些斑驳的墙上也开了数个大大小小的窗户,一个窗户里一个穿线衫的女人在忙碌着,她姣好的身段看得宝瓶有点出神。他们让宝瓶点一个菜,他瞄了一眼菜谱随意地点了一个菜。这个时候他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只是等他点完菜,那边的窗户内丰美的身影消失了。
那边依稀听见有人说话,他们谈的是晚报上的内容。一个人说道,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他说着边抖动着报纸。另一个说,其实怪事还不是天天有嘛。先前的那个人继续说,这蛇比一般的蛇大一点儿,肚腹这儿还有些花纹的样子呢,看看。
那人将头凑过去,报纸哗哗地响着。哎,是的,倒像朵菊花呢。
说蛇胆里竟然有一个弹子球一样透明的东西!
昨天电视上还有一个用鼻子唱歌的!另一个说道。
南方又干旱了,唔,又有煤矿死人了。报纸又哗哗地响了。
报上说那阿拉法特不是什么病死的,是被暗杀的。
唔,或许吧。看,又一个巨贪毙了!
而这边宝瓶脑海里却印着刚才那个窗内的影子,屋子里有一个女人多好啊,宝瓶想。他喜欢这种感觉,现在他的视野里空了,只剩下绿叶藤蔓和空口的窗。宝瓶心里有点怅然若失。这种感觉一直包围着他,一直伴随着他吃完了这一顿午饭。再次上路的时候,宝瓶明白他大抵是过于想念如美才这样的,他可以肯定。
他在屋檐下泻的阳光里摇了摇头,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如美。可是他办不到,一路上短须和眼镜不明就里,他们搞不清楚宝瓶为何沉默不语了,可是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小心地观察着。这种情况一直到了西门渡口往北湾走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运河在眼前闪动着,远远的樯帆,还有迎面的风和树使宝瓶一下子心情舒畅了起来。
很快他们又恢复了交谈,宝瓶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问:“你们说知道我下岗的百分之八十的原因?我这会儿倒想听听呢!”
短须笑了,他的声音被风滤过一般显得清爽悦耳,比此前说话要清晰多了。他说:“其实那是我们随意说说的,你也相信?”眼镜也在一旁笑。随后,短须继续说道,“不过确实有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譬如你碰见你们经理那回。不光我们,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你算是吃了哑巴亏吧。”
这件事情宝瓶想起来仍有点愤愤不平,他嘴里左一个狗娘养右一个狗娘养的。显然他对那个经理恨之入骨。宝瓶说他才33岁,就已经下岗三年了。他的日子过得不轻松啊。他开始讲他一天两顿,他的如美,他的女儿,他的旧房,他的冷清清,他的没有尊严,甚至他的性生活。他的诉苦显然再次博得了短须和眼镜的同情,他们也一致谴责那个私弄职权的家伙,其实他们也只能这么说说,安慰安慰宝瓶。宝瓶说他其实是无意中碰见的,再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就此事说三道四,更没有想到在这个事情上做什么文章,他说他宝瓶向来不是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