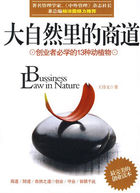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超出人们预期的轨道而一意孤行。
一个寒冷周末的清晨。曾子凡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怀揣酝酿多日的梦想,匆匆赶到禾玉曼的工作单位。
深蓝色的棉线围巾缠绕在他稍显清瘦的脖颈上,颇有点五四青年的范儿,略长的黑发被路风吹得像个鸟窝。自行车刚一停稳,他便钻进楼洞,来到禾玉曼的宿舍。
“咱们结婚吧!?”刚推开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说,仿佛这会儿不说,后面就无法说出来似的。见禾玉曼表现出一脸的惊愕,他才感到自己的表达有些莽撞和唐突,神情略有不安。
“结婚,太仓促了吧?”禾玉曼闷了一会儿说道。
结婚,在她的心中似乎是功成名就才可谈及的一件事情,成家立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婚事被大大超前地列入议事日程,缘于曾子凡父亲病情的不容乐观。年龄大的人,特别是身体有病的人,都不太容易适应气温的骤然下降或升高。上周末。从西伯利亚吹来一股寒流,给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带来骤降,老人的病情因此突然加重,饭量锐减。庄稼人一般视老人的胃口来判断其身体状况。前两天家里发来电报,催促尽快举行婚礼。
农村流传一种冲喜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能够举办一件喜事,就可以冲破家里的灾难,或是化解家人的病痛。对于曾子凡来说,父母把他养育成人不容易,如果真能如乡俗所预言的那样,用一场婚礼能拯救父亲的疾病,甚至生命,他绝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即便是一场虚妄预示未来的蜃景,他也要尽力去试一试。
而对于思想相对传统的禾玉曼来说,结婚是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大事情,和他才认识几个月就要结婚,未免太过匆忙,太过草率。从小缺乏母爱和家庭温暖的禾玉曼自从遇到这么一位细心体贴的男生,真切感受到人间的幸福和温暖,兀然出现这个状况,又怎能不让她纠结万分。
可婚姻到底是什么?她不了解,他也一样不知情。一想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希望将要和一个不甚了解的人今生今世连接在一起,禾玉曼感到十分惶恐和茫然,带着心中的疑问,她后来向过来人询问真谛,却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看似浪漫的恋爱,熔化在平日的生活里,不免附加琐碎的烦恼。情感的浓度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稀释和降解,生活无处不像汉语拼音的四声,平仄起伏。她隐约感到过一支不和谐的音符,那是对志趣理念解读上的误差,就像每个人对衣服的颜色款式审美上的差异。然而,最终却是时间的胁迫,乡俗的魅力,爱情的冲动,她顺应了他的全部渴求和执拗。
稚嫩的青春色彩,在懵懂和忙乱中渐渐离去,在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被截然分隔,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记忆,成为生命长河中一个难忘的节点。当丘比特的神箭射穿她的灵魂,她的全部善良、真诚与情感将全力以赴地朝他奔去。
一间小小的斗室。她宛如一条柔情若水的藤蔓,用纤弱的触角抚摸他结实的每一寸肌肤,棱角,额头,脖颈,炽热的烈焰燃烧着两颗剧烈沸腾的心房,他第一次真切找到了母性肌肤的气味,沉醉在迷雾般的仙境中。在他的带领下,她的指肚不失时机地沿着一片坚实平滑的黄土地不断探索和攀援,直至长着几根坚硬毛发的腹部,到达让彼此感到惊恐与慌乱的沼泽之地。
窗外,寒风轻吻枯树,太阳羞涩地钻进云层。曾子凡眉头紧锁,跌入使身体全部倾空的痛苦与黑暗中,一丝失落划过大汗淋漓的脸颊,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禾玉曼的身旁。
自那一刻起,禾玉曼内心的孤独正式宣告结束,模糊而清晰地住着一个日夜牵挂的人。不经意间,思念的帷幕开启,一种崭新未知的生活,就将像季节变换一样自然翻开。
谁能料到:在未来生活的胶片上,将会留下多少美好的瞬间;多少平淡的岁月;多少痛苦的画面……这些都会像电影胶卷一样,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不断的被剪辑,复制和收藏。无论怎样,都是一本厚重的历史长卷,需要用漫长的生命历程去谱写,去演绎。
禾玉曼同意了。两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商榷婚礼举行的日期,购置一些必备的物品。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来到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场。思来想去,时间不容对衣物有更多的犹豫和选择,只逛了两家商场,就把必备的外套鞋袜基本购置齐当。
腊月里一个平常的日子。天空阴晴不定,干燥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一大早。身着红色毛呢褂子,蓝色裤子的禾玉曼站在母亲那台老式木柜前照着镜子,第一次给自己冻得发紫的嘴唇涂上鲜艳的唇彩,在白皙的脸庞上用面友抹了一层,还打了些腮红,再用眉笔添了几笔,原本普通的五官顿时看起来漂亮了许多,姐姐为她整了整衣服。
穿戴一新的曾子凡前一天来到禾玉曼家,吃完家人特别制作的小巧玲珑的饺子,两人携手走出家门。禾玉曼的父母,姐妹和弟弟站在大门口,满含热泪目送一对新人踏上牵手百年的背影。
“路上小心!”伤感的父亲不放心地叮咛道。
“放心!”
就在回眸的那一刻,情感的丝线蓦然间搅动伤感的泪花。禾玉曼不敢直视家人的面孔,赶紧转过头挽起新郎官的胳膊,走过家乡尘土飞扬的街道,登上开往平原市的长途汽车。
上午十点多钟,他们换上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禾玉曼垂及双肩的鬈发随着车身的颠簸而微微抖动。中午时分,汽车盘旋在山涧坡道,西北风吹得更加强劲,扭曲尖利的哨音在山谷间呼啸。漫天黄土,天地间一片混沌。她用手指划开玻璃窗上的薄冰,沟壑纵横的黄土山坳,褐色灌木,苍黄枯草,白茅在孤寂的寒风中随风摇曳,远处宛如珍珠般的绵羊点缀着苍凉大地,严霜封冻的大地寂然不动。
薄暮时分。一对新人,风尘仆仆踏上充满喜庆的场院。橙色灯光照亮了往日寂静的窑洞,照亮了半个山坳。门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和窗花,红色对联。临时搭建的帐篷下,一群孩子围着放有瓜子喜糖的桌前椅后嬉戏玩耍,看热闹的乡邻站在张灯结彩的窑洞外张望说笑,操办人背抄着手忙前忙后,露天大灶台前,厨师忙得红光满面,帮忙的乡邻开着浑色玩笑,烘托着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因时间仓促,没有置办一件婚嫁,没有一件家用电器或家具,只有临时粉饰的窑洞。墙壁涂料还未干透,几张明星画,两床叠放整齐的被褥,充当了新房的全部装饰。
见到新娘新郎到达婚礼现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山谷间响起,等候已久的婚礼主持人扯着嗓子召集宾客乡亲就坐。一对新人站在众乡邻面前,就像两个听话的木偶任凭拉线人任意摆弄,完成婚礼设定的几项程序。
一帮裹着白毛巾,花头巾的男女艺人站在主持台的一侧奏响锣鼓唢呐,震耳欲聋的信天游响彻在窑前屋后,在寒冷的夜空中激情回荡。前来祝贺与帮忙的人们轮流吃完羊肉汤,饸烙面。一场不同于城市,有别于乡村的婚礼就已渐近尾声。
夜间,西北风裹挟着粒粒细雪越过喜庆退潮的场院,钻进门窗的漏缝,冻成晶莹剔透的冰凌。午夜。新娘被一股浓重的烟熏味呛醒,她迷迷糊糊地爬起来。黑暗中,炉火旁有团明亮的星星火光,她意识到:什么东西着火了。
“着火啦!”她一边喊,一边慌忙扑打。
身旁酣睡的曾子凡被她的惊叫声吓醒,赶紧点亮了灯。隐火被扑灭了,可禾玉曼的手腕却被烫起了几个发红的大水泡。洞房花烛,意外着火,一丝不祥的预兆在禾玉曼的脑海中闪过。曾子凡赶紧从隔壁厨房端来醋壶,为新婚妻子的烧伤处涂抹……
当窑洞的拱形窗户露出晨光熹微时,大雪已经停下了。禾玉曼用力推开被寒冰封冻的门板,寒气倏地趁机钻了进来。屋外的树枝,枯草,山坳披上一层美若如画的银装素裹。崖畔上,一株腊梅正傲雪盛开。
纵然顺应了乡间习俗,也未能拯救曾子凡父亲的生命。那年正月初三,病魔缠身的老人最终走完他坎坷多舛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