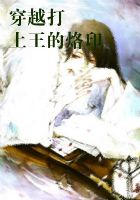其实,看风景的人,本身也是风景的一部分。
这个暑假的午后,站在敞口车皮里的梁晓刚,不停地向北张望着。这时候,车子已经到了一个弧线形的大弯处。汽笛“呜——”的一声长鸣,滚滚浓烟中,车头隆隆奔出;梁晓刚向后望出时,只见车尾正蜿蜒盘旋在百十米外的圆弧上。蔚蓝的天顶下,这架势,还真像一条长龙正腾云驾雾而来。
到了直道以后,火车北侧又换了另一番景象:这是一条西东流向的大河,河身大致与铁道平行。微微西斜的阳光洒在河面上;微波荡漾的水面上,点点鲤鱼般的金黄,不是跳跃着,闪烁着,煞是壮观。一群羽毛如雪的鸭子,也正自西向东游动着。显然,它们对南侧这移动着的庞然大物颇感兴趣,奋力拨着水面,要和这庞然大物一较快慢。然而,“呜——”的一声响过之后,这巨龙般的庞然大物,头部远远超过了它们;瞬间之后,连“龙尾”也掠过了它们眼前;甚至,当这群鸭子定睛细看时,这“龙尾”也越走越快,越变越小,远远地把它们这些水上健将抛在后面了。这群鸭子目瞪口呆之余,拼尽洪荒之力扇动着翅膀,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嘎嘎声。然而,不管它们如何愤怒、不解,这列火车还是远离它们而去了。车皮北侧的梁晓刚,饶有兴致的观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
电影《铁道游击队》那悠长、舒缓、乐观、动人的歌声,缓缓流过心间。只是,这漫漫长路,一路上的风景,再怎么变化,终究也是大同小异。于是,再过了一阵子,阵阵倦意慢慢袭来,那眼皮也快睁不开了。也就在这时候,一大片乌云涌向那西沉的太阳,天幕下的一切,一时也不那么炎热、炫目了。向车皮里看去之时,发现哥哥正在小憩,梁晓刚就走了过去,坐在哥哥北侧,支起膝盖,以手为枕,打起盹来。行进中的火车,尽管外面风声呼呼,这节敞口车皮里的风儿,却是恰到好处,既没有暴晒之虞,也不至于声音过大影响休憩。于是,午后的清风中,梁晓刚甜甜入眠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他觉得自己的眼睛霎时睁开了。“柳州?这是柳州火车站——”这样轻轻念叨着,他环顾一下,发现周围满是涌向涌向出站口的人们。“哦,柳州站到了,怪不得这么多的人——”这样想着,再转头一看,伯伯正在他左侧,正挑着一担用麻袋装着的豆角、辣椒、西红柿、白菜。
“晓刚,你还跟着我干什么呢?”伯伯的话语,透出一丝不高兴。
“这,这——”梁晓刚支吾着,眼光依然投向了前边的出站口。
“你超高了,不能够跟我出去了,我只买了一张票。”伯伯这样说道。
“那,那我走峨山——”梁晓刚说着,向月台西北侧的峨山望去。
伯伯点了点头:“对啊,你又不是第一次到柳州了,怎么连这点都想不起来?你没有票,只能走峨山,到时,我去找你——”说着,伯伯挑起担子,向出站口走去。
尽管有点不情愿,梁晓刚也没有跟在伯伯后面:卖菜这样的小生意,利润本就不高,多买一张五毛钱的车票,也不知要多卖几斤菜?再说,因为没买票而走峨山的,也不只他一个人。
于是,当伯伯的身影看不到时,梁晓刚跟在了前往峨山的人群的后面。这峨山,离月台有三四百米,二三十分钟以后,也就到了。这,其实是一个道口,铁路的西南侧,有一个小小的值班室。从两边穿过铁路的人,满眼都是。到了那儿之后,梁晓刚也算是出站了;他,站在值班室另一侧的一小片空地之上。这片空地东南数百米处,就是正规的出站口;半小时之前,伯伯就是从那儿出站的。
时近正午,快到头顶的太阳,大火球般炙烤着大地。在空地上站了一会儿之后,梁晓刚撑不住了,就来到了对面的一个屋檐下。尽管一时免了被太阳暴晒之苦,梁晓刚的心里,依然沸水般翻涌着:从铁路值班室那边走过来的人也就罢了,从火车站方向走过来的人,少说也有百儿八十了吧,可是,这些面孔,都是那么陌生,绝不可能是伯伯啊!伯伯,现在你在哪儿呢?是忙着卖菜?只是,你再怎么忙,也不能忘了我啊。哦,是不是一时忙不过来身呢?不,不会吧?刚才明明交代我在这儿等待的。那么,会不会是忘记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可不妙,我身上连半毛钱都没有!伯伯是个生意人,这点记性,应该是会有的。只是,既然精明能干,如何就不赶过来呢?这样的等待,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唉,早知道是这样,这个上午,不跟他出来好还好。如今,上头有烈日,心里——“咕咕咕——”几声响起,不错,是饿了;此外,口也渴了,那嗓子快要冒出烟来了。
路边的小树,影子都缩成一个小黑点了,梁晓刚所盼望的伯伯,依然没个影子!
从东南方走来一个穿工作服的中年男子,不是伯伯。
从东南方向走来几位谈笑风生的生意人,其中没有梁晓刚的伯伯。
几个提着菜篮的中老年妇女走过来了,自然也不是梁晓刚的伯伯。
“这,这可怎么办呢?”这样想着,梁晓刚皱紧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