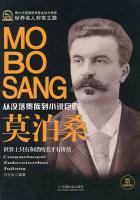华桑的冬天总是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却不知掩藏了多少深宅高门的勾心斗角。
齐颂带着东西回宫禀报太子殿下,却没有意料之中未完成任务的责备。太子殿下收了东西后,只从沐阳宫内殿一帘之隔传来淡淡的声音:“无妨,这次倒不是你办事不利了,该来的,总会来的。传信让齐云回来吧。”之后便再无声息了,仿若那声音从未响起过。
齐颂走后久久,太子依旧坐在棋盘前,神色清淡,左手执白子,右手执黑子,伯仲未分。棋子莹润柔滑的材质衬着那纤长有力,骨节微现的手,更显清雅高贵,完美无瑕只怕更让女子羡慕。
只见他右手指腹缓缓摩擦棋子,看着棋盘之上纵横捭阖,似乎想到了什么,眉梢上挑,唇边溢出一抹微不可见的弧度,一声呢喃消逝在凛凛冬夜中:“九儿你到底去了哪里呢。”这事在华桑太子殿下的身上甚是罕见,几乎很少有人有事能让他笑,然而现在却真真切切存在,若是让他的近侍们看见,一定会惊得掉落下巴或眼珠了。
再说今日距离无声楼被灭已过两天,大将军府中东边院子里,晏卓绎对元九说着这两天来的发现。
千影阁暗杀无声楼果真是玉清和林枫二人带的路,他们恰好是玉门宗被灭的那一年进的无声楼。千影阁阁主陈烈是玉门宗宗主的亲弟弟,此次怕是为兄报仇。然这两天千影阁动作频频,似在紧急寻找什么人什么事。元九当然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只因事关重大,她不能对晏卓绎说出来。
元九有一颗七窍玲珑心,片刻的思索,再加上这两日她也在考虑日后的事,已在心中有了计较。晏卓绎问她今后有何打算。
她静静看着晏卓绎,这个多年的知己朋友,笑道:“华桑自百年开国以来,朝廷便设了一处官位,独立于六部之外,只对皇上直接负责,是也不是?”
晏卓绎不知她心中所想,但并不急于问出,只答道:“不错,那是谏廷司,从开国建朝时就已经存在,且此处官员官位不高,司谏大人也只有五品,没有实权,却是朝中最特殊的一处地方。它直属帝王,只对皇上负责,专职犯言直谏,为帝王敲警钟,更可指出朝臣之不足。他们不介入朝堂党争,只做帝王的一面镜子,亦可说是朝廷的镜子。谏廷司谏士虽官位不高,却极受人尊敬,并且谏廷司的官员皆不是由科举选出,而是在每三年一次的春闱期间,由京师有名望的人举荐,通过述谏考选拨而来。这些人或为府宾,或为幕僚,亦或为其他市井之民,只要他们有胆量有担当,刚正不阿,敢做大多朝臣不敢做的事,不怕得罪人,就可通过述谏考进入谏廷司。”他还没有说的是,谏廷司的谏士口才极佳,善于雄辩,而且他们大多出身不高,又是孤家寡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因而就算当朝皇子权贵也对他们客客气气,礼让三分,更不想一朝犯错被他们逮到。
“明年开春,又到了春试的时候了吧。听闻建国至今,华桑国也有过女子入朝为官的典范,当今圣上贤君明主,任用人才更是不拘一格,当朝一位正四品翰林学士正是女子,对吗?”元九说完,便走到窗边,径自欣赏屋外雪景,不管晏卓绎惊异的眼神。
晏卓绎脑子一转,显然被惊吓的不轻,大睁着眼睛看着元九说:“你想入谏廷司?你可知那是个什么地方?我知道你素来胆大不拘小节,可女子入朝为官,其中艰难险阻何几?全天下没几个这样的例子,再说翰林学士与谏廷司谏士那可是天差地别。且不说你胸中是否有墨,单凭你是无声楼少主的身份,皇上与朝官就不可能让你进去。小九,你可知道?就算你进去了,那里没有实权,你又拿什么来寻找真相?”
他的惊诧,在元九的意料之中,不过元九依然望着窗外,嗓音空灵清远,却透着说话人的坚定。她说:“卓绎,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别无选择,我要完成秦叔叔的临终嘱托,我要拿回原属于我的东西,我要揭开这重重迷雾,找出真相。秦叔叔给我的线索在皇宫,一旦进入皇宫,无论什么身份,必定多方掣肘。何况我也不想被困在那个华丽的牢笼。我思量左右,入谏廷司是最好的选择。我知女子入朝为官之艰险,也已做好走在风口浪尖的准备,这些我不怕,我只怕自己势太单,力太薄,没有坚固的后台为我做引荐。现如今,我也只能依仗你,你,会帮我的吧。”说完她转头看着晏卓绎,切切的目光好像在说“你不答应我就一直看着你”。
晏卓绎看着她的眼,只觉那魄人的目光竟生生为那平淡无奇的脸庞添了溢彩,明眸流光,夺人心魂。他暗暗压下心中的触动,眉眼舒展,眼中盛满无奈,轻笑道:“你我相交多年,在利益方面从来都淡如清水,这是你第一次有求于我,我岂有拒绝之理。”
元九走向桌边,端着茶杯细细嗅了一下,又抿了一口,咂咂嘴笑道:“啧啧,不愧是大将军府,这骆陵峰的青骏眉可是红茶中的上品,非显贵之家不能享用啊。用冬日的雪水煮沸冲泡,会有淡淡的幽香,生津清热,提神消疲,养胃护脾,最适合冬日饮用。”
晏卓绎突然觉得这几年的相交,自己竟从未真正了解过她。彼时她是那个喜嬉笑打闹,话里不饶人,大大咧咧的无声楼三只手,种种表现完完全全的江湖草莽儿女,只差用目不识丁来形容。此时却又头头是道,条理清晰,俨然不似从前。江湖草民哪里懂得品茶,还是京师权贵之茶,连功效都说的那么清楚。截然不同的感觉,却又真实存在。他亦望着元九,示意她为自己解惑。
元九坐在他对面,收起方才戏谑之情,正色道:“我虽自小长在无声楼,但秦叔叔却让我把该学的都学了,现今我十六年所学,应是当个谏廷司谏士足够了。至于我的身份,你不必担心,我已有了计较。再说没有说进了谏廷司就不能移职,当今户部侍郎李承甫不就出自谏廷司,他也不过而立之年便被皇上破格提拔,我又有何不可?”
晏卓绎听罢,又道:“看来你对朝堂还是有所了解,定然早有打算,何苦不早早明说呢。相识多年,你的胆略我多少知晓一些。只最后一点,你打算以何身份去?”
元九走向窗边,指着外面的天空对他说:“陆者,万物之始也。浩渺星河,盈盈月华。搏击青海,翱贯长空。从今天开始,再没有无声楼的元九,只有长空,陆长空。”空灵悠远的声音四从天边传来,晏卓绎只觉得连空中的月都黯然失色。清冷的银辉洒落在窗边,为窗边的人镀上一层华光。隐隐夜空中,将渐渐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光华流转间,灿然不可逼视。
很多年后,晏卓绎每每想起这一晚,都忘不掉窗边月光笼罩下,身影淡薄却心志坚定的女子。也是这一晚,让他丢失了十八年来一直不曾悸动的心,许下了他用一生来坚守完成的诺言。
元九极郑重对他说:“卓绎,你知晓我是恩怨分明的人,让你涉入朝堂做你不喜欢的事我已愧疚不已,荐我之后,我必不再难为于你,你亦可远离庙堂之高,安心做你的闲暇游士。今后的路,我要一个人走。今日之恩,他日你但有所言,我莫不以诚想报。”
听罢,晏卓绎掩下心中的涩然,只淡淡一笑:“你我无需客气,况且荐你本不是什么大事,报恩就不必了。日后朝堂艰难,有事对我说便是。我谨在此祝你心愿得尝罢。”心中却暗下决心:“往后,你不会是一个人,只要我在,诸般险阻,我愿与你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