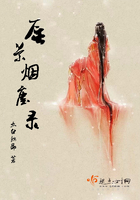“不是,他不像我这么文武双全的,呵呵。我搓手是冷的。魏野当时说…那句话是…噢,是说’野寺群僧媚骨庸,岂识赋闲真英雄。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
“嗯,你这可别是影射我俗吧。”王梦雨搭手过来,目光晶莹地看着我问道。这完全出我意外,急忙摇头说:“啊,哪呀,绝对没有那意思,就是提到了区别对待的事儿,想起来那么个故事。”
“不是笑话我俗气?”王梦雨恢复了微笑时的柔美。我使劲点点头,又说:“知道你是为我着想所以要铲了去,又不是说不好,再说我写的东西,凭谁褒贬了我还能不答应是怎么?”
“我替你不答应,你倒又无所谓了。”这种硬气的话由王梦雨一贯的轻柔口吻说出来,别有一种娴雅雍容、磊落恢弘的气度,我笑道:“真要有人愿意褒贬的时候,那我还不就已经出名了,想也不用想的事。”王梦雨说:“没人知道的时候,写得再好也不会有名气,出了名,不好也可能被吹捧,就像郭沫若的诗,49年以后的我就偶尔看到一眼,简直受不了,连我爸妈那么老革命似的思想,都受不了。反正你的我挺喜欢,不过不是那种题给余红图的,像刚才写在沙坑旁边的那个,意境不错,又没有什么敏感的内容。其实,你就只写些抒情隽永风格的就行吧,省得万一招惹出什么麻烦来,中国的事情谁说得好?”
“那倒是,当年清三代搞的文字狱,有几个不是莫名其妙的就被定了大罪?连嘉庆即位以后,只看了两个他爸乾隆判的案子,都觉得受不了那种惨绝人寰的做法,和最信任的大臣承认是冤案,哼,其实要是嘉庆能看到1百多年后的…算了,咱们聊天就甭说这些了,怪沉重的。”
“可我一点都不知道。”王梦雨说时轻松的微笑,忽然让我对历史积淀出的一切,头一次有种旁观者完全可以淡然面对和冷眼漠视的惬意境界的感觉。
“不知道挺好,太血腥,没意思。”
王梦雨微笑道:“那好吧,我就不请你讲一个了,所以你也别一时兴起就写和政治扯上关系的东西,平常心最好,像那句’落花听风雨,别梦问流连’之类的,又清新又自然,我誊写给宿舍的女生看,她们以为是哪个古代著名诗人的呢,我还开玩笑,说不是出土文物,是文坛新秀。”
我得意中本想着可以假谦虚一下,却眼见着已经到了外语系的楼前,原来开心的聊天总会让距离缩短。我走过去打开自行车锁,拍打着车座和架子上非常松软的厚厚积雪,一边说:“还是我带你到车站吧,这么着快。”
“这么大雪不能带人。”却是上面意外传来的声音。我们都抬头看去,只见孙子琪穿件军大衣,胸前挂着一个包着护套的相机,黑亮的厚底大皮靴大模大样地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走下台阶,冲王梦雨说:“刚才看见你一个人在操场,正好我和系主任在一块儿,要不过去看看你一个人忙活什么了,可这原来还有同学一块儿的,不过大冷天的,你这么半天还没回去呢,难道今天还住学校不成,可食堂都关了啊?”
王梦雨说:“吃饭倒好说,有方便面呢。也本来是想这天儿不好走住校得了,都怪他瞎说些鬼故事,吓得我不敢一个人住了。”王梦雨笑着扒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说,接着说:“反正只好回家了,我还想着要不要罚他一直骑车带我到家呢,而且雪没化的时候不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