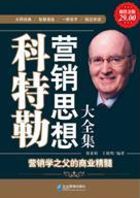吃饭可以把人的距离拉近,可以聊些不随便告诉人的家事。我这是第一次跟凯瑟琳吃饭。之前我们只是同事,泛泛之交。这顿饭后我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在她大四那年车祸过世了,母亲现在也下岗在家。她来澳洲留学的费用一部分是父母的积蓄和父亲车祸的赔偿金,一部分是她在外资公司工作两年的积蓄。怪不得她那么急于找工作。我一直认为新生代留学生的背后都有家里强大的经济支援,只管无忧无虑地上学。不像当年我们,向后看空虚无援,向前望兵荒马乱,一脚踏出国门是死是活全看我们的造化。其实不尽然。
凯瑟琳的情况容不得我慢慢等机会。我现在对她的感情不只是在喜欢、欣赏的层面了,又多了层同情和惺惺相惜。我看到曾经的我也曾经那么的需要帮助。像放电影一样,我在脑子里过一遍当上老板的朋友们:素鸡?听颜然说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他是建筑承包商。一个女生能在建筑行业做什么呢?就算是做文书、记账员,我做过,琐碎繁杂,而且这种位置往往需要全职。找素鸡?不是为难他吗?算了。‘素鸡’两个字在我的脑子里被划掉。钟耘?对,钟耘。他的公司那么大,安排个把杂工应该没问题。我给钟耘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苏珊。她用浓重的越南话腔调广东话告诉我钟耘去了广州,个把月后才回来。我跟她没话说,我特别不喜欢越南话腔调,尾音细高拉上去,听着耳膜被刺得生疼,像听窦娥冤似的,满世界暗无天日,就挂了电话。还有谁可以帮忙的呢?每当遇到难事,我总会不期然想起澳黛丽,我们曾经相互搀扶走过艰难困苦日子的朋友,想到她就想到了大卫。也许大卫可以帮忙?我怎么就没想到他呢?
我给大卫拨去电话。大卫静静听完我介绍凯瑟琳的情况,想了一下说:“安平,你应该早说,前两天我才招了仓库临时工。对不起。”
“仓库临时工?好啊,这工种最适合凯瑟琳。没责任。机动。没时间限制。她想来想不来,由她。功课紧或者考试时,可以少来;放假了,可以多来。你就多加她一个吧,大卫?”我用恳求的字眼但没有恳求的态度跟他说话。忘了他是老板,还当他是多年前的寓友。
“这样吧,我需要人的时候一定找你。”大卫的口气比刚才冷淡。我一听急了,顾不了那么多,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大卫,她就快毕业了,有你的帮忙她就可以把书读完。你的帮忙对她很重要,可能会决定她今后的人生道路。想想我们,当初如果有人帮一把,就不会走得这么辛苦……”
“安平!”大卫打断我语调高亢急速的话语,他也急了。
“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呀!我还没有能力救济别人!”
我没趣地放下电话。我对不起凯瑟琳,我没能帮到她!
过了几天,大卫来电话,问我凯瑟琳介不介意做家庭助理?“不介意。”我自作主张为凯瑟琳做主。
“如果她不介意,我就辞退现在的家庭助理,让她来做。我只需要她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三点半到六点在我家做家务活包括做一顿晚饭。工资是每小时二十块。一周二百五十块。她考试时可以调时间。”大卫这次的口气极为谦虚,像是为上次的冲撞道歉。
我不计前嫌,连声谢他。
为了凯瑟琳,我到大卫的家去,送凯瑟琳去。
从南到北,有两条道可以选择,要么过悉尼大桥,要么走太平洋高速。我选择后者。畏高,畏速度,没方向感─不认路都是我的强项。我害怕走桥,害怕在桥上凌空的感觉,害怕在桥上以一百公里时速与五条车道并行行驶同时辨认路标。走错车道是没有回头机会的,唯有将错就错到下个出口重新找路。走太平洋高速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最保险的选择。我宁可兜远路也不要迷路。
他这白宫我来过一次,当时伙同一大班朋友来贺他乔迁之喜。晚上,一大班人嘻嘻哈哈,吃吃喝喝,我没来得及观赏这大房子。
大卫胖了,更像唐僧了,也少了些早年的稚气。重量与年龄剧增,平添了些中年人的平稳和成熟。大卫看上去稳健自信,文雅中透着精明,应该说很有魅力。男人的魅力来自于他的财力和权力,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当他过了青春期,头发不再乌黑油亮挺拔蓬勃,屁股不再像公鸡一样向后翘起而前面的肚子又不甘寂寞地要显山露水时,财力和权力更显示作用。大卫来到这个人生阶段了。
“你这里不好找啊!我们算是跋山涉水不辞辛苦了啊!”进门我就叫苦。
他的两个孩子也在家里。“壮壮,去,烧水,给阿姨泡茶。”大卫给儿子派工作,大概是想给我显一下孩子在他的教导下如何懂事吧。
凯瑟琳想着以后要跟孩子打交道,就主动跟他们套近乎,跟着两个孩子到厨房里去了。
两层的房子,通到第二层的楼梯从客厅左边靠墙开始旋上去。我靠墙拾级而上,一路看墙上的镶框相片。相片按孩子的成长过程排列,较早期的都有澳黛丽: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她搂着儿子蹲在沙滩上傍着大卫如花的笑容;大卫与两个孩子在后花园抛球玩……到了楼上的书房,里面凌乱,摆满了小孩的玩具。我拿起一把小提琴,看看。我不懂音律,没有音乐耳朵,罗丽莎说俄国人有句谚语形容这是“小时候耳朵被熊踩了一脚。”
“这是壮壮的琴。”大卫一直跟在我身旁。
“为什么是小提琴?”我摇了摇手中的琴。
“开始是学钢琴,半年不到就不肯学了。我说必须学一样乐器,长大了容易找女朋友。女孩子都喜欢懂乐器的男生。他就选了小提琴,也很努力学习。”听了大卫的话,我大笑。如果是澳黛丽,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教育他?
“生意怎么样啊?”我随便问问。
“不好做。中国进了世贸后,澳洲的服装市场就风雨飘摇了。那些欧洲大品牌都在中国设厂,价格卖到跟我们这些无名牌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做不过他们,大浪淘沙,被冲掉是迟早的问题。我准备改做房地产。澳洲的三大经济支柱之一,房地产,经过1990年以来的大衰退,长达五年的谷底徘徊,从去年开始爬坡了,现在应该是入市的好时候。”
三句不离本行,大卫滔滔不绝的生意经,我听得云深雾罩。出于礼貌,我不懂装懂频频点头以示我在听而且与他有同感。抓住他停下来换气的瞬间,我切入:“这么忙,怎么照顾孩子?”
“大的读二年级,小的读学前班,基本上不需要照顾了。早上我送他们去学校,放学我付钱托别的学生家长接回家。我要凯瑟琳三点半来就是为了让他们回来家里有人。以前的家庭助理管接孩子放学。家务事是洗衣服、烫衣服、洗碗吸尘等等。晚饭我让附近的餐馆送餐,两菜一汤,一周五天,120块一周。小孩吃了两年,腻味了,我希望凯瑟琳能做一餐晚饭,简单点也无所谓。”
我很快地扫一眼整个环境。偌大的一个厅,衣服,板球具,小孩单车,电脑,电话,书包,作业本,钢琴等等,林林总总,随意待在不恰当的位置上。我嗅到一股缺少女人的味道,很想打趣他:“像你这样的钻石男,给孩子找个好妈妈,应该不难吧?难不成你真是唐僧轮回?”话到嘴边被咽回去。我们虽然是老朋友,但关系还没近到可以关心彼此的私生活。不适当的关心就变成好奇窥视,会讨人厌的,弄不好还要招人鄙视。
“素鸡也做房地产。他是承包商,规模不小哪,你跟他有没联系?”我没话找话,东拉西扯。
“以前很少,最近我们见过几面。我最近在西区买了一块地皮,准备盖仓库群。我想把工程给素鸡做。盖仓库的材料不讲究,我准备从中国进口。素鸡只负责施工。”
呵呵,这两个人,女人,喜欢同一个,生意,也做到同一行业。“你们上辈子是双胞胎吧?”
“喔?哈哈!可能吧。”大卫开始不明白我的意思,反应过来后,自嘲地苦笑两声。
“‘中国造’已经侵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毛细血管里了。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欧洲名牌服装、手袋、鞋袜,日本的名牌瓷器,英国的名牌瓷器等等全打上‘中国造’。现在看来连房子也要‘中国造’了。”我们聊着,沿着楼梯拾级而下。
“所有打上‘中国造’的商品在价格上都要便宜百分之三十甚至五十以上。也劣质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以上。”大卫附和我。
“什么东西不经用,我的同事就说是‘中国造’。他们以为幽默,我却觉得尴尬。”
“你放心,我建的仓库不会不经用,我可以保修一辈子。”
说话间我们到了楼下,看到壮壮和平平已经和凯瑟琳玩得很熟了。喝完咖啡我们告辞,平平虽然没说什么,眼神却流露出依依不舍。临走前,大卫和凯瑟琳说好了上班的日期。
两个孩子跟着父亲送我们到大门外,一直看着我们的车开走。孩子是乖巧的也是寂寞的。澳黛丽是走了,却留下了她所有的风景。
我在努力地适应新工作。悉尼的公司只负责筹钱,实际运作公司在北京。公司设计师迪荪为公司重新挂牌赶写招股书,他晚上来上班,到凌晨三点回家睡觉。董事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移民,会讲但不会看中文。他长住中国。中国的股东都是他拉来的。CEO Mayo去了北京。白天,办公室里只有我和妮娜。妮娜喜欢买衣服,上班时间她也会拉我陪她去买衣服。
我永远不会穿得比她时尚。我给自己规定两条纪律:1.她永远比我时尚;2.如果哪一天我比她时尚了,就服从第一条。感觉上她是我的宠物狗,只要理顺她的毛就行了。
凯瑟琳偶尔跟我通电话,她告诉我,每次下班,大卫都开车送她到火车站。
半年后,凯瑟琳毕业了。
“怎么样?什么时候去美国?”她请我到悉尼塔顶上的旋转餐厅吃自助餐。餐间,我问她。
她恢复了原来的清秀模样,神态悠然自得,语速快缓适宜:“去美国?”她停住手中的叉和刀,眼神疑惑。
“记得你告诉过我毕业后要到美国。”
“哦,你还记得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释然,“我现在跟大卫一起─工作。他现在很忙,大陆悉尼两边跑。我除了管他公司的账,还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她在“工作”两个字前面顿了顿,像在斟酌用字。
“……”我脑子慢,没听明白凯瑟琳的意思。
“我们准备结婚。”我们静默一会儿,吃东西。凯瑟琳又开腔。
“谁?”我咽下口里的食物,问。
“我和大卫。”
“哇!恭喜你!”我突然提高声音,周围的人都看向我。原以为凯瑟琳请吃饭是为了庆祝她硕士毕业,原来是告知我她的婚讯。
凯瑟琳是位好姑娘。她配做澳黛丽的接班人。
我回家就打电话给颜然,告诉她大卫的婚讯。
“男人有钱有事业就不愁找不到好老婆。女人有事业大多数是因为没老公。”颜然听了,发表了一番“颜子曰。”
生活的平淡,我不自觉成了小广播。我打电给碧姬,告诉她大卫的婚讯。她用毋庸置疑的语调说“嗨,她还不是看上他的钱!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这么年轻就当两个孩子的后妈。要是我,多少钱都不干。”
我脱口而出:“你怎么这样看别人?你又不认识她,怎么就断定她是为了钱?再说,你有过这样的选择机会吗?”我生气了。我不喜欢她这样说凯瑟琳,凯瑟琳是我的朋友。
“你有权力说你的看法,我也有权力表达我的看法呀。”说完碧姬把电话挂了。
平生头一次被别人摔电话,为与自己毫无相干的人事。
三
接到公司要派我到北京查账的通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颜然家,看她有什么要捎给猛男。我已经半年没见颜然了。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上,看着颜然做咖啡。厨房是开放式的,厨房与厅间是一堵一米多高的曲尺形吧台。我在吧台的外面,她在里面,做好了意大利泡沫咖啡放在吧台上,推到我面前。早年间她在意大利人的咖啡厅打工,做得地道的意大利咖啡。来颜然家我必喝咖啡。为这,猛男开我玩笑:“你来我家不亏,一杯泡沫咖啡三块半,你来我家的汽油费用不了这么多。”
我翻着吧台上一本Donna Hay的烹调书。我对西餐不感兴趣,电视上她的节目我都转台。现在跟颜然闲聊,手闲不住。“他没碰你?”我从Donna Hay的书中抬起头来看住颜然,问。猛男回国一年多,其中回来过一次,就是元旦回来一个星期。我知道颜然为猛男郁闷,
“没有。”声音是委屈的。
“你怀疑他有人?”我看着书上色彩鲜艳的插图,漫不经心地问。这本烹调书主要是教做沙拉,Donna Hay的沙拉不外乎松子、小番茄、澳洲豆苗,放在碟子里,红是红,白是白,绿是绿,煞是好看。老外的菜好看比好味道重要。“做老婆不容易,要管住丈夫的身体也要管住丈夫的心。”我继续说,手还在翻Donna Hay的书。跟颜然胡说八道惯了,今天也不外乎如此。在我看来,怀疑丈夫有外遇是普天下妻子的通病,只要还爱着就会有怀疑。“没想到你这么爱他。”我继续说。
“我怀疑他,不是无中生有。我每次打电话给他,都是同一个女人接。”
“是他的秘书吧?”
“他是这么说。”颜然看向我:“难道秘书跟到家里去?”
“你把他的电话给我,到北京,我去看看他。”对于夫妻间的问题,我没资格发表什么意见,甚至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在我看来,夫妻吵架就是耍花枪,是一种交流方式。颜然这次跟以往不大一样。一改往常的玩世不恭,神情肃穆。“这次动真气了?”
“行,你去,看看他耍什么花招,回来告诉我。”
“那是当然。”我几乎给她发誓,“放心,猛男不会怎样。他不敢。”我不能免俗,讲些肤浅的安慰话,听在颜然耳里,更像挖苦。
颜然看我一眼,想讲什么,又不吭声。
“别这样呀!看你这个样子,我都不敢结婚了。”
“别吹了。”颜然笑了。
看着颜然笑,我对这次去北京有了重大的责任感,暗下决心要帮颜然摆平猛男。
我跟迪荪一起去北京。他去是要写招股书,我去是为总会计师核实年度账目凭据,为向澳洲证券公司提供年度财会报告所用。
我只管核实凭据,别的事务包括应酬由迪荪应付,工作不繁重。我找个下午去了趟三里屯猛男的酒吧。的士把我带到酒吧门口,我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里屯?”冷清的街道,露天桌凳蒙着一层灰,太阳伞收着。“这伞什么时候用?”我好奇,“难道晚上才用?挡月光?”
我一脚跨进猛男的酒吧,环顾四周,一个客人都没有。柜台上有个女孩,我说明来意,她让我坐下稍候。我就着身边的桌子坐下。不一会,猛男从柜台后面进来。
“你好!”我马上站了起来。
“你好!坐、坐。”猛男大步向我走来,挥手示意我坐下。客随主便,我坐回原来的椅子。
“喝点什么?”猛男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他个儿高,腿长,为了坐得舒服,他斜着身子坐。
“卡布奇诺吧。”我知道三里屯的酒吧出名,来之前公司里的人跟我说了。为了省事,我还是要个简单的。
“这里的咖啡没悉尼的好喝。”猛男提醒我。
“你还记得呀?”我半开玩笑地说。有两年没见过猛男了,他见老,脸色苍白,眼睛浮肿,鼻翼两边出现两条沟,上眼帘有下坠的趋势。人比以前胖,中年人的魁梧。他一只胳膊肘子支在桌子上,手里拿着一串檀香念珠,估计平时戴在手腕上,现在褪出来拿在手里,他跟我讲着话,大拇指不停地一粒一粒拨佛珠。另一只手臂被他的身体挡住,看不清楚,估计是放在膝盖上,只见那手臂有节奏地上下抖动,估计他抖脚的缘故。好像流行带佛珠,不管男女,不管是否信佛。
“我们这里的牛奶没澳洲的好,做不出那味道来。”
“你的生意怎么样?好吗?怎么没见有客人?”我头扬一扬,看一眼周围。
“现在是白天,晚上才来人。生意还可以,就是累心。”
“这年头干什么不操心?”我觉得他这话讲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