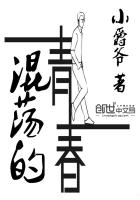回到家中,东启脑念一起忍不住伸手在背上挠痒,刚才的情形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就觉的浑身鸡皮疙瘩,他打消念头,不去帮助那位生死不明的刘先生了。
本来两者之间就殊不相识,仅凭一段话就相信别人自己都觉得够傻的,那血淋淋的场景把东启狠狠的敲打了下,这些高能人物处事自己最好别逞能,卷入漩涡就小命不保,哪怕想为常伯出口气也得将命留下来才行。
天已经黑了,黑夜里的清河城与往日大不同,纵横交错的夜街比平日多了许多火团,那是巡防司的人们打着火在巡夜,今日接到叛军起事,欲图谋逆的情报,过去荒废下来的防御工作也必须重操旧业了,清河是远东大城,必是叛军的夺取的目标。
城门大关,东启可以看到一些大户收拾细软准备出城北上却被拦截下来,因为国法有律夜间不得开城门,尽管这条律令前几十年都未认真执行过,但这会是要来真的了。
正在家中吃着面饼充饥,华枰白天出门自今未归,东启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也无事可做。
久违的敲门声沿阶梯传来,东启闻之打开窗户,见到下方的华叔正抬头看,正招呼着东启下去开门。
华叔的面色似乎不太好,从进门后就略带苦涩,东启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么华叔?”
华枰缓缓的坐在藤椅上,这般颓废模样东启只能想到两种结果,一是他出门被人打了一顿,或者是他已经破产。虽然不太可能,但今天东启实在想找点好笑的事冲冲喜。大叔好像想到什么了,他飞快的起身,纵步跑进房间中。
一刻钟后东启走进门框,却见到华叔挥舞着手臂在桌案上龙腾虎跃,他前面放着几个信封,笔架上的毛头也是黑润润的,看来他是在写信,东启心说那位平日懒懒散散的华叔也有看似健壮的时候,至少那股想把纸业写穿的气劲他还是看得出来的。
“华叔,你到底怎么了?”从一开始的好奇现在他已经但心了。华叔挑了挑眉头:“说了你也不懂。”
我去,你说啥我还真懂啊!东启心下为自己愤愤不平,直接不鸟他了。
华叔拿起几个封袋走出房门,二楼的窗台涌进寒风,让人衣襟浮动,餐桌上还放着吃剩下面饼渣,华叔好像终于回神了:“你吃饭了没有?”
“嗯……吃了些饼干和水,现在不饿。”
“等等。”他从怀中掏出了些银钱,随手抵到东启手中,“出去外头吃一顿吧,不要走太远啊。那二街上的面馆你还记得吧。”
东启苦笑:“叔啊。今晚是没人开张的。”
是啊!今日得知叛军造反的消息,整座城池都在加紧戒备,晚上谁敢随意开门,门外一队巡防军打着火把应景的从门前走过,华枰忍不住靠到窗口观看。
“抱歉呀!我现在有事再出门下,你先去休息,晚点回来我做点夜宵。”
“可是外头门户四闭,华叔你也犯不着现在出门找信客吧,在怎么快别人也是第二天出门。”
华枰呵呵一笑:“自然不是找普通的信客了,我想去的是猎火武馆。”看着东启不说话,又说:“这个你们是不清楚的,我先走了。”
猎火武馆是城内相当有名气的雇用机构,连东启这样成天呆在小塘堡的都听说过它的大名。
猎火和其他的武馆不一样,他不只是一间武馆,也在其他多种行业中涉及,门员众多,来源混杂,有宗派的、军伍的、还有还俗的武和尚,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江湖能手,有些人也把他们当镖局,或雇佣力士做护卫,当然,只要雇主出得起钱。
也许猎火武馆的人也有兼职当信使的呢,东启不知道但他相信那个传说中鱼龙混杂的地方肯定有这种日常职业,外面已经是晚上,如果给的起钱,恐怕那些人裹着睡袋也会信送出去吧。
在这雷雨般的动荡下,清河府的居民抱着忐忑的心进入梦乡。
清晨微微亮,远方天际线慢慢绽起一道白光,星空开始褪色,万物无声。
守职的门卫打着呵欠与几位僚友将城门打开,对于过去城门通畅,彻日不闭的情况而言,这表示他们以后将多出一份工作了,所以他们的脸色并不是很愉快。
一个年轻的军士正忙活着,忽然停顿了下,天刚亮的时候,一般而言都是寂静无声的,但他却灵敏的听闻到来自远方的嘈杂,其他人似乎也有了与其一样的感觉,纷纷向城外看去,那尽头慢慢升腾起一抹黑色。
东启坐在阁楼上,他昨天晚上睡得不好,眼睛带着几丝黑框,因为他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梦到那死状惨烈的尸场,这明明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东启心中虽然被吓了一跳,但也没什么不安,可是他再次睡下的时候,居然看到那个快断气的刘七,不知为何一见到那个人东启反倒内心喘喘,两人间说好的事东启却半途退却了,其实现在他应该把见到的情形跟刘七说下才行,又或者找个大夫给其治疗,但他就这么将其抛掷脑后。
他娘的又不是圣人,自己的事都不能把握又干嘛烂好人去在意其他的,我的良心有那么大不成。东启心中说着,那股烦躁感也渐渐弱下去了。
忽然城池中炸起了浪花,纷乱声如海浪卷席上岸,能将东启从窗台冲下来。
无数门窗打开,露出穿着里衣眨着睡眼一脸困惑的市民,东启这里能听到无数人的吵杂声,一般只有盛大的节日才有这种景象,发生何事了?东启踩上栏杆,整个人挂在窗口看出去,却见不着什么。
但他低下却出现了许多人,一些人茫然四顾的走上大街,他们似乎历经风尘,裤脚皆沾有污渍,或多或少带着包裹,好像被赶出家园的落户。
“你们是什么人?躺我门口干么?拉屎啊!”打开窗口的市民对下方一个蹲坐的大汉嚷着。
“来自洪县的……”
“发生何事了?”华枰起来看到这一切,问了下东启,他能知道什么?摊开两手示意下无知。
我去看看吧,华枰这么说着,直接下去跟人交流去了。
过段时间,他回门皱着脸,东启询问什么原因。
“这些人是灾民。”
“什么?灾民!”东启想到了不妙的结果。
华枰叹着气说道:“叛军已经打到了贡江边上了,那个叫什么杨、杨其昌的,开始带人打上来了。江边两地各县城遭遇战祸,都携家带口的往上跑。”
“糟了,那我们怎么办?他们肯定打到这里来?”心下估算了下贡江到清河城的距离,东启惊讶的发现两者相距竟然不到百里,考虑到清河作为远东一座著名城府,不用说都知道叛军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们这里了,一两天可能就打过来了。
“去收拾好行李。”华枰思索许多终于打定主意,这地方估摸是待不下的了,且不说城池防御,坐镇的城主还不在这里,他必须考虑到孩子的安全,而且战报上来可能城门封锁,到时候谁也出不去。
“但我们能去哪?”
“记得我们上回去的地方吗?”
“高城?”东启想到那里,那座飘着古风的城市和那外糗内丽的鉴武堂。
整座城池算是乱了,无数遭遇战祸的难民蜂拥云集至城内,其中还有逃跑士兵和将官,城主府也是一样,鉴于文武最高长官胡申与司空志都上山没了影,代理的田儒对政务也不熟悉,能否挡住叛军的攻势大家都没底。
“为什么胡大人那边还没有回信?”年迈的田儒看着堂上的诸人不解的问道,自接到叛乱的情报后,他们已经派遣了好几只队伍进仑海山脉,按说祭天的人也才走不久,急赶慢跑怎么着也该追上了,却毫无音讯。
“田大人,圣域之中凶险不等寻常,我们派去的人哪有七宗门大的本事,会耽搁时间也迫不得已。”说此话的是一位体态肥胖的中年,他是胡申的属官黄理,现在能主事的其中一人。
“那就再派人过去,无论如何定要通知特使大人,他们可是有着众多天师跟随,还有强劲的三宗四教,我们与他们联合定可一举击敌。”
一举击敌?说得轻巧,黄理苦笑,他们已得知南山的杨其昌带领数万叛军北上进攻,这其中肯定会不停的整编叛军降军,势力定在不断壮大,而他们这边的加上下辖的驻军,人数竟不到万人,自保都成问题了,哪有力气进攻。
当前之际,最应该是稳住阵脚,等待王朝的增援部队,但是远东离国都太远,哪怕他们用最快的速度传信,从接到情报到派出兵马也要十数天,到时估计敌人都打进城内了。
田儒年迈却还未老眼昏花,知道这个问题,现在讨论起来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今日接到消息,叛首杨贼已过贡江,剑指我等清河,短短数日之内连失五城,守军毫无战意,王师又需要时间才能赶来,这样下去我们也逃不出去。诸位有何方案,说给我们听听。”
这下就热闹了,堂上的人个个张口,有的主守,有的主攻,但主守的意见更大,理由很简单,敌众我寡,而且军备荒废,军士无战力,若是主动出击一旦全军覆没定然全完,若是如此还不如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补给,坚守城池一段时间,朝廷的增援军队必然到达,到时使以全力必然致胜。
这个理由似乎有很大的说服力,从事黄理也主张守,但一个更大的声音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懦夫!叛军攻至城下,我堂堂大朝更应该勇猛出击,震慑敌胆,如果连打都不敢打,岂不是增加叛军的气势了。”
说这话的看装饰应该是个武人,似乎不比其他人高贵,确实如此,此人仅仅只是个都头,平日里的任务也就是练兵,没什么话语权,但他的名字叫司空庭,他练的兵隶属与清河守备,他还有个哥哥叫司空志,有这关系说话气力自然大。
“刚才说的,守军毫无战意,一触即溃,可叛军打得都是吃惯太平粮的太平军,而且情报之中不是说得很明白了么,我军都没有做好防御准备,才那么点人如何能挡着敌人的攻势,而且其他有战力的雾谷驻军和我哥手下的兵将都还没打过呢,怎么可以简单的就示弱了呢!就此判定我军不能打你们就不觉得太过草率不成。”
这话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一下主守的就有些举棋不定了,田儒老人也这样想。确实,敌人也不是百战雄兵,说到底也是群乌合之众,如果就此后退等其壮大势力必然更加难对付。
况且平叛,某些人都会被追究责任的,要是他们因此被落个资敌的名头,谁也跑不了。堂内诸人又是一番众议。
“好吧,老夫明白了,光守不行的了,但是我们兵力不足,也没有余力进攻,杨贼看其攻线必然是清河,定要寻其他府县增援,城主府也会出资招募力士,一切等援军到来再议。”田儒说完便缓缓躺下,其他人也陆续离开。
只有黄理没有走,两人很有默契的闭口没谈。
良久,田老人才开口:“步场也没能知道城主大人的消息吗?”
“是的大人,毕竟晚上几天,不过应该快了。”
“若是明日敌军到来,步场能否有战力应对。”田儒抬头看着他。
黄理闻之苦笑:“大人呐!步场说到底也是一帮探子而已,如何有力气对付大军,再厉害的高手在千军万马面前都是徒劳无功的。”
田儒哀叹一声,他对这些事了解不多,其实按他的年纪应该退休了,却好死不死碰上谋反这等事,道了声下去吧,就闭目养神。
黄理点了点头,他看着地板没看他,静了一会就出了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