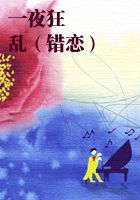“务必守住鹿城,如果守不住,他这个督办也就不用要再做了。”
沈怀信不怒自威,电话那头的安格对着话筒肃然起敬,当即立下军令状: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沈怀信放下电话,后面的话藏在心里。城亡了还能再夺回来,人若亡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他没说,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此次的对手不是别人,偏偏是陆承恩。当年陆承恩带着胡风寨助他保住鹿城,稳住了辽东,今日,却要从他手里拿下鹿城,多么戏剧性的一幕。沈怀信重重的靠在椅背上,整日的打打杀杀,何日才是尽头?
此时此刻,沈怀信忽然觉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从前的他,以为掌控了京陵城,掌握着对外的话语权就可以掌控一切,而现实却给了他相反的结果。他因为厌倦战争而开始厌倦自己,从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妙灵就在咫尺之远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做着翻译的工作,无论多么复杂,从无怨言。三天前,她终于成了他的妻,白纸黑字,他本想还她一个隆重的婚礼,她却执意不肯,两人仅在几个好友的见证下,于教堂宣誓完婚。当他再次拥吻妙灵,才真实的感受到妙灵的存在,这一次,是切切实实的,不是梦境,更不是虚幻。他暗自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可以比她先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比他亲自去照顾妙灵更让他放心。
沈怀信漫无边际的想着,眸光流转,回神的一刹那,刚好对上妙灵探究式的目光,四目交叉的瞬间,心意共鸣。
“你似乎并不紧张此次的战事。”
他倒吸一口气,叹道,“打的多了,自然不当回事儿了。”
妙灵噗嗤一笑,“我看不是,都说物极必反,你心里有紧张的人自然会紧张此次的战事。况且,这次对战的人是承恩,不是别人。你们对彼此都太熟悉,赢起来并不容易。所以,你的压力胜过从前打仗时的百倍。所有的情绪都压抑在心底,你不说,却都体现在眉间了。”
怀信纳闷着揉搓着眉心,嘴里嘀咕着,“也就你看的出来。”
“不过,你这招连同西北军一同抗徐的对策,却是对付徐正中最好的对策。”
怀信迟疑了会,“你觉得西北军会答应吗?”
“除非他们是傻子,甘愿被徐正中收复。”
怀信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那你认为陆承恩会怎么打这场仗?”
妙灵略一沉思,正色道,“他是个天生的将才,打起仗来善以奇兵制胜。如今,咱们和西北军联盟,对承恩来说,等于又是一场以少对多的战役,我想,他会用离间术。”
“离间术?”怀信颇是意外,“你认为他会挑拨西北军,在关键时刻倒戈?”
“没错。其实我们都非常了解西北军,他们最是无常,只要是有好处,他们就不可能不要。咱们许他三个市,如果徐正中愿意,可以许他更多。承恩又善说服, 所以,我们要提防西北军。”
怀信思忖着,觉的妙灵的话不无道理,防人之心不可无,无论是西北军还是他自己,若不是迫于形势,是绝不会跟对方联盟的。
果然,西北军前脚跟沈怀信签了联盟协定,共为一家,后脚就提出借道古州。古州就在鹿城边儿上,属于唇寒齿亡的地理位置。沈怀信多了个心眼,知道西北军想跟他玩个假道伐虢,表面借给他用,实则暗地里做足了准备,结果,西北军的阴谋没得逞,反倒因统帅猝死,引发内部动乱。
沈怀信随即派冯健出兵西北,以镇压叛乱协助西北军之名攻进西北腹地,又收买西北局副将,以作内应。里应外合下,沈怀信顺利拿下西北,再无西北之患。
陆承恩得知沈怀信拿下西北,此事对自己颇为不利。却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原本,他也没想跟沈怀信真打,所以才屯兵到鹿城城外,仅是两天一小打,三天一骚扰,不想竟猜错了沈怀信的心思,反倒给了他喘息的机会,失了先机。徐正中一个电话打来,劈头盖脸就训斥他一番,陆承恩也是委屈连连,怨声之下,另阿九和小四儿分别带一支部队突袭鹿城的左右两翼。安格不防,被陆承恩接连拿下两个小镇。
沈怀信闻讯,派兵支援鹿城。不想,徐正中另外派心腹李垚出兵东安,好在沈怀信留有一手,固守东安而不破。
徐正中本想用一个月的时间拿下辽东,不想却拖到了三个月仍旧拿不下来。此时已经步入冬季,辽东乃苦寒之地,陆承恩的兵多有不适,也没带那么多御寒的东西,手上和脚上冻疮滋生,握着枪的手都冻得无法灵活使用,更别提打胜仗了。
小四儿和阿九接连谏言,此仗不可再打。陆承恩一直拿不定主意,决定暂停攻城。
巧的是,李垚那边被沈怀信打的落花流水,没等他们拿下东安,反倒被沈怀信南下夺了两个城。徐正中气急败坏的调回李垚,陆承恩,整修以待。
这一仗沈怀信虽然胜了,却也是元气大伤,战线拉的太长,又要应付左右两头,赢的并不轻松。
才进了十二月,就下了一场雪,雪不大,一夜间将京陵城变了个模样。皑皑白雪下的京陵城有着说不出的孤寂,又好像是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一大早却还要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梨园的枝杈上也蒙着一层银白色的新衣,一尘不染的梨园,寒风过去,漫天雪花,千树万树梨花开。
妙灵欢喜的紧,也顾不得冷还是不冷,棉衣也没穿,就跑进梨园里去。地上蒙着一层及踝的学,踩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特别有感觉,让妙灵喜欢的感觉。
妙灵就这样漫无目的的在雪地上踩着,兜了整整一大圈,双颊被风打的红扑扑的,双手也是,可却不觉得冷,心里暖呼呼的,甚至还透着热气儿。
视线里忽然走进一双黑皮鞋,她微微一愣,不过抬头的一瞬,便被一双强而有力的手拉入怀中。坚实YING挺的胸膛,温暖无比的狐裘大衣,从脖子暖到脚踝。
双手环抱着他的腰,就那么没心没肺的靠着他的胸膛,细细感受那熟悉的气息和心跳,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这么冷的天,居然就这么跑出来,真是个孩子。”
怀信那略带着责怪的语气在妙灵听来却是如此的宠溺。
她闭上眼睛,也不回答,只是紧了紧手臂环抱他的力度。
妙灵的小性子在怀信看来实在可爱至极,原本就该这样,天知道,这样的妙灵才是他一直盼望的模样。
怀信的下巴轻柔摩挲着妙灵的头发,“我知道你喜欢这样的雪,喜欢这样的园子,但我却不能不管你的胃。”
妙灵先是一怔,脚下忽然腾空,身子一倾,整个人都被他抱在怀里。
沈怀信不由分说抱着她回到卧房,暖气扑面而至,被冻得发僵的手和脸慢慢的有了复苏的迹象。
怀信亲自用双手帮他捂着脚,揉搓着让血液慢慢的沸腾。
杏儿推着餐车进来的时候刚好撞上这一幕,忍不住偷偷的笑。妙灵见状,立刻羞红了脸,“噌”的抽回了脚,使眼色不让怀信再揉。
怀信看看她,又看了看门口的杏儿,温和道,“行了,下去吧。”
杏儿掩着嘴偷笑离开,怀信目送着她好一会儿,继而端起小米粥坐到床边,舀起一勺喂到嘴边。
妙灵忽的想起他的手才刚碰过她的脚,忍不住偏过头去,一脸嫌弃。
“嫌弃我?”怀信嗔怒道。
妙灵忍不住笑,“瞧您说的,我哪儿敢嫌弃您的手,我是在嫌弃自己的脚。”
怀信突地探身往她脸颊上亲了一口,妙灵不妨,被他占了个便宜,脸上更红了。
怀信就势凑到她的耳畔,软软的湿湿的,“我不嫌弃。”
同样的清晨,陆承恩穿戴整齐准备去跟徐正中请罪,皮靴有力而有频率的在地板上噔噔的响,上了三楼,左转,顺着长廊进去,在濒临尽头的时候从徐正中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句尖锐的略带着负气又任性的声音,那意思就好像是在打赌,虽然赢面不大,却依旧要在声音的响度上搏回一局。
“我心意已决,若是拿不下,我就跟你姓!”
跟你姓?走到门口的陆承恩不禁为此愣了一下。
还没收回神儿,迎面撞上一个人从里出来的人,怒气冲冲的,一头撞到他的肩膀,许是撞的不轻,那人捂着额头斥道,“哪个走路不长眼的,敢撞我?”
陆承恩正为难,是不是该告诉他,他就是那个不长眼的,就听对方不怀好意的怒道,“你是谁?”
我是谁?陆承恩略微一蒙,迅速收回了神,又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陆承恩。”
那人斜睨着他,恍然大悟似得露出一抹诧异,“原来你就是陆承恩。”
不施粉黛的脸蛋上映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樱唇微启,利落的短发与一身笔挺军装搭配的恰到好处,脸上的倔强与稚气略有些违和,但不管怎样,是个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