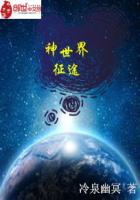陈王府的首领侍卫名叫王川周,追随陈王已是十几年,多年前便也与秦蓦相识。第二日秦蓦去时,正赶上他一身戎装,腰悬大刀,在府门外巡视,一见秦蓦到来,二话没说,也未及通报便即指令守门的侍卫打开王府大门。秦蓦想着此举到底破坏王府规矩,便即拦住,这边歉然谢绝他好意,只道出来意。
“王大哥,王爷在府里么?”他问道。
那侍卫黑黝黝的面庞,在灼人的日光下更有亮色。他见秦蓦时,知他与陈王素来交好,加之对其印象极好,索性未经通报便欲打开府门。但这时听到秦蓦问陈王,便诚然回道:“说真的,王爷还真不在。”
“不在?”秦蓦微有诧异,颌首淡笑道:“劳烦王兄了,那秦某先回了,若是王爷回来,请你得空转告一声。”
那侍卫微微犹豫了一瞬,继而道:“秦公子,王爷这阵子大概都没法子回府了。”
“哦?”秦蓦心中犹疑,面上笑说:“那好罢,我过些日子再来。”
“秦公子!”那侍卫首领见他转身便走,忙步下石阶,追了过来,道:“公子莫怪,卑职说的是真话。”他说着,四下看了看,低声道:“太子监国,王爷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可是……你是说王爷他不在洛陵?”秦蓦疑道。
“还没动身,”侍卫叹了口气,“不过也是早晚之事。”他说罢,见秦蓦不语,续道:“秦公子,卑职跟随王爷十几年,知道你是他信得过的人,本来我想找个时间去你府上,现在你来了,就这么和你说了罢!”
“王大哥……”秦蓦见眼前黝黑的汉子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不知说些什么。
“卑职身份低微,这话本不该讲出来,”那王姓侍卫竟是一副极忐忑的语气,令秦蓦深觉蹊跷,按说武将理应直爽而言,然而这人今日竟如此支吾,反常之极。
秦蓦疑惑地看着那侍卫,只见他暗暗舒出一口气,道:“太子监国,只怕不容我家王爷。”
他声音很沉,而秦蓦的脸色渐渐凝重。
“王爷没这么说过,可卑职这么些年也见多了,”他顿了顿,复道:“公子,王爷信任你,万一王爷日后离京,你可别放着陈王府不管不顾啊!”他说着,眼睛发红,竟是极为激动。
“王大哥……”秦蓦见他神色不变,而多年来便是极忠诚之人,复道:“秦某承蒙陈王千岁提携,若当真有那么一日,定当尽全力保陈王府周全!”他说着,双手拱起抱拳,斩钉截铁地说道。
王川周看着他跃上马背,疾奔而去。他站在陈王府门口,身后虽伫立着一众侍卫,但心中空隙实难填平。他身为武将,虽不通诗文经史,却也知道何为岌岌可危。
身为陈王府的首领侍卫官,他并未向秦蓦透漏陈王的行踪。但他言语中所传达出来的已是沉重的危机感,无需再多言了。
太子向来与陈王不睦,朝野尽知。
与未来的天子矛盾重重,是极不明智的行为。但对陈王而言,或许人人皆知的道理他亦清楚。或许,这不只是一种固执的行为,而可以视之为一种选择。
“选择博得贤王之名,博得朝野乃至天下的敬重,以同无能而偏狭的储君之间的矛盾取悦天下人,赢得身前生后名。”这是楚魏对于陈王一直以来的评价。
苏溪在微有颠簸的马车中,思付着楚魏的这句话。
他说:“如陈王这样的人,若不是如他所想那般工于心计,便是大大的正人君子。”
“可是,试问哪个正人君子会与自己的侄女纠缠不清?”
她依照楚魏信中之意,前来拜访陈王妃——曾荻。
前日她叫人递送了书信,相询何时可以前来拜见,而曾荻极为得体地亲自动笔写下了回信,差府中五品家将送到楚戴侯府。
楚魏并未言说细节,苏溪想着,或许他此举的目的,只是拜见而已,至于说些什么,不足挂齿。
既然如此,楚戴侯夫人拜见陈王妃之事,理当宣扬出去,虽不可大张旗鼓,但到底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苏溪今日的车驾极尽显赫之能事,金丝线围拢的外围,悬垂着赤金走珠的车帐,而车盖上的璎珞,更是数也数不清,车驾由四匹纯白色的高头大马拉动着,马儿身上裹着金色的甲胄,而车驾之后,精锐的卫队快步跟随着,个个腰悬宝剑,昂首阔步,一路行来极为引人注目。
紫真坐在她身旁,时不时撩起一旁的车帘,看到外间行人瞠目结舌的模样,不禁在车帐之内笑出了声音。
“笑什么?”苏溪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
“小姐,”紫真将车帘放下,“咱们这马车比得上罗筝大小姐了罢!”
苏溪别过头来,漠然看着她,直至紫真脸上的笑容渐渐收起。
洛陵人人皆知,罗家小姐每每出行,所乘坐的必然是这般奢华无比的车驾,而且所到之处皆是大张旗鼓,说来,紫真所说是没错的,毕竟苏溪鲜少这样张扬。
她并不知道苏溪的用心,只单纯地以为她是忽然想通了。
到时,正是午后申时。
苏溪一身平常的青色长衫,外罩着月白纱袍,与这样奢华的阵仗颇为不符,但好在她生来一副出尘气质,竟也看不出有何不妥。
她在王府侍婢的引领下缓步走去。
陈王妃曾荻是个刚过三十岁的少妇,苏溪只觉在见到她那一刻,方知何为倾城之姿。
苏溪的相貌已是令人惊叹,但在陈王妃面前,她竟有自愧不如之感。
曾荻身形高挑,眼底卧蚕,说话时声音极是婉转,仪态雍容,一见便知出身不凡。
“怪不得……”苏溪想到了陈王与平伽郡主之事,抬眼见到曾荻眼梢隐藏的愁意,微微懂得。
她只在陈王府逗留了一小会儿,离开时,也不过是申时而已。
楚魏交待之事算是完成,她完全依照他所说而行之。
她坐在奢华的车帐之中,冥思中,渐觉可笑而可悲。
也正是同一日,太子韩昇在朝堂之上公然就通柒一带水利之事对陈王大加苛责,甚至将陈王提交的奏章以衣袖挥落。
朝野震惊。
也正是同一日,平伽郡主顾不得王妃曾荻的阻拦,径直闯入了陈王的书房。
陈王微高的眉骨紧紧聚着,但她的闯入并未使他出现愠色。
“叔父!”她尚未觉察到陈王隐有忧色的神情,便急急走了过来,“太子欺人太甚,我看你……”
话未说完,陈王侧头看了她两眼, 摩挲着手掌,道:“皇上病重,太子监国理所当然。”
“皇上的病好不了了!”平伽郡主清澈的眼眸中聚满了愤怒,“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叔父,你为什么要忍他?”
“本王说了,”陈王冷眼看着她,“太子监国只因皇上病重。”
平伽定定地盯着他,过了几瞬,她忽地转了身,复又转了过来,脱口便道:“叔父!就算不是皇上病重,太子他继位也是早晚的事情,现在他监国就敢这么对待你,日后说不定要怎样呢!”她一向爱惜陈王,此刻只觉怒不可遏,连语调都改变了。
“伽儿,女孩子别议论朝中政事。”陈王面色沉重,但说出这话时,语气却是极温和。
“叔父!”平伽冲口而出,“你明明都明白,却就是没有半点行动。”她不停着眨动着双眼,语速渐快,心中因愤懑不平而渐起的焦灼令她痛苦不已,她在犹豫着,犹豫着要不要将楚魏及一众贵戚的拥立之意告知她的叔父。
她看着陈王,想到这件事,心中不禁砰砰狂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