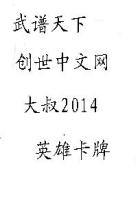王自成狠狠眨了眨眼,将泪水挤出去,再将未流出的泪水挤回去,声音渐渐变得寒冷:“不管是军令还是处罚,都来的仓促而迅捷,可此案中关于老八旅的重重疑点,却并未有人提及或深挖。”
“为什么原本游击目标在额尔古纳河的老八旅会偏离方向,反而去了连天城外?为什么在一次普通的游击任务中会碰到数倍于己的敌人?为什么原本应该寸步不离金帐王庭的金刀游骑兵会突然出现在王庭之外的连天城......而在事发之后,为什么整个国朝,上至天子,下至军机院,会选择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对这个骇人听闻的大案进行处理。最重要的是......关于此次事变中的所有卷宗资料,筑龙城没有丝毫的记载!”
王自成看着楚敦煌,问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楚敦煌沉默片刻,答道:“知道,这意味着,真相可能仍旧在被掩埋着!”
“对!”王自成握紧了拳头,凌厉道:“真相,我想要的,就是真相!我不信真相是所谓的老八旅战场抗命,不相信所谓的不遵军令,我了解他们,了解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说了这话,王自成长长舒了一口气,道:“事发后,也许是因为我父亲战死,也许是因为我太小,所以并没有受到株连。我央求筑龙城每一个官员,央求他们帮我伸冤,帮我替父亲主持公道,我求了整整七年,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这七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便包括,我的母亲改嫁。”
沉默,从两个人中弥漫出去。
“我的母亲是洛城人,是显赫之家的千金,她和我父亲成婚之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旅长,官拜下大夫,可谓军中英才,前途无量。但自父亲死后,母亲却在第二年就匆匆改嫁。是啊......她是千金小姐,怎么能轻易的就把往后的命运葬送在筑龙城里,自然要谋个好出处。可,彼时的我父亲,连二十七个月的丧期都没过,躺在草原上的他,尸骨未寒。”
楚敦煌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不由得伸过手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将他身前的酒水收起来,让店家拿来一张毛巾。
“八岁的时候,父亲离开我;不到一年,母亲回到洛城......我一个人在筑龙城,吃百家饭长大!”
“在行伍中待了一段时间,我越发的想探究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身处远在天边的筑龙城,消息闭塞,卷宗全无,根本没有希望窥探当年事故之一二。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筑龙城,进入京都,但这对于一个孤儿而言,难如登天。于是我只好拼命的积攒军功,希望能以军功累迁,可在筑龙城当中,哪里有敌人?所以,我就带着一把刀,一个蛇皮袋,出了筑龙城,进入草原,做了一名猎狐手。”
“北关猎狐手,离群索居,独行于茫茫草原,对落单的半狼族军人进行猎杀。这个身份孤独、寂寞、乃至绝望,但它却是最快的,积累军功的方法。我用了三年时间,在草原上割下了八十八双耳朵,堆满了蛇皮袋。这八十八双耳朵,为我换来了一个尚武堂推荐生的名头,我因此,才能回到洛城。”
王自成的目光逐渐雪亮,他握着酒杯的手隐隐发抖,沉声道:“北关的尚武堂学子是最多的,我从一个师兄那里打听到,关于十年前老八旅一案,所有的卷宗都被军机院存放在了藏武阁里。所以我才拼命的,想要来到京都,来到尚武堂。我必须给老八旅一个交代,我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
楚敦煌恍然道:“所以那一天,你才会迫不及待的进入藏武阁?”
“是。”王自成苦笑一声,“为了这件事情,我打听了很多藏武阁的情况,大多都是从北关那些师兄那里听来的。可结果,却还是一无所获。”
楚敦煌紧皱着眉头,顿了一顿,忽然问道:“那你今晚去的是......”
空气忽然抽离的静默,王自成抬头看了一眼楚敦煌,目光中是莫大的凄凉与叹息。那种情绪很轻易的感染了楚敦煌,让他张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悠悠的叹了口气。
“是她的家里。”
王自成平静而冷漠道:“我只想看看,她活的怎么样。在离开了我父亲,离开了我之后,她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子!可是侯门深似海,我哪里进得去,只能在外看着,看着里面通明的灯火,和门房老头打听关于她的事,门房老头说,他家夫人,刚刚喜得贵子......”
楚敦煌的眉头紧皱起来,身体有些僵硬。
“我真的是个......”王自成有些醉了,目光迷离的道:“没有家的人啊!”
楚敦煌沉默片刻,忽然道:“咱们两个,其实很像啊。”
王自成却没有听清楚他这句话,于是皱了皱眉,问道:“你说什么?”
“咱们两个......”楚敦煌看着他,却没再复述刚才的话,而是叹了口气,道:“还喝吗?”
王自成被楚敦煌这一下的跳跃性思维弄的愣了愣,他望着脚下横七竖八的酒壶,挠了挠脑袋,呢喃道:“我喝的有多少了?”
楚敦煌叹了口气,将毛巾湿了水,递给王自成。
“我从没想过会把这些事情说给别人听,你是第一个。”王自成感受着毛巾上的淡淡凉意,这些凉意将他因酒气上涌而发热的脑门变得逐渐清醒下来,他喃喃道:“就像你说的,有些事情,总会是内心固执守护的。可这些事,守的久了,就会变成刺,每个不眠的夜里扎进你的心口,扎进骨头里,一点一点的进去,疼的哭都哭不出来。我想我是自私了,这些事情何必说给你听呢?让你帮我分担还是帮我解忧?我分不清楚,只是感觉,太沉重了。”
楚敦煌看着微醉的王自成,心里一阵惘然。
他谨记着轩琅易青的交待,在每个日日夜夜里,将自己的仇恨小心翼翼的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半丝。他藏的很好,有多大的仇恨,就有多大的毅力,就会奉献出多灿烂的笑容。但当月上中天,四下无人的时候,楚敦煌总会梦回破城之夜。梦里的火光,哭喊,刀锋入骨的摩擦,在高高的旗杆上插着的人头以及母亲投入火海的那抹绚烂绝望的光芒......这些东西在梦中萦绕着他,啃噬着他,几乎要将他拉入梦魇不得超脱。但他每每都能安静的醒过来,看着空档的房顶,神色寂静而淡漠,心中却告诉自己,又是一天,又是一夜,自己终将回去,回到冰海之国,回到王城,手持北海天心,将叛国者一一诛杀!
这是他心中固执守护的东西,秘不示人。
王自成的酒劲慢慢上来了,他从盘坐变成了侧躺,口中呢喃着听不清的话,唱着南方的歌谣,梦一样的歌声从窗子飘出去,飘入深深的夜空。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