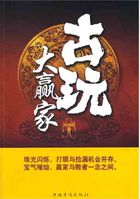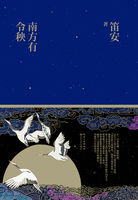据说这把戏本来是老车的光头表哥先玩的,但他的手笨,没赢人家反倒自己先输了,老车嫌他窝囊,撺掇二壶、老一都学学,谁的手快谁上阵。二壶在这方面有天赋,眼疾手快,我们小时偷个瓜摸个梨的,都只有给他望风的份,所以耍牌这事也非他莫属。我后来就这事问过他,他像放电影慢镜头般给我表演了几次,才看出点眉目。等工人们都知道这看似雕虫小技的把戏实在是个不小的骗局,另在别处又修了一座可以对开两辆卡车的大桥,况且赌风越来越盛,派出所也开始出动抓赌的时候,老车他们已赚得盆满钵满了。
在赌摊上,二壶扮演的虽是庄家的角色,出力最多,风险最大,但这创意是老车的,道具也是他提供的,且他在团伙范围里有表哥这样的亲信,又掌管着钱的出入,所以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赢家。他怎么跟他表哥分的赃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跟他鞍前马后地当了多日喽罗的二壶、老一找他分一杯羹时,他表现得颇不耐烦,都他妈吃了喝了,还有什么羹可分?
这话自然哄不住人,另两个也没那么好打发,这些天是没少跟着老车吃香的喝辣的,但想想连日来在冰天雪地里挨冷受冻担惊受怕一场,到头来只混了个肚儿圆,还是觉得不值,就说老车你狗日的太黑太不仗义了,大家一起赚的钱,你一个人吞了也不怕噎死?
你两个傻逼也不想想,老车嘿嘿笑说,还以为光咱三个能把这游戏玩得转?便扳着指头说他打点派出所花了多少钱,让他表哥雇了几个打手以防不测又花了多少钱,再加上还了当初从黑市贷的启动资金的本钱和高额利息,以及这些天花天酒地挥霍的,充其量也就剩仨核桃俩枣了,塞牙缝都不够,还什么噎不噎的。
这些情况老车事先都没说,二壶、老一虽明知他话里有水分,却无法证实其真假,可不真叫他当傻逼一样耍了。二人无心跟他开玩笑,绷了脸问他到底还有多少钱。老车仍不肯说具体数目,但还是一人赏了一盒过滤嘴烟说,钱是剩了一点,但几个人一分也没有多少,不如买辆摩托车,谁有事谁骑,算咱三个人的行不?
二壶一向没主意,觉得能骑上摩托车过把瘾风光风光,也不失为一种补偿,就敲打了老车一句说,要买就抓紧吧。说好了,这可是咱三个人的车。
老一则比他想得要多些,知道三个人合买一辆摩托车近乎扯淡,钥匙还不得是老车自己把持着。于是他说,三个人不三个人的吧我不管,平常我也不骑,但我三姑刚给我说了个媳妇,说好这两天要见个面的,我去相我媳妇的时候,车得叫我骑。
老车说,好,就这么定了。
三个人统一了意见,次日便跑到河南濮阳买了一辆大红色的铃木125摩托车,据说还是日本原装的。虽然出了省,但濮阳距离我们墨水村,别说比我们的地区所在市要近,就是比百里外的县城也要近,所以我们那儿很多人家需要进城买卖东西的,一般都要到濮阳去。我不知老车咋想的,他买来车就突突突地开到白沙村的单小双家去了。正值晚饭时分,单小双没让他进院门,叫他有事开了学再说。老车说,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有没有啥事。这几天过年呢,走亲串友的事特别多,这不我刚买了辆车,你用着它了就跟我说。
老车说时没熄火,足以证明车的性能好,大灯也很亮,照得单小双家门前那条逼仄的巷子一片光明。有狗迎着灯光咬起来,有邻居出来看稀奇,单小双一边转身回家一边说,谢谢你,我不用。
老车又说,看你还跟我客气。这车是我的,也是你的,你想啥时用就啥时用。对了,过几天开了学,你也别再骑车了,我驮着你去。
我说了我用不着,单小双头也不回地说,你还是问问你表哥用不用车吧。
正月十六去县一中报到那天,我又突然不想走了,磨磨蹭蹭的。但是,单小双已去校长那里帮我开好了转学信,同时也写好了给县一中一位老师的信。我知道单小双做这些有挖学校墙脚的嫌疑,在生源锐减的情况下,她能做通校长的工作,一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后来我听说石悄悄没少就这事挤兑她,嫌她都不跟她吭一声,分明是没把她这个班主任放眼里。又去校长那里告黑状,指控单小双吃里爬外,拆学校的台面。因为随着我的离开,不少同学也跟着转学退学,至少老车、二壶、老一三个家伙是这样的,我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收拾起书包走人了,弄得教室里一下子空了一片,叫她这个班主任又窝火又丢面子。而我那时还想不了太多,满腹的离愁别绪纷至沓来,一句顺溜的话也说不出口。也不容我多说,老车已鬼使神差地跑来,非要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县城去。
墨水镇距离墨水县一百五十余里,又冰天雪地的,难为老车古道热肠如许,如果是我一个人乘车去的话,没准真会半途而废,走不到头就又折回。出来镇子就算正式上路了,我们各自把棉袄倒过来穿,以期多少暖和一些。我和老车已很久不在一块儿谈心了,这次腹背相贴的旅程使我们得以重温久违的沟通。他说我走了,他也该退学了,原本还要去当兵的,现在村子里百废待兴,行情看好,他连兵也不当了,只全力以赴地发家致富去。一朝石油从地底下开采出来,他卓有远见地说,墨水村也将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我那时还没有具体的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虽然表面上在走求学的路子,但跟思路清晰的老车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老车给我算了一笔账,我在高中阶段最少还得待一年半,就算顺利考出去的话,光大学就得读四年,五六年以后,谁知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如先下手为强,直接到社会上混去。就问我是否一定要走,不走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干。
我叫他说得乱乱的,随口说你不是有二壶老一两个哼哈二将吗,还用着我来瞎掺和。
狗屁,老车不屑地说,那算什么哼哈二将,他两个加起来,也不如一个你。
我有点替二壶、老一抱屈,不料老车又说,咱俩真要在一起干,怕也干不了多久,谁听谁的就是个问题。弄不好,那两个家伙也会被你收买了去。所以你走了也好,一个槽上拴不了两个叫驴。
这家伙还越说越玄乎了,叫我觉得又被他给忽悠了,便在他背后拍了他一下说,你这是什么屁话,敢情你就冲这个才送我走的?
谁说不是,老车嘿嘿笑了,回了回头说,我这是在送瘟神哩。
在乡间,正月十六正好是送一切牛鬼蛇神出门的日子。因为过年,人们不仅要供奉各路神仙,还要从墓地请来已故亲属的鬼魂供奉。供奉前者多是自觉的,供奉后者未必就情愿了,只是约定俗成,会有亲戚邻居来给死者的牌位叩头拜年,你不请要遭人闲话的。但到了十六这一天,就可以把写着死者名字的牌位从墙上扯下来,一把火烧了。大风一吹,爱去哪游荡就去哪游荡。有怕孤魂野鬼赖着不走的,就非得送到坟头子跟前了,也是烧一把火,再用土或砖埋了,想不消失都不行。举目望去,道路两旁的野地里还真有不少这样的送行者,一片片纸钱燃起来的火苗和灰烬漫天飞扬,四处飘零。孤苦伶仃中,与我何其相似乃尔!
既是在送瘟神,老车自然把车开得疯快,一路上都飞扬跋扈的,超过了沿途大大小小的车子。一排排树木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风沙从头脸上掠过,凛冽的寒意钻心刺骨。如果说单小双帮我转学是为我前途考虑的话,那么,狗日的老车执意送我去县一中的动机,还真是孰为不纯了,那我这一走,岂不正遂了他的心意!那时大约已走了一半的路程,我看见老车又风驰电掣地超过一辆去县城方向的客车,就很突兀地拍了他一下说,你把车停下,我自己走。
看把你急得,老车没停车,只是慢了慢车速说,怎么还当真了?
这次去县一中上学,我是稀里糊涂地上路的,何曾像他一样想恁多。明明是他太当真了,反还说我当真,说得我真有点情绪了,很负气地说,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你回吧,我也好去汽车上暖和暖和。
不亲自把你送走,老车又嘻嘻笑了说,我怎么会放心。
话不投机到此,我已没心思说笑了,一纵身跳下来,使劲收住惯性,回敬了他一句说,你放心好了,一是我不用你送也会走;二是我不会跟你拴到一个槽上,抢吃你的驴料。
都是说着玩的,老车也不得不跳下车,一脸无辜地说,何必往心里去。
我承认我不如老车有气度,憋着气没理他,我想即使是一个瘟神,也不必非要别人送走,就自顾自站到路边,向那辆从后面赶来的客车招手。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老车急得搓手跺脚地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只想在咱俩之间做一个试验,你求学,我求财,看看咱们谁比谁跑得快。
这时客车已停到跟前,我说好了,你回去吧,记得也别把车开得太快了。无论如何,我都会记住你今天的送行。
老车在我上车时又拽了我一下,没拽住,追着车门补充了一句说,白梦娣那里你放心好了,我一不会动她,二会替你照顾好她。
我不知老车何以要做这样的表白,但知道他的话越来越不可信。与其说我放心他,还不如说放心白梦娣,她岂是他想动就能动得了的。只是我眼下已顾不上多想白梦娣了,我得先给自己找个下脚的地方。车是辆老爷车,又脏又破,但时值春运高峰期,车上人满为患,身子挤着身子,包裹摞着包裹,连一个扎针的空儿都没有。我踮着脚尖斜站在车门一侧,望着这满车背井离乡的旅人和窗外迷蒙的天空,想坐在这样的老破车上也许真不如坐老车的摩托车好,一个人孑身上路也许真不如在得天独厚的村子里混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老车的关系说到底不过是两股道上跑的马车的关系,出发点不同,目的地不同,怎么合作?又怎么赛得出快慢输赢?如果说我先前对去县一中上学还觉得可去可不去的话,此刻哪还有一点退路,我被这狗日的从墨水村里给赶出来了,形单影只中,突如其来一种丧家犬的感觉。此后的日子里,一想起这次不欢而散的旅程,我心头都会油然滋生些许悲壮的情愫,后悔没有跟老车说,快也好慢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看谁比谁走得更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赛。但我和老车就此别过,一个向北,一个向南,恰似我们后来的人生,无论物理上的距离还是心理上的隔膜都越拉越大,再也倒不回原点上去了。
世事无常,仿佛是一觉还没睡醒,大学生就业压力剧增,俨然成为社会一大问题。与我们相邻的黄坡村,业已出现大学生回乡竞聘村干部的事例。二壶、老一觉得是个契机,相约着从老家跑来,动员我回乡扳倒老车,给他们当大学生村官去。那时老车已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化工集团公司,县里市里都有名,并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政变,让他二弟出面当上了墨水村的支书兼村长。谢天谢地,我的运气还没差到无从就业的地步。工作之余,也好歹在诗坛上浪得一点虚名,在出了一本日文版的诗集后,又跟一个远道而来的美国人洽谈起英文版的翻译事宜。所以当他们说起家大业大的老车今非昔比,资产早过百万千万,我还何苦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独自挣扎,非要当一个又穷又累的小编辑,不如回乡发展经济时,我委实感到了我的奋斗毫无意义,感到了我恁多年的求索毫无意义。有一句流行至今的老话说,愿赌服输。但我骨子里仍不肯服输,我像说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圣人一样不胜苍茫不胜辛酸地笑了笑,反问他们说,老车的钱再多,家产再大,即便是身价过亿富可敌国,那你们总还算知道他的大致底细,看得见他的影子,可你们谁知道日本人读过我的诗,美国人也即将读到我的诗,又有谁能看见我走了多远呢?
问得二壶、老一云里雾里的,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私下里去咨询我妻子。什么远啊近的,他俩比比画画了半天,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脑门儿说,俺们老班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他不就在这屋里坐着吗,怎么会说我们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哩?
你们还不知道他啊,我妻子显然比那两个人要了解我,也早听说过我上学时候半夜乱跑的事,不屑地撇撇嘴,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都是当年梦游落下的后遗症,大白天也照样说胡话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