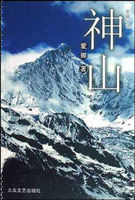“没的。我只有一个儿子。他在福建打工,福建你晓得不?很远哩。那处还有海。岛比我们这处大。他讲我们这处是小岛,小得可怜哟,穷哟,落后哟。清明节他回来过,给他爹烧纸钱罗。他爹是老肺气肿,是什么癌哈,七年啦。”
“这村子里还有没有叫严素素的?”黎妮打断她。
“没得。就我一个严素素。”
黎妮沉默下来,望着林小弟。
“就我一个严素素。就我一个严素素。”女人强调似的不断重复着。
林小弟掉头就走,不理睬那女人尾随在身后发出的“喂、喂”的叫喊。
严素素成了一个谜。她是谁?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冒名顶替?她现在何处?三个人猜测着,时而争论几句。黎妮似乎热衷于猜谜这类子事情,她得出结论:人生是一团迷雾;每个人都是一个谜,如果你不是谜语的制造者或参与制造者,你就永远猜不到谜底。宋育金联想到田橙,她也是一个谜,除了知道她叫田橙(也许也是冒名的)之外你一无所知。回去的路上,林小弟将车子开得飞快。
路中间出现了一只野兔,蹦蹦跳跳,奔着他们的车子而来。林小弟眼疾手快,一个急刹车。轮胎摩擦路面,一声尖啸。野兔居然也停了下来,望着汽车。它的眼睛红红的,亮晶晶的,一片温柔。黎妮道了一声“咦”。宋育金欠起身子看。林小弟靠在座椅上,双手撑着方向盘,耐心地等待它过去。可它就是不愿动,蜷坐于车前。双方对峙良久。林小弟笑起来。等吧,看谁拗得过谁?它坐了一会儿,起身,朝车子挪腾过来,嗖地钻到车子底下去了。黎妮连道了几声“咦”。三个人跑下车子,探头朝车下望。它坐在车肚下,在悠闲地梳理耳朵。它用前爪拽住一只长耳朵,使它耷拉下来,将它送到嘴边,伸出舌头舔它,一遍一遍。它的样子使林小弟忽然想到自己爱舔东西的癖好。他嘿嘿笑起来。它可能是喜欢上了车肚下的凉爽,外面阳光炽烈,热气熏天。他们挥手、拍手、招手、跺脚、叫喊,可怎么轰它,它都不为所动。林小弟只好回到驾驶室,在黎妮的指挥下,轻轻点着油门,带着刹车,小心地缓缓驶离。回头望去,兔子仍然坐在那儿,保持着舐舔的姿势。
林小弟的情绪被这只野兔调动起来了,话多了许多。他指点着沿途的芦苇、榕树、合欢树、江水、采砂船、拖驳船、水鸟、电线杆、房屋,将其中蕴含的美一一指出。他所有的关于植物、动物、人造物以及关于美的看法都得到了黎妮的赞同。而且黎妮还从他的话题延展开去,飞越斐济、夏威夷、马尔代夫和迪拜棕榈岛,飞越一只鹳和鹈鹕的颅顶,飞越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飞越纽约帝国大厦,飞越1000千伏特高压铁塔,朝阿尔法星和黑洞飞去。话说回来,江心洲是个美丽的岛屿,有时间他们会再来的。
次日下午,林小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以为是严素素,便急慌慌地揿下了接听键。那头那个人自称是江南。他心中一凛。杀人犯江南。亡命天涯的江南。面孔已经模糊不堪的江南。
“你还好么?”林小弟问,纯粹出于礼貌。
“唉,不说这个了。”
“你在哪?”
“嗯——”
“啊?”
“我有事,请你帮忙。”口气虚弱,病恹恹的。
“什么事?”他莫名地感到恼火,语气冷冷的。
“我需要钱,”话语中夹杂着唉声叹气,“能不能借点给我。”
“要多少?”
“一两千吧。”
他记下了他报的银行账号。他的心里犹疑着汇不汇这笔钱。杨思桑说:汇吧,不汇他会报复你的。他杀人不眨眼。何约说:不汇,他是个杀害自己亲兄弟的凶手,没有人性的家伙。宋育金和黎妮不表态。他坚持让他俩表态。何约忙不迭地游说着他俩——天网恢恢。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不能助纣为虐。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中山狼。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钱是我们的血汗。钱应该给予需要钱的人们。我们应该关心失学儿童和灾区人民。向红十字会捐款。还可以捐献旧衣服。还可以无偿献血。还可以死后捐献眼角膜、心脏和肝脏。只要病人需要,医学条件允许,连乳房、卵巢、生殖器都可以捐献。向罪犯提供犯罪资金是犯法的。包庇是犯法的。知情不报是犯法的。大义凛然,激情澎湃,说了很多,直到宋育金、黎妮不耐烦,点头为止。于是第二天林小弟来到刑警队,向警方举报。经警方调查,那个陌生电话是在贵州的一个叫六盘水的地方登记的,机主名叫童国柱;那个银行账号也是以这个名字开户的。这部手机曾给包括林小弟、宋育金、黎妮在内的六个人打过电话,声称自己是江南,向他们借钱。最终只有一笔两千元汇往了该账户。但这六个人都否认汇了款。银行监控录像显示,宋育金曾在汇款时段内出现在银行营业窗口,办理过存汇款业务。宋育金辩称自己办理的是存款业务,但在银行并未查到相关凭证。经过笔迹比对,警方认定,汇款人是宋育金。林小弟终于知道了宋育金、黎妮不表态的缘由了。此前这二人竟没有谈及此事,这令林小弟不痛快。警方说,那个自称童国柱的人很有可能是江南,现在他应该逃往别处了。
两兄弟中,林小弟最先认识江北,也最与他合得来。两个人性格相似。江北是个为人爽快的小伙子,每次聚餐,都是他和林小弟争着买单。而江南和宋育金从来都是吃白食的(宋育金明知道可能是打水漂却毅然借钱给江南的举动让他十分困惑)。他与江北相识是在一家游戏机室里。大约两年前,他经常去那家游戏机室玩一种叫“明星97”的老虎机。江北也常常在那儿玩,他的兄弟总在一旁站着看。江北看上去像个小混混,人却很热情。坐在相邻的位置时,他们有时便聊上几句,话题总是围绕着明星97,哪台机子被老板动过手脚,哪台机子可以连续下大注,怎样提高出现9个7的概率。有一天夜里,他在一台机子里输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他很光火,瞪着闪烁的屏幕发呆。他想用榔头砸碎屏幕。可手边没有榔头。江北问他输了多少,他伸出拇指和食指。八百?他摇摇头。八千?他点点头。他站起来,准备离去。江北一把拉住他:“找老板去?”他诧异地望着江北,他看见江北的眼中射出一抹愤怒。“算了。”认赌服输,他自认倒霉。“我帮你去要,要回来一人一半?”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同意了。江北转身去找老板。他看见江北趿着拖鞋,肩膀一摇一晃地向收银台走去。江北和老板说着什么。先是江北说,再是老板说,再是两个人一起说,两个人一起沉默。老板脸上堆着笑,江北脸上没有表情。老板的笑容凝固了,江北脸上没有表情。老板满面怒容,江北脸上还是没有表情。江北看上去很酷。两个人哈哈狞笑。两个人握手。江北递给老板一支香烟,老板拿着香烟翻来覆去地看,江北用打火机为他点上。老板吐出一口烟。江北吐出一个烟圈。烟圈很圆,在空中经久不散。江北回来了,手中多了一沓钞票。四千。他将这沓钱交给林小弟。林小弟数出两千,可是江北死活不要——“一人一半”只是一句玩笑话,我怎么可能那么不讲义气?林小弟不知道江北是用什么说法从老板那里拿回这钱的,他以前只是听说过爱玩的混混们输了钱,都是可以从老板那里讨回一部分的,想不到真有这回事。打这以后,林小弟再也没有玩过赌博机,却与江北成了朋友。
林小弟的心中有了恐惧。严素素和江南(不知他们现在化名叫什么),他们可能就躲在黑暗的巷口、花坛里、地下车库、消防楼梯道,甚至可能就藏在他家的阳台上,等着他,给他突然一击。虽隔着也许是遥迢的时空,他仿佛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仇恨。他将门锁更换了(严素素有他家的钥匙),在通往阳台的门上加装了一道移动铁栅门。他的大嗓门变小了,说话时喜欢东张西望,喜欢淌汗,喜欢眨巴眼睛,喜欢穿长袖衬衫(无论天气多么热),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上卫生间(直到脸涨得通红仍然憋着),不喜欢听到音乐声(尤其钢琴声,他一听到就恶心),不喜欢听到别人的喝水声和咳嗽声。每晚上他都失眠,他开始与宋育金交流司可巴比妥和舒乐安定的好处和不良反应。“你这样子可不行,”有一回黎妮担心地对他说,“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他坚持说自己心理上没有问题,只是有点儿时空错乱,比如将此刻当作梦里,而梦里又会将那里的情境当作现实——可能这就是司可巴比妥和舒乐安定的副作用吧。他说:我也想用个化名,去周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