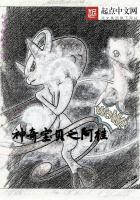近来,闲庭苑的住户经常可以看到一男两女出入小区,或在小区里散步。走在中间的是一个身材苗条、气质优雅的女人。一个年轻些的女孩,微微丰满,嘴角总含着笑意,挽着她。两个女人都很漂亮,是那种看一眼就让人难忘的女人。旁边,走着一个年轻男子,戴着近视眼镜,神情里似乎总怀着什么心事。他与走在中间的女人保持着一尺的距离。通常,都是走在中间的女人在说话,两边的一男一女听着,不怎么开口。小区里锻炼或闲聊着的老太太猜测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的认为这三个人是姐弟。有的认为那两个女人是姐妹,那个男人是姐姐的丈夫或男朋友。有的认为那两个女人是姐妹不错,但从年龄上判断,那个男人应该是妹妹的丈夫或男朋友。
宋育金觉得三个人之间的关系还真让人说不清楚。说自己是邵轻云的男朋友吧,邵轻云又不肯承认——至少不肯公开承认;说自己是田橙的男朋友吧,又没有男女关系之实——除了允许他牵手和接吻之外,田橙从不肯让他进一步深入,仿佛除了手和脸,她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是禁区,像那里藏着宝贝似的。有时,在邵轻云家,邵轻云和宋育金去卧室里做爱,田橙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或去书房里看书、上网。有时,三个人郊游,邵轻云和宋育金在无人的山坡或山顶上做爱,田橙就坐在不远的石头上朝山下眺望,或看云雾,像是自愿为他们把风似的。她看风景时有时还哼着歌,对他们的举动无动于衷。每逢此时,宋育金就感到揪心:我做什么田橙都无所谓,说明她并不爱我。他更加频繁地与邵轻云做爱,想唤起田橙的妒意,可她一点儿也不在意,照常笑眯眯的,甚至在他们完事后还亲手为他们端上她炖的银耳莲子汤。
有一次,宋育金和邵轻云在床上做爱,田橙拿着摄像机走进来,对着两个人慢慢移动镜头。宋育金惊问道:干什么?田橙没有回答,邵轻云悠悠回答:拍电影,好玩呗。看来拍摄是邵轻云指使的。宋育金翻身从邵轻云身上下来,慌乱地说:别,别,关了,关了,这是隐私,不能拍。他身上没有任何遮盖物,用脊背对着田橙。田橙定格在那儿,僵立着不动,任掌中的摄像机自己工作。镜头偏离了他们,拍下了床头灯、床头柜、床头柜上的邵轻云和田橙的合影、闹钟、台灯、散尾葵、飘窗、拉上的窗帘、壁挂空调、椅子、椅子上的一堆衣服。邵轻云恼了,叫道:这有什么?又不会给外人看,你紧张个啥?宋育金重复说这是隐私这是隐私。邵轻云继续叫道:什么隐私?做爱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做爱很美,裸体很美,你是不是担心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怕别人说你找了一个妈妈级的情人,是不是?宋育金否认:不是。邵轻云坚持:就是。宋育金只好作出妥协,回到邵轻云的身上,闭着眼睛任由田橙去拍。这一次宋育金没有达到高潮,一直到邵轻云满足了仍射不出一束精液。宋育金想起邵轻云保存在手机草稿箱里的袁一槐的短信(她从不回他的短信,却将这些短信保留着)。她和宋育金常常在完事后,靠在床头以欣赏这些短信为乐。这些短信或长或短,都是一些情人间才有的甜言蜜语,有股酸不溜秋的文学味。袁一槐有时称呼她“云”,有时称呼她“亲爱的云”,有时称呼她“飘来飘去的云”、“变幻莫测的云”、“孤独的云”、“含泪的云”,有时索性称呼她“让人恐惧的黑云”、“不祥的乌云”。接着是表白和倾诉爱与恨。这些短信都像优美的爱情诗,言之无物,却饱含深情。诗歌害人啊,宋育金心里感叹道。邵轻云会不会将自己和她的床上镜头也放给别人看呢?宋育金止不住这样担心。
宋育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试图结束与邵轻云的关系。他将这想法悄悄告诉了田橙,说:我只爱你,我只想保持我俩的关系。田橙说:不行!云姐爱你,你不能抛弃她。除非你离开我们两个人。宋育金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田橙低着头,默不作声。
有时,宋育金不想回去,就住在邵轻云家,这时田橙就睡沙发。田橙几乎不回学校宿舍,宋育金不在时,两个女人就睡在一块。他们常常一起吃晚饭,而中饭各自解决。晚饭有时由邵轻云做,有时由田橙做。邵轻云只会做西红柿鸡蛋、丝瓜炒鸡蛋、烧冬瓜等几个简单的菜,而田橙似乎什么菜都会做。有时他们也叫外卖,两个女人特喜欢吃肯德基。宋育金说,我是具有中国国情的肠胃结构,几千年的传统基因,不适应汉堡包,邵轻云就给他点培根蘑菇鸡肉饭。他边嚼蘑菇片边想: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吃过晚饭,倘若不做爱,他就坐在书房里看书,这时两个女人往往会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他架着二郎腿,靠在椅子上,捧着书,内心平静,一目十行。读过了一个章节,他会有意识地让眼睛歇歇,听听她们的聊天,望望窗外。这里楼层高,可以俯瞰很宽广的区域,条条街道,幢幢高楼,各种颜色的灯火装点着夜色里的城市。有时他想扯喉咙唱歌,但他考虑到自己唱歌不好听,就没有唱。有时他想手舞足蹈地跳一支什么舞,但他不会跳任何舞——他常常为此遗憾,就没有跳。他边捻着书页的一角边想:要是能永远这样就好了。
邵轻云经常出差,有时去省城,有时去省外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参加各种名目的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宋育金发现,只要邵轻云一出差,田橙就不愿与他见面。他约她,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终于,他对她的理由产生了怀疑。一天,邵轻云又出差去了,晚上七点多,他来到邵轻云家楼下。他看见九楼她的房间灯光亮着。田橙有邵轻云家的钥匙。他发短信给田橙,问她在哪儿,她回复在学校。她分明在撒谎。他将耳朵贴在门上,听见拖鞋拍打地板砖的噗噗声。他敲门,拖鞋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感觉有阴影覆盖到猫眼上。他将手掌蒙住猫眼,继续敲门。门一直没开。他拨打田橙的电话,门里面彩铃响了几声,电话被挂断。再打,没有彩铃声,也没有人接。他手脚并用,开始用力捶打门,喊着:橙子橙子。没有回音。他发短信:我知道你在里面。她回复:我不在里面。他问:何时你才能有独立性呢?她回复:这样挺好啊。第二天下午,他提前下班,来到闲庭苑等田橙。从四点半等到七点一刻,终于等到了田橙。她见了他,很惊讶。她问他有什么事,他反问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吗?他跟着她上了电梯,下了电梯。她站住了,又问他有什么事,她手里拿着钥匙,不愿开门。他一声不吭,一把夺过钥匙,将它插进了锁孔。他大步走进房间,走进客厅,四肢张开仰躺在沙发上。他等着她进来。他饥肠辘辘,感觉到自己即将发作。等了许久,没有动静。他来到门口,发现田橙不见了。他急忙往电梯口跑。电梯正在向下运行,到了一楼,停住了。等电梯上来将他带到楼下时田橙早就没有了踪影。他拨打她的手机。关机。这一夜,田橙都没有回来,一直关机。他拨了无数电话,发了无数短信(疑问、质问、斥责、谩骂、诅咒、请求、哀求、引诱、倾诉、示好、示爱、悔恨、发誓、媾和),骂了很多脏话,说了很多遍“我爱你”。一直折腾到凌晨。他担心她的安全。他想象她跑着跑着,斜刺里一辆车飞速而来,将她撞出好远,她被撞成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他接着想象自己如何悉心地在病床边照顾她(如同她在他的病床边照顾他一样),如何感动了她。他想象她打车遇到了坏司机(可能是两劳释放人员,也可能是从未沾过女人的老光棍),见她妩媚动人,顿起歹意,将车子开往荒郊野外;他接着想象她如何机智地与坏蛋周旋,最后成功地逃脱(她被别人凌辱,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会放纵这样的想象)。他想象她忧伤地来到湖边(野鸭湖?),望着湖水发愣,然后纵身一跃(他转而想:这是不可能的)。他想象她回到学校宿舍,蒙头大哭(为什么哭呢?是痛恨他态度粗暴吗?),同宿舍的姑娘如何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这是最佳结局)。他后悔自己的莽撞。要不是天太晚了,他都想去她的宿舍找找去。天快亮时,他在沙发上打起了盹,她发来一条短信:我没事。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邵轻云的论文《论顾城<一代人>的觉醒意识》在《文艺美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这天晚上,三个人谈到了顾城的诗。邵轻云和田橙喜欢顾城早期作品,而对他后期的作品持否定意见,认为过于晦涩,近乎搞怪。宋育金则认为顾城早期作品虽玲珑温润,却失之清浅,只能满足低层次的读者的阅读欲望,而激流岛之后的作品才更加自在,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唯一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远离了我们的世界,显得过于抽象和不及物。说着说着他突然想到了顾城、谢烨和英儿这三个人的奇特关系,联想到自己和邵轻云、田橙。同样一男两女。同样奇特。同样让人不可思议。南太平洋。全球排名第三的自杀国度。毛利人的木屋。未经加工的女性。食人族土人的冷漠。套着绳索行走的诗人。斧头下的冤魂。有那么一刹那,他产生了邵轻云和田橙倒在血泊中而自己提着刀站在房间里茫然四顾的想象。他觉得这想法荒唐,甩甩头摆脱了它。邵轻云说:小帅哥,你甩头的样子很好看哩。她忘了他对她珍视的优美诗歌的诋毁。
在田橙的要求下,宋育金选择性地将自己的“杂记”发给了两个女人。一天晚上,三个人讨论起这些“杂记”。邵轻云说:这里面好多东西过于晦涩,可能只有你自己才看得懂。她指着其中的一首诗说:你解释解释它们的意思。他说:我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她说:既然是你写的,你怎么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呢?难道诗是可以胡乱写的吗?你看看徐志摩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多么通俗易懂,又多么优美。
林小弟和田橙在网球场打网球,我和邵轻云在一旁观看。我略感嫉妒(为什么?)。当发现网球其实是一只吱吱叫的活老鼠时,我感到我的嫉妒顿时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于是我和邵轻云也抓了一只活老鼠当作网球打起来(它还咬了我手背一口,不疼,痒痒的)。两对选手跑来跑去,很快乐。两只老鼠飞来飞去,好像也很快乐。田橙长着孙舒怡那样的四环素牙(其实田橙的牙齿整齐洁白)。
对这一段梦境两个女人都表示不符合逻辑,无法解读,活蹦乱跳的老鼠怎么会成为网球,任你拨来拍去呢?她们让宋育金解释。宋育金没好气地说这是梦呢,有什么逻辑不逻辑的?她们说梦由心生,梦也应该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会有《梦的解析》了。他说那么就让弗洛伊德去解释吧。他后悔将“杂记”给她们看。他突然冒出一句:南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名叫激流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