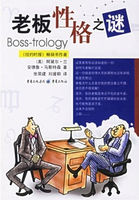话说我和水风轻都被石壁上的图画深深吸引,当下又砍了两根长一些的大树枝,把剩余的部分清理出一些来。但由于石壁实在太高,所以也就只能量力而行。等一清理出来,才发现这大石壁上不光是记录了祭祀一事,还有战争场面,还有庆国大典,还有结盟场面等。可见,这些事迹并不是一次性雕刻上去的,这块大石,也只是记录了它背后人们的生活点滴。除了这块大石壁,附近应该还有类似的遗迹才对。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和水风轻自然是喜不自胜,这些玩意儿,对考古工作来说,肯定是一大笔财富。回头一向考古研究所打个报告,没准还能获得一些表彰,为国家做上一点贡献。
我一边清理着石壁上的地衣,水风轻就一边用手机拍照、拍摄记录。当然,在这种深山老林里,手机是不可能有信号的。旁边几个土老汉不了解这些玩意,除了寻宝,他们对这些东西概不关心,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弯来扭去的山石壁画,价值和一株万年老参比起来,那可是天上地下的事儿。看我俩在大石壁前玩得这么起劲,马旦、马良、马由江几个年轻点的也会过来凑凑热闹,帮我们清理清理,并顺便听我们扯扯关于古滇国的事。马老头和马如泉则不闻不问,只顾在那湖边徘徊,该抽旱烟的抽旱烟,该抽卷烟的抽卷烟。时不时地盯着那湖中凝眸远眺,好像是盼着那株万年老参赶紧浮上来一般。
“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俩正忙活得不亦乐乎时,忽听马老头来了这么一句。
我是被先前那些大蚂蚁整怕了,听马老头这么一说,心里不自觉就绷了起来。我扒在那大石壁上,回头看去,只见远处那半月湖中有一个大水泡,比户外使用的大型遮阳伞还要大。水泡呈淡蓝色,非常清爽,像个半圆弧一样浮在水面上。细细观察,那水泡貌似还会发光,一闪一闪地像夜空中的飞机信号灯。直觉告诉我,这肯定又是碰上什么大家伙了。赶紧从那石壁上跳下来,把背包背在身上,又帮水风轻把东西打理打理。
“快,大伙赶紧过来,情况有点不妙。”马老头慌里慌张地说。
我们几个赶紧跟了过去,一望,那水泡又浮上来了一大截,看那样子,应该还有一大半在水下面。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咕噜一声闷响,那水泡竟划开水波、翻起浪头,朝岸边快速游了过来。
“快,快跑,往一线天那边跑。这是幽灵水母,他奶奶的,要命的玩意。”马老头大声叫着,已经撒开脚丫子跑了出去。
幽灵水母?这又是什么鬼东西,这马老头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稀奇古怪的玩意。我正看那大水泡看得出神,寻思又是什么妖魔鬼怪呢,这老头子又撒出来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字,立马让我这震惊的脑瓜子蒙上了一层糊涂雾水。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一把拽起水风轻,玩命儿地跟着几个山人狂跑。分秒之间,那大水泡已经快游到岸边来了。
刚才我们沿着这岸边也就走了二百来米的数,以我们的速度,跑出去也就是分把钟的事。刚才听马老头说那是幽灵水母,既然是水母,那它就只能生活在水里,上不了岸来,想来也不至于真要了人命。殊不知,这幽灵水母不止一个,就在我们奔跑的时候,前方湖里又游出来了十来个,并都在向岸边疾速靠拢。一个个湛蓝湛蓝的大伞盖,着实是非常漂亮,只是也都凶神恶煞。
突然之间,只听“啊”的一声惨叫,跑在马如泉身后的马旦一个踉跄,狠狠地摔了个狗啃泥。马如泉赶紧转过身来扶,但哪里扶得起来,两只脚已经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滑腻腻地在腿上翻卷蠕动着。那滑腻腻的东西,正是从水里伸出来的,而水里面,一只大水母正慢慢地浮起来。与其他水母不同,这只大水母却是呈暗黑色,大伞盖上,还夹杂有深红色的斑纹,黑红相间,的确是阴森可怖,乍眼一看,直叫人凉意都渗入骨髓里边。叫它幽灵水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那马旦被幽灵水母伸出来的触角绑住,在地上直打滚,不知道他是疼还是害怕,只见他手抓脚蹬、面目狰狞。马如泉张口大骂了一句:“****姥姥的阴险东西。”左手拽着马旦,右手刷地从腰间抽出砍刀。也就在此时,马老头、马良、马由江也已经赶过来帮忙,纷纷拽住马旦的臂膀往上面拖。咔嚓一响,马如泉手上一抹寒光闪过,向那水母触须剁了下去。刀锋过处,泥土四溅而飞,一条触须应声断裂,掉在地上扭曲得像条大蚯蚓。一招得手,马如泉更不含糊,且让另外三人牢牢拽住马旦,自己誊出另外一只手,双手握紧砍刀,把另外一只触须也砍落在地。歇斯底里地狂舞着,朝几根伸出水来的触须猛砍。
水母触须既断,另外三人赶紧把马旦从地上拽起来。正准备撂开脚跑,突然又见几根触须从水里摆荡出来,碗口一般粗,直剌剌地向空中横扫过来。遭马如泉刚才一通乱砍,估计这幽灵水母也是发飙了,只感觉这力道有如秋风扫落叶,电光火石之间,就朝马老头、马如泉、马良、马旦脚下扫去。一个横扫千军,就把四人撂倒在地。四人哪里料到这幽灵水母会向自己攻击,一点防备都没有,个个摔得人仰马翻。
那幽灵水母既已把四人放到,也不乘胜再击,反而把触须松了开来。但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那几根触须又齐齐向马旦绑去,这下不光是脚,就连腰部、臂膀都被绑了个扎扎实实。一抻一抖,马旦就被连根拔起,坠向湖岸。此时此刻,唯有我和水风轻未遭攻击,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早已把恐惧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一个雨燕抄水,把马如泉掉在地上的砍刀抄起来,往那触触须上狂舞乱挥,水风轻则一个匍匐卧地,像足球守门员拦球一样,着急去抓马旦的手。只可惜双拳难敌四脚,孤身难挡恶魔,那绑在马旦身上的触须,少说也有七八根之多。我只恨自己没有长上三头六臂,在那么一眨眼之间,也只砍断了两三根之数。眼见触须正在没入水中,我再挥刀去砍也是徒劳无益。水风轻一只手紧攥着马旦衣领,另外一只手在地上乱抓。可惜地上都是厚厚的地衣,几乎没有什么依靠可以提供顽固的抓地能力。马旦半截身子已经下滑,水风轻也在一步步下滑。我看着都傻眼了,赶忙把砍刀丢在地上,双手往水风轻腰上一挽,双脚在地上蹭得跟刹车一般,使出全部的力气把她往回拖。
说来也是奇怪,可能那幽灵水母一半的触须都绑在马旦身上,另一半的触须在水里使劲,此时没有伸出多余的触须来绑我俩,只是感觉那水母在拼命往湖里游动。摔在地上的几个山人,眼见情势这般危急,个个都是失魂落魄,像猴子一样弹地而起,也要过来帮忙。遗憾的是败局已定,那幽灵水母能够声东击西,把四人先放到,先让马旦失去外援,然后集中触须把他绑结实,再往那湖里死拽。这就足以说明,这只大水母并不傻,懂得各个击破。
水母见四个山人爬起帮忙,使的力道比先前更大了,大伞盖加速扇动,把浪花都翻起一米多高。只听刺啦一声响,紧接着,我挽着水风轻向后一倒,摔了个四脚朝天。水风轻手里攥着的,已经不是马旦,而是一大块衣领。哗啦哗啦的湖水翻滚声、声嘶力竭的呼喊叫骂声混成一片,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马旦被那幽灵水母拖下了水。瞬间沉到湖底,卷起一个大漩涡。
登时之间,马氏几个山人全都疯了,怒不可遏,有的嚎啕大哭,有的捶胸顿足乱骂,有的抓起地衣像石块一样往那湖里扔。悲痛,同样笼罩在我和水风轻的心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酸甜苦辣的滋味一并涌了出来。那感觉,似乎就将你凝固在了这一个瞬间。可是时不我待,正当我们竭尽全力救马旦之时,远处的十来只幽灵水母也快逼到眼前。事不宜迟,凭咱们几个人的力量,绝对干不过这些大水母。这一点,相信马老头再清楚不过。从悲痛中回过神来,照例由马老头招呼,大伙速速退到了大道内侧,风驰电掣地向前奔跑。马由江又摆出一副不要命的姿态,想跟那大水母硬碰硬,被我们几个抓着拽了出来。
跑到大道里侧,与湖岸的距离拉远了,纵使那些大水母能够日天,它也不能如鱼得水。刚才那一只黑色的大水母,完全就是靠埋伏取胜,如果我们事先料到,倒也可以躲过这一惨剧。湖里的幽灵水母眼见够我们不着,只得顺着湖岸向前游,有那强壮的,时不时地把触须甩出来阻挡,但碍于距离,顶多也就只能甩到我们脚边就偃旗息鼓。
心脏鼓动的声音,似乎比双脚点地的声音还要剧烈,充斥在脑海,让你觉得热血都快从天灵盖上喷涌出来了。前方就是茂密草丛,脚下在飞奔,心里在倒数,终于脱离危险了。马氏几个山人几个纵跃,接二连三跳到草丛里,进入安全地带。我和水风轻体力没他们好,落下了一截。就在我也准备一跃而起之时,突然感觉手一拧巴,水风轻的手一下子脱出去了。猛回头看,他娘的,水风轻的双脚竟被水母触须给绑住了。这丫头一声惨叫,扑通摔在地上,由于奔跑的惯性过猛,这一跤摔得可着实不轻。
我脑袋里像断电一样,根本就来不及闪过念头,双脚猛地一个侧蹬,把身子弹回去匍在地上,紧紧地抓着水风轻双手。同时嘴里朝那几个山人大叫:“快来救人啊!”抬眼望去,那水里又浮出来一只黑红相间的大水母,比刚才杀了马旦那只要大得多。
马氏几个山人跳出去惊魂未定,转瞬间却又遭上一劫。刚才马旦被杀之时,大家已然怒火攻心,此时见又是同样的水母暗地里埋伏行凶,当真是火上浇油、怒上云霄。刷刷抽出砍刀,三两下纵跃了回来,向准那水母触须就要落刀。马由江的砍刀先前在大蘑菇下被水风轻失落,只得滚翻在地,抓住我的双脚向后扯。
就在几把砍刀堪堪落下之时,那水母早已做好了防备,呼呼地又甩出几根触须,向几个人身上砸去。所幸几个汉子身手颇为了得,那幽灵水母向准的是时机,几个汉子反应得也甚是及时。那触须刚刚突出水面,赶紧一阵落英缤纷,把手中的砍刀挥舞得跟朵花相似。吃过亏的人,又在气头之上,使的劲儿更加猛烈。但见水沫横飞、液体四溅,那水母触须当真是像砍瓜切菜,碎的、断的当空掉了一地。几个山人口中大声叫骂,手上毫不间断,那幽灵水母吃了痛,想必心里也是震惊起来。触须又被砍残一些,剩余的触须又不能全部伸出来,只得把绑在水风轻脚上这两只勒得更紧,往水里拽得更急。这疯丫头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这会儿目睹着自己快落入水母腹中,焦急加上害怕,眼泪哗哗就流出来了。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盛满了无边的绝望与留恋。
话说就在这时,那十来只水母也已经靠了过来,有两三只游得快的,早早把触须往岸上疾甩出来。三个山人砍刀舞得正酣,果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在绝境中时,潜藏的爆发力有时会把自己也吓到。他三人当前的状态,无法用更多的言语加以形容,只能说个个都爆发着雷霆万钧之势,杀敌欲挫骨扬灰才行。
那只绑住水风轻的幽灵水母,触须被砍得七七八八,剩下的也就只能维持身体平衡,外加牢牢拖住水风轻。我突然感觉这些大水母也是懂配合的,被伤到的大水母知道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敌过三人砍杀,索性就死死缠住拖延时间,好让其他水母前来帮忙。等其他水母拢过来之后,它倒变得游刃有余,只听啪的一声,另外一条触须从它身下甩了出来,猛的打在我脑袋上。我只顾着对视水风轻那双绝望的眼,全然没有提防到位,就这样遭了一袭。脑袋嗡的一响,感觉眼睛都冒出了一大片星星。攥着水风轻的双手差点就松开掉,但不知道咋回事,似乎只要大脑还能发射信号,那两只手就绝对不会让它从指间滑落。一击既中,那水母更不消停,接着又来一击。可是老子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可能被你像****一样打来打去。眼见那触须又要砸到脑袋了,赶紧一个头点地,深深地埋在两臂之间,呼啦一声从耳旁扇过,那触须紧擦着脖颈滑溜溜地甩到了另一边。
这一击被我躲过,触须甩得太猛,幽灵水母身体顿时失去平衡。和着身子、和着力道,水风轻身子硬是被牵扯着滑了一节,双脚都浸入了水里。绝望,霎时间笼罩上我全身,三个山人被聚拢过来的水母搞得应接不暇,我和马由江虽然拼尽全力,也未能保住仅存的一息生机。我和水风轻的身子都被扯得跟电线杆一样直,感觉绷得几乎都快断了,根本就没有余地来施展多余的动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彼此,一个迈向死亡的深渊,一个徘徊在阴阳之界。那马旦落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浮动在记忆的表面未曾下潜。而那一幕,又即将发生在眼前这个鲜活的丫头身上,于心不忍、痛彻心扉、呼天抢地,但是只能选择继续顽抗。
那水母又左摇右摆地甩开触须,朝我脑袋打了几下,都被我顺利躲过。看它那鸟样,也是被我这种防御功力给惹毛了,打在臂膀上又滑不溜秋的,一点都不解它心头之恨。一怒之下,竟然改变策略,把触须伸到我脑袋下面,顺着脖颈绕了几圈,像打绳结一样勒得死死的。我被它这么一搞,登时涨得脸红脖子粗,呼吸呼吸不得、出声出声不得,只觉得天在转、地在旋,眼前的景象慢慢从视线里模糊开去。意识到自己就要死去,我鼓着最后的劲想对她说“我爱你”,但愣是被堵在气管里出不来。
死之将至,其鸣也哀。果然,恰恰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唳叫声自空中绽出。紧接着一道黑影急速俯冲而下,落在幽灵水母那大伞盖上面,咔嚓咔嚓几声响过,那水母的触须就松了开来。我刚才堵在喉咙里的三个字也被挤了出来,水风轻没听清,只是瞪着眼睛像是喜从天降的样子。绑着我俩的触须松了,那水母也慢慢沉了下去。又见那黑影跳到旁边一只水母头上咔嚓几下,另一只水母也半死不活地沉了下去。趁着这当儿,我赶紧加了一把劲,把水风轻从泥浆里拽了出来,又往后一跃,跳到大道正中。
定睛一看,那个从天而降的黑影,居然是刚入林时看到的那只大乌鸦。正在幽灵水母头上啄来啄去,像啄木鸟捡虫子吃。被啄到的水母,眨眼间就失去知觉,瘫软着往水里沉。其他未被啄到的水母似乎也意识到了危险,赶紧停止攻击,接二连三地翻滚着潜入水里。水母松懈下来,三个山人也趁机退了回来,手里的砍刀仍然挥舞个不停。
退到草丛里,再看那湖面上,幽灵水母已然一个不见,躲避危险的速度果然是如离弦之箭。却说那只大乌鸦,眨眼间把三四个幽灵水母啄掉,好像还意犹未尽,见水面上十多只水母顷刻躲得无踪无影,兀自在湖面上空盘旋着不肯离去。飞了十来圈,又冲着我们唳叫几声,这才鼓开翅膀向高空飞起,转眼就消失在了蓝天白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