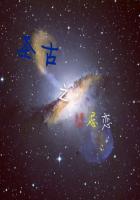于冰雪中封冻三月之后,时值大邾庆元十七年春祀,冰雪消融,候鸟归返,枝头河岸已经有了淡薄的绿意,甚至春虞已开。
本就是为了即将来临的春耕而欢庆的大节,当今圣上趁此喜日宣布平云公主与荒原皇子的婚约定在明年七夕后日的荒原漠灵节,为庆祝订婚,令户部组织在临安城中开放酒水美糕,并宣布开放封禁了数月的涌泉山道。整个临安举城欢庆。
又是无比热闹的一天,正午午时渐过,宴歌渐消,自东北方浮来一空乌云,淅沥而绵延的细雨随着清风降至临安。大家慌乱而开心的循着最近的屋檐避雨,喜悦浮现于微红的脸颊之上:“春雨贵如油,看这雨,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碎璃泉,樊烁依旧盘坐在泉边,与去年入秋时坐定的位置纹丝合缝,竟是数月未曾动过。雨落,自沾不得身。落夕祠下山的小径伴着雨声传来一串愈发清晰的脚步声。莫词撑着一把比寻常纸伞还要大一圈的纸伞,牵着刚满十二岁的小君琸来到樊烁身边:“师尊。”
莫词沉稳的声音与小君琸依旧稚嫩的声音重合在一起,在施礼后毫不累赘的安静下来。纸伞已经将三人护住。
“无须忧我,你们潜心修炼即可,君琸资质悟性都为上佳,由你为她护法足以,若你急需参悟幻月幻日,便将此事交由方泽代劳。”
“往事成空,师尊还是任之消去为好,徒儿先告辞了。”
莫词单手一揖,樊烁挥了挥手,二人便又转身离去。天色阴沉如暮。
…………
不知几何时,密雨渐稀,泉边景色便清晰起来,绿意更浓几分,密植的春虞美人更为艳丽起来。樊烁睁开眼,因为山下小径又传来一阵细碎的步声,没了沙沙细雨,闻之更为清脆。
来者是一华裳凡女,撑着一柄泛黄的纸伞,樊烁虽不愿多与凡人交涉,但却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在通山的第一天冒着雨来碎璃泉。于是他看了那女子一眼。一眼便看出其不凡。
“公主整整半生都守着临安,离这泉如此之近,为何于此时到此处来?”
罗群女子看了他一眼,以答带问:“将远游,怎不思?你认得我?”
“气度看自然可知你是宫中人,春祀而不必尊宫中俗礼者,自然是国君最为疼爱的小公主。”
女子踱步自泉边的春虞旁,轻抚一朵傍开的虞美人:“疼爱,精养,不就是为的摘下送人搏他人一笑而成自身心愿么?”说着便将那一朵欲放仍含的花苞摘下,随意撩拨开来,手中便多了一抹凌乱的娇艳。
“这朵花我看了它整整一月才生至如此动人!你怎问都不问便将其摘下!”坐在泉边的樊烁神色间有些怒意。
“你下令封山自囚便可,为何将这花也囚在这里?你可知它生来便是为的被人赏?”女子反问。
“临安皇城中又囚禁着多少凡人终其一生都难得一见的奇珍?只怕是你们都早已看腻。”
“我也觉它被城墙困的可怜,才令人移了片栽在这里,未曾想又被你困在这里。”
“既然是你予它自由,又为何夺其生命?”
“我先前便说过,它生来便是为的被赏。”
“哪怕它不愿?”
“俗花一朵,谁人管它愿不愿?凡人一个,谁又来问我愿不愿?”女子拿捏着花梗轻轻旋转,使其在眼前以不同角度呈现。
“嫁荒原?你不愿?”樊烁有些疑惑。
“似乎全天下都觉得我应当远嫁以换取平安。似如我觉得这花生来便应当是被赏,无论愿不愿,无论残不残。”
“你若不愿,便不要去。何必自找苦吃。”樊烁有点不屑。
“父皇已昭告天下,君无戏言,荒原那边早已开始准备。我便是逃,恐也逃不掉。”左手撑伞,右手执花,峨眉间覆了一层愁。
樊烁有些沉默,如同先前几个月中静坐如石一般,沉默的令人将他忽略,于是乎那女子此刻便像在自怨自艾一般。在他思考很久之后,抬头凝视着女子那倾城容颜上的素眸,缓声说道:“你若舍得富贵荣华,虚权闲逸,离开大邾之后隐名而活,也无甚难事。”
“舍弃虚荣自是不难,然而让我忘祖,我又有何颜面能活的安心?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能修行!我听父皇说过,修行界与凡界有律:修行者不得干政。我若修有小成,自然不用再政婚!”
“你的资质……实在有些差。”樊烁直言。
“差是差些,总能修行吧。”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希冀。樊烁背过脸去。
“你的资质其实是极差,完全不能够修行……”
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华裳女子转身告别,雨却真的停了下来。
…………
十七年间的春雨着实有些慷慨,每隔几日便是一阵小雨,农家将早已准备好的数种粮种播下后,不出一个月嫩苗便覆满了田野之间,远远望去临安外犹如铺了一层翠绿的绸缎。
春耕将过,天气回暖,临安正式繁华起来。各地的商人陆续前来,街头小巷井然有序的摆放着售卖各种衣用食画之类的商品。以邾服为主的行人更是如织,每日络绎不绝的穿行在临安四面的数个集市之中。
城中几处风景优美的林园中的游人也逐渐多了起来,蜂蝶围绕着新开的艳桃素杏不停飞舞,燕雀儿或飞于空中捕虫或降在房檐逗乐,每日不歇。
或是觉得春景怡人,或是因为碎璃泉边的春虞败落而觉无聊的樊烁决定下山走走。
临安有一奇景,便是城东湖中一座断桥,某年大雨将此链接湖心岛与岸边的桥自中心冲断,正好留了中间的观鱼亭,稍加修复之后这亭便成了长谈的奇景。湖心更是只有泛舟划过荷群才能抵达。
想着此时节荷叶初露,还不是红荷映日的美景之时,东湖游人应该稀少,樊烁便来到此间。
掏出几块用灵石换取的碎银给了船家,说明要到湖心之后,他便坐在了船尾静静的看着湖面初展的荷叶以及岸边三两游人头顶的绿树——他不怎喜观人。
湖大,湖心岛按照民间丈耕地的算法也有几亩方圆。虽说这时节湖心岛还不是最美的样子,但是因为清幽倒也有些游人在树荫中偷闲。
樊烁登岛后顺着小石径漫无目的的走着,虽说有迎春之类的早花,但是看一会便觉得有些腻了,正打算寻一方幽静石椅稍作休息,不经意间一瞥发现断桥观鱼亭一位佩剑简装女子有些眼熟,起步寻之。
踱步于木断桥之上,才发现那女子原来正是数日前所见的公主。她右手轻搭在剑柄之上,正望着桥下柱子边的一条不知何时死去已然发僵的浮鱼发呆。
“一条死鱼,看它作甚?总不会又是你放生在这湖里的吧?”樊烁调侃道。
公主转头看了他一眼,目中疑惑散去便又转回头看着那鱼:“这亭子不就是用来观鱼的吗?它活着时多少人慕着东湖锦鲤的名字来看它,死了就不值得别人看了吗?”
“世人是为的看它生时的可掬活泼。总不会有人如你一般盯着它死后失色的斑鳞发半天的呆。”樊烁不以为意。
“照你说,众生死后便无任何价值?”
“先贤自然不能与这等俗物并论。”
“那这无数凡俗,只是这一死一别,便此生成空?”
樊烁无语,这一问他答不出。于是他也凭栏,静静观着那鱼,再不出声。直到暮色起,公主唤了船夫归岸,他也似没听到告别之声。
月光起,风起,湖中僵鱼仍纹丝不动,樊烁观鱼,已然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