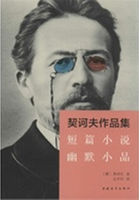老乐池和尹皋两人午后出发,路上谈笑风生,自然走的很慢,加上尹皋本就年老体衰,走走停停,当游览完王城南部的街市时已是傍晚时分了,眼见暮色四合,老乐池吩咐家老在相国府中准备了晚宴。一辆马车缓缓驶来,快到他两跟前,驭手“吁”的一声,马车稳稳地停在街市的一边,驭手跳下马车。
“太老爷,先生,请!”说完驭手深深一躬。
“中大夫,晚上我略备薄酒,在府中为你接风。走了大半天了,中大夫初愈不宜太累,一同坐车回府吧。”老乐池笑道。
“好,那就只好再次叨扰相国大人了。”尹皋显得有些疲惫,回话中夹杂着些许咳嗽声。
两人登上马车,驭手一捋手上的缰绳,马车便向相国府辚辚驶去,跟在马车后的家老和尹皋的弟子则骑马紧随其后,不一会儿,马车便稳稳地停在了相国府的大门前。
老乐池领着尹皋从正门直径走了进去,尹皋前几日一直抱恙在身没有机会好好打量一番这位中山国第一权臣的府第,这次便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探究了一番。老乐池的相国府是一座六进庭院的府邸,甚是庄严,从大门进去第一进是国政堂,虽没有一般大臣府邸那般庸俗的雕梁画栋,摆设简陋却不失摄国大臣的品位,堂中的后厅中中摆着一张朱色的檀木大案,为老乐池办理政事所在,大案的两边各有三个小案几,为他手下的幕僚议政时所坐。从国政堂的耳房绕进去到了第二进会客堂,这里是老乐池接待各国使臣的场所,陈设比起国政堂倒是讲究了许多,会客堂的铺陈处处精致典雅,好一派富丽堂皇,会客堂之外,东西边便是老乐池家人的自家庭院。从会客堂侧门进去便是第三进,这里是老乐池休息生活的场所,东边分别是卧室、客房和书房大小各四间,还设置了一个内院,内院通向偏室又有一间琴房和棋室,西边是家老、仆役们的住所,大大小小数十间之多。四进是一座后院围起来的林苑,林苑东边是一片竹木花草园囿,中间一座假山,西边便是歇息的亭台水榭,景翳翳而深幽。老乐池见尹皋要参观相国府的兴致很高,便领着他一一看了一遍,尹皋一路走马观花把相国府游览了一遍,心中暗自惊叹不已。
前几日一直躺尹皋在第三进的客房,不知老乐池的相国府竟有这般宏伟的规模,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
两人刚溜达完一遭相国府,在院子的石凳上小憩,家老便迎上来道:“太老爷,晚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席否?”
老乐池和尹皋相视一笑,老乐池笑道:“中大夫,今晚你可有口福了,走,去聚餐厅。“说罢便挽着尹皋的手朝聚餐厅走去。
到了聚餐厅,老乐池一家老小早已入席等候在那里,煌煌灯下,晚宴开始,钟鸣三遍过后,府中的歌姬从筵席的东西侧的厢房长廊上徐徐飘来,汇集在筵席的中央的舞池中,雅乐奏起,歌姬们摇曳着婀娜的身姿,身披纤薄的轻纱长裙,跳起了从白狄部族带来的中山国独有的胡舞。
宴席开始,老乐池向尹皋一一介绍了晚宴府上请来的宾客、乐氏族人和自己的几个儿子,还有一些中山国朝堂的官吏,其中不乏司马赒等。虽然乐池和司马赒政见多有不和,龃龉不断,但乐池毕竟为相多年,处理人际关系定然会把握好分寸,表面上和司马赒还是没有撕破脸皮的,每逢府上有重大的宴饮,他都不会落下这个朝中的宠臣。
虽说只是家宴,但是这一次家宴的排场绝不亚于一场中山王室以往举行的任何一场朝宴。堂中的嘉宾个个都非富即贵,一时场面热闹非凡。
尹皋一面应承着场上的宾客,一面心中嘀咕:这些人都是中山国的达官显贵,这场面也算得上中山国的精英汇聚了,但却丝毫没有发觉有一人符合他探寻大才的标准,心底不免有些失落,然而,他还是强颜欢笑,和宾客们举爵对饮。虽说有些失落,不过在失落之余,他倒是对坐在老乐池两边的儿子的有所注意。
尹皋在老乐池的介绍中得知,他有三子,长子乐深,次子乐康,三子乐朔。
乐深身为长子心思缜密,为人处事和老乐池颇有几番相似,老乐池见他有心往国政上靠拢,便时时带在身边提点,由小吏做起,已经过了知天命年纪的他已经在朝中做了上大夫,由于他在政治上悟性极高,老乐池对他一向不用操心。老乐池的三子乐朔生的一副虎背熊腰,从小就立志要征战沙场,以军功授爵,老乐池很是欣慰,在乐朔小时便亲自教授他武功,刚满总角之期便让他投身行伍,跟随老乐池四处征战,不想他每每征战总能拔将斩旗,从一个小士卒做到百夫长,从又从百夫长做到千夫长,此时的乐朔已是中山军中的中军司马,在中山军中威望甚高。两人先后都另立了府第。唯有次子乐康,从一生下来便身体羸弱,常年患有肺疾,他确实是个天赋异禀之才,很小的时候便能将《易经》、《尚书》等古籍倒背如流,其他六艺无一不精,可他性格和其他两兄弟很不同,他崇尚老子的“清静无为”,喜欢庄子的“逍遥”,生在相国这样地位显赫的权臣世家,他虽然聪明绝顶,但不贪恋权势,所以在朝中也就做了一末等的文职,这个职位与另外两个兄弟相比自然逊色不少。前几年乐康肺疾加重,竟一病不起,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乐康郁郁而终,只留下苦命的妻子和一个几岁的儿子乐毅。乐池对这个年幼的孙子甚是喜欢,时常带在身边,倒不是觉得乐毅年幼丧父可怜,他就要多加关注这个孙子,而是他总觉得这个孙子结合了他自己和乐康的优点,假以时日,必定有一番让人意想不到的作为。
尹皋案子打量一番,坐在老乐池左边是长子乐深,他生的面若冠玉,仪表堂堂,大红锦袍在夜晚的灯下泛着光亮的红光,仿佛折射出他在上大夫这个职位上游刃有余,自感春风得意的神色。他不时恭敬地向尹皋敬酒,举止文雅,让人看着很是舒心。坐在乐池右边的是三子乐朔,他体型彪悍,生得虎头虎脑,脸上的腮边长满了络腮胡,一副胡人的模样。他身穿一身甲胄,披着一件蓝绿色的斗篷,好一派英勇神武,但却少了乐深那般礼数,他光顾着自家牛饮一通,此时已面泛红光,酒气熏天。
如此热闹场面在胡舞谢幕后,未免有些冷清,于是司马赒便即兴提议道:“辞去歌姬,场面冷清了不少啊,我听说乐氏一门人才济济,文能安邦,武可定国者,不可胜数,不如就由相国大人的后辈来赋歌舞剑,以助雅兴,如何?”
司马赒的一番挑逗,显然不安好心,他的用意不过是借助兴,来为难老乐池罢了。
话音刚落,微醺的乐朔便站起身来,颇为傲慢地对司马赒大声嚷道:“大人说的好,只是这赋歌还需酝酿一番,方得风雅,不如先由我舞剑一番如何?”乐朔面对司马赒的挑衅显然不服。
“也好。”司马赒略显尴尬地回道。
只见乐朔一个空翻站在宴会案几围城的方形地毡中央,他随手拔出泛着寒光的长剑,潇洒自如地挥舞起来,动作干练精粹,沉稳中不乏锐利,不时赢得众位宾客们齐声击案喝彩。
舞剑结束后,众人皆翘首以盼乐深来赋歌一首,不料,乐深虽然官居上大夫之职,处理文案稳妥适中,但对音律却是颇为棘手,辞赋更是俗不可耐,自己也觉得出不了手。大家齐刷刷的看了他半天,他竟然纹丝不动,通红着脸,一脸羞赧。
老乐池一时难以下台,司马赒轻蔑地笑道:“难道乐家能武却不能善文了么?”
正在这时,乐池身后一位容貌俊朗的少年抱着一樽古琴,朝司马赒缓步而去,他礼貌地回道:“我伯父并非不善辞赋,不精通音律,而是在场人多口杂然乱他的心境,一时未能形成也,我虽未及冠,但时常受祖父教诲,略通音律,辞赋更是忝列门墙,我虽不才,愿献一曲,以资助兴,如何?”
一番话让司马赒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连声说好。
少年把古琴摆在宴会中央的案几上,轻轻拨弄琴弦,清越的琴声便飘荡开来,少年微微合上双眸,长歌破喉而出:
阳春召吾以烟景兮
得大块假我以文章
开琼庭以坐花兮
飞羽觞而醉月
如南山之松柏兮
恰廷芳之介兰
悲夫吾人独咏兮
郁郁难伸雅怀
孟仲各倾陆海兮
幽赏未犹转高谈
若诗辞之不佳兮
罚爵三樽以自勉
……
周围的一席人,被眼前的少年给怔住了,各个都很惊讶地看着他,他们每个人都难以置信,这样高雅的乐律配上如此精妙的辞赋,只怕是伯牙与子期在场也无不赞叹。
老乐微微一笑:“此乃我幼孙,让大家见笑了,诸位继续畅饮。”话音刚落,宴会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场面。司马赒瞪着大眼睛,张着大嘴,一时目瞪口呆。
其实此时内心最激动的人要数书尹皋了,他仿佛看见十年前自己坚持的预见的天象,笃定自己的判断,与眼前的少年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