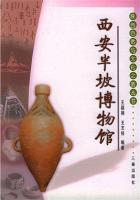死后,他的作品及其研究仍经久不衰。然而,又有谁知道这个声名显赫的硬汉子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呢?战争的残酷使他无论在身体、心理、精神还是感情上都受到了极重的创伤。海明威一生多病,痛苦难捱。他受尽消瘦症、酒精中毒、肝炎、肾炎、高血压和精神疾病的折磨。饱尝人世间辛酸的海明威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大的斗牛场或拳击场,残酷、罪恶且充满暴力和死亡。每个人在此生活既空虚又毫无意义。人生在世总是要孤军奋战,注定要失败。后期,海明威又面临着头部剧疼、思维和说话迟钝、记忆力下降和耳鸣造成的听觉失灵。白天他潇洒面世,夜晚却倍感孤独和绝望。他既要跟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搏斗,又要和他自己一个人的世界搏杀,而这似乎是更残酷和更激烈的厮杀。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爱、安慰、理解、真诚,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于是他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在一个个硬汉子形象身上表现出来。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恋呢?也许是海明威式的吧。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小说《钟形坛》应该称得上是典型的自传体小说,这是她在自杀前一个多月署名维多利亚·卢卡斯出版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艾斯特在美国家喻户晓。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文学在它的小说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妇女英雄形象,而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更是寥若晨星,自然也就没有与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伊丽莎白(《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相齐名的妇女形象。人们该怎样了解美国妇女在当代广阔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呢?
普拉斯的《钟形坛》给人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而小说的女主人公艾斯特成为一面镜子。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城。女主人公艾斯特·格林伍德出身在新英格兰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50年代初,她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女大学生,一家颇享盛名的妇女杂志比赛奖的获得者,一个富有天资的未来的作家。
可是她的前途和女性角色在她的面前并未清晰地展现出来,她无法将她学业上的成绩同成为她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女人熔为一体。当时作为女人,要么婚姻美满,是个“尽责的”妻子;要么成为老处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艾斯特试图否认即将把她禁锢在这两种女人里的角色和生活道路。她被这两种无法选择,没有前进方向的情绪缠绕着,处于一种消沉、沮丧、滞呆的状态之中,企图自杀。
在纽约进行新闻采访实习时,她的两个女友的行为让她惶惶不安:一个老于世故,靠美色诱惑男人,一个天真无邪,靠勤奋成了杂志封面女郎,而走向不同的成功之路。艾斯特想同时成为她们俩人那样,这促使她人格分裂,精神失常。而她的男朋友——一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巴迪·威拉德则要求艾斯特结婚后为他生儿育女,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是艾斯特无法接受的,她想成为她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妻子对前途选择的犹豫不决,对未来生活的恐惧,在加上男朋友给她带来的失望,使她精神失常了。艾斯特怀着迷惑恐惧的心情拼命挣扎着试图完成她的学业,并设法使自己变得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喜爱。于是她开始戴上了不同的人格面具,对所有的人都撒谎。她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同时也不愿意让人们了解她,她变得孤独、郁闷、空虚、绝望。在实习期间,社会对男女不同要求的法规和双重标准更困扰着她,使她处于极度迷惑和犹豫不决之中。从纽约返回家后,她夜不能眠,总是想起杂志上跳楼自杀的报道,于是精神崩溃了。于是她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此时她已陷进了试图自杀的深渊。
小说的结尾没有点明女主人公的最后命运,但其最终的命运却已昭然。普拉斯显然在作品中使用了她本人的大量材料,她在生活中的艰难拼争,神经紧张状态和试图自杀的发疯插曲,在作品中都有生动的记载。艾斯特可以说就是普拉斯,普拉斯就是艾斯特,尽管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普拉斯以她尖锐的洞察力和亲身感受,描写了西方当代妇女的苦闷和烦恼,以及她们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她指出了造成妇女悲剧的症结,可无法指出摆脱这困境的方法。但普拉斯毕竟不是英雄,《钟形坛》既然是作者大学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却用虚构的形式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出版时也没有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她始终寻求着自我,而不自量力与社会传统观念顽强抗争,最后以她自身悲惨的结局书写了《钟形坛》的最后一章,完成了艾斯特形象的最后塑造。她让人们记住了艾斯特这个并不英雄却具有堂吉诃德式勇气的现代女性,也让人们记住了她——普拉斯,一个以整个生命创作的女诗人。这大概就是普拉斯式的自恋吧。
如果普拉斯的自恋充满了女权色彩,那顾城的自恋则完全是男权主义的,他的遗着《英儿》更是一本典型的自传体小说,是他作为疯癫/巅峰诗人小说生涯的启端,也是终结。他在书稿的简介中写道:
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与作者同名)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错阳差。
他不仅不想建功立业,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
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奇异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英儿》全书以女主人公英儿和顾城的相恋为缘,出走为因,迭迭展开,淋漓尽致,表现了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情。
小说中的顾城,执着地要实现他理想中的乐土——女儿国的幻想,渴望深爱他的两个妻子互相爱慕,形影不离。他的发妻雷有着无私的天性,她作出了一般女子无法做到的事情——她帮助“情敌”英儿自大陆到新西兰,并为英儿做一切事情,甚至在英儿为居留身份苦恼时,提出要与顾城离婚,以便让英儿与已获得居留权的顾城结婚,好拿到居留证。
作品中的顾城不仅在生活中是个异样的人,在爱情心理上也已变态,他仇视欲望,但欲望又很强烈;他深爱发妻,依赖发妻,甚至到了没有发妻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但同时他又不断伤害她。一妻一妾和睦相处的好景却不长,英儿后来跟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与顾城夫妇不辞而别。这意外的打击使他几乎发疯。
失去英儿,他活像一个人被分成两半。于是他决定自绝。
《英儿》一书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的顾城的真实写照,是顾城沉醉自恋以至成“癖”,无可救药的表现。顾城不是普拉斯,他不必用虚构的形式把自己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也不必用笔名出版,连主人公都跟自己同名,这就明白告诉读者,这完全是一部纪实作品《英儿》的开篇就是“你们是我的妻子——我爱着你们”一洗顾城浪漫式的童话诗人的朦胧色彩,直抒胸意,表达了他对女儿国的向往。他嫌弃纷乱的尘世和做作的人生,向往在世外的桃园和童话的世界,过着率由性情的生活;他拒绝传统的道德模式和既有的社会规范,企望在一张“白纸”上抒写自我的天地,展开理想的翅膀;他讨厌世俗的婚姻和囿限于婚姻的情爱,向往灵肉和谐而又不拘形式的情爱和性爱;他反感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世社会,总想逃离开来进入想象中的女儿国,与天真可爱的女孩们相依为伴。但到头来,他仍然还是回到了他的男权主义的中心。他的自恋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什么女性中心主义,让妻妾绕膝,从身心上占有她们,而又不肯为人丈夫,更不肯为人父亲,还要情敌之间和睦相处,一旦这个所谓的女儿国遭到破坏,便要寻死觅活的,这难道不是不折不扣的男权主义的表现吗?
《英儿》是顾城因自恋成“癖”而最终走向自绝的遗书。他因自恋而成为童话诗人,因自恋生活在非现实的世界里,他逃避,他寻找,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新西兰,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又到某一个荒岛。与英儿在异域相会后的情投意合以及英儿和雷米的亲密共处,差不多使他看到自己女儿国理想的实现,但英儿的陡然离去却把这一切打得粉碎,使他明白自己终究不过是生活在自造的幻梦里,幻梦醒来,一切对他更加格格不入,而且彻底破灭了他的一切理想,死便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选择了。顾城由生到死都以自己特异的方式显现着自己特异的心灵,明知可想不可即,而即使碰了壁还要孜孜以求,并且无怨无悔。这种至死不渝的追求本身,颇令人震撼。这或许就是顾城式的自恋吧。
自恋许是人的一种本性,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在诗人那里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对于自杀的诗人则更是逃避现实,寻求自我的主要通道。不必谴责这种自恋,也不要把它和自私划等号。它是我们在对神话思维的考察中探寻诗人自杀之谜的必由之路,难道我们不正逼近诗人生死之门的真面目了吗?
在诗人的神话思维里,梦想让他们沉醉,当他们沉醉于童年的梦想,沉醉于“安尼玛”的梦想,沉醉于自恋的梦想中时,他们是幸福的,他们会成为诗神,成为爱神,成为美神,创造出他们神话的世界。只有这种沉醉变成沉溺,并最终走向极端,他们的梦想才会被惊醒,但当他们知道这不过是一道幻影时,神话的大厦也就倾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