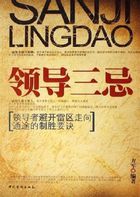入夜,上郡的月光倍显清凉。长窗扇扇开着,凉丝丝的风吹拂进来,灯火摇曳着,折射在墙壁上,好似魅影一般。
萧拓第一次半靠在窗前雕镂矮榻上,遥遥望着窗外满天的星空,和那轮皎洁的圆月。
月圆时便是人圆日,于他来说,仿佛总是笑谈。
晓月抱了薄被过来,靠在他身畔坐下,轻轻替他盖了半个身子,抬手轻柔试试他额角温度,柔声关切问道:“怎么了?只出去了半天怎么就累成这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萧拓忽的就牢牢握住了她的手,极其用力,目光缓缓从那遥远的星空移了回来,落在晓月温和的面容上,她在微笑,是那般令他心安的微笑。
房门被轻轻叩响。
“进来吧。”晓月回首轻言。
房门开阖间,正是左原青,看见晓月,隐有难色。
萧拓轻轻抬一抬右手,“说吧。”
左原青稍有疑虑,便禀道:“禀陛下,恭王府别院管家来报:恭亲王重疾不治,突然薨世了;魏娘娘前来视疾,兄妹情深,心痛甚哀,当即服了恭亲王房内白杜鹃自尽了!”
晓月登时全然愕住,似有满屋的魅影横行一般。
满室的寂静,凉风好似吹得愈盛,灯火摇曳得愈发厉害,满地的影子,是窗外的树、是遥远的星辰,皆变得黯淡了。
时间好似突然间变得漫长无度。
萧拓的声音沉重且疲惫,乏力般的倚靠着软榻,右手微握成拳,掩唇轻咳了两声,阖目道:“恭亲王身染重疾多年,今朝离去,朕心……,在武陵皇陵选处地方,按亲王礼葬,皇兄身子不好,未免到了那边无人照料,恭王府别院所有侍从仆役及多年照料皇兄的太医悉数陪葬;魏妃……,虽被废多年,毕竟是朕之发妻,今朝念及与皇兄多年的兄妹情谊,同赴黄泉,其情可悯,其心可嘉,就在皇兄陵寝对面起陵,按贵嫔之礼安葬吧。……明日朕要巡视河工,你去安排妥善,下去吧。”
“是。”左原青领命退了出去。
晓月呆呆的望着他,他的脸色渐显灰重,紧抿双唇,虽是阖目,她却听得出他呼吸中的极度难过。
那双空洞却满载企盼的大眼仿似就在眼前,好似还是她用尽全力翻掌去握他的手。
她心中的愧疚还未全然消退,她最为愧疚的那个人已然香消玉殒了。
突然间离世的两人,一个,是与他血浓于水的亲哥哥;另一个,是与他幼年结发的妻子。
失去亲人的痛苦,她已然品尝过多次。
然而,他心中的难过悲哀,其中的许多却是她品味不到的。
望着他,一面是倍觉愧对亡灵,一面是心疼难耐。
她真的从未见过他这般痛苦。
晓月缓缓伏贴在他胸口上,他心口‘砰砰’的跳着,那一定是满腔炙热的情怀,激烈的想要喷发,却生生的被压抑着。“拓,你有话要对我说么?”她极尽温柔的轻轻问道。
萧拓始终牢牢握着她的手,未曾睁眼,只有她清幽的发香慢慢的一丝丝沁入鼻中,缓缓沁入他心口,安抚着他酸涩已极的心绪。
“晓月,我是不是太无情了?”他良久方问出这一句来。
不消他说,她已猜到了几分。
“拓,……你真的累了……”她本想劝慰他的,可终了,她竟只说得出这一句来。
空气似乎静谧得连吹进窗口的风儿都听得清晰无比一般。
“哥哥长我三岁,蓉儿小我两岁。高祖爷爷的王夫人多年随高祖征战南北,甚得高祖的喜爱,蓉儿的祖母便是王夫人的亲妹妹,而哥哥的母妃魏昭仪正是蓉儿的姑母。蓉儿常常入宫玩耍,我们自小一起长大。蓉儿生性如男孩子一般顽劣,无拘无束。哥哥常常带着我们一起闯祸,每次闯了祸我们就躲到王夫人的丹荷宫去,连父皇也奈何不了我们。王夫人于弘治十三年薨世,魏昭仪也不十分得宠,我和哥哥也早已入上书房学习,功课渐渐繁多,那以后,蓉儿便很少入宫了。及至我们成年,魏相国权倾朝野,舅父身为太尉,尚能与魏相国分庭抗衡,为稳固我的地位,便想尽办法,穿掇了我与蓉儿的亲事,甘愿自己的女儿亚儿为太子良娣。大婚当日,我才知晓,原来哥哥一直属意蓉儿,可惜木已成舟,一切都迟了。我与蓉儿成婚之后,魏相国自然由哥哥一面倒向我这一边。故而,发生了我穿越千年时空的事情。弘治二十四年,我回来时,魏相国已复倒向哥哥一面,舅父也身染重疾不起了,哥哥,几乎已掌握了全局,唯有父皇的遗诏明谕传位于我,哥哥怂恿蓉儿替他盗取遗诏,意图篡位,幸得亚儿拼死将遗诏从蓉儿处偷出予我,我才得以登极。当日血染奉华门,舅父家的两个哥哥,也就是亚儿的两个亲哥哥都为我命丧当场,血溅白璧。从那时起,天下人都知晓哥哥患了狂癫之症,移居上郡别院。我登极第二年废蓉儿改立亚儿为后,满朝文武虽少有非议,却无人敢明言。这一段过往,已成了宫中禁忌,无人敢提及。这些年来,我一直极力的想保全他们性命,无论怎样,只要他们可以安然的渡过余生,终了,却还是有人要借着他们的名头寻事。”他许是一时说的话语过多,又轻轻的咳了一声,右手微握成拳,抵在唇边。
晓月连忙掏了帕子替他拭去唇边一点湿润。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对他说,更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只轻唤着:“拓——”
萧拓微微睁眼,眸中有一片微薄的红,“晓月,我真的好累——”
他一语未完,已又阖了双目,轻轻咳着。
晓月温柔拭着他唇角,柔声的、低低的、轻轻的,“我知道,睡吧,我陪着你。”
她的话语那般温和,仿似微微暖意融进清冷的、凉丝丝的风中一般,令他渐渐觉到心安、渐渐心静。
他依旧牢牢握着她的手,终于渐渐睡去,幽蓝色的月光从窗口直射进来,照在他俊朗的面孔上。
她就这样呆坐着,痴痴的望着他。
他当真是累极了,这一夜,睡得这般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