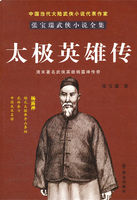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相府是丞相的相府,相府里的事自然是丞相说了算,我们这些外人又岂有置喙的资格?”魏夫人顿了顿,又道:“城门失火固然令人遗憾,然池鱼无辜,还望丞相手下留情。”魏夫人这话说得意味深长,袁旭闻言不由面色微变,众人也是无声附和。
城门失火,尚且殃及池鱼,今日相府遭受回禄之灾,朝中百官又岂有幸免之理?
朝堂风云瞬息万变,权臣倾轧朝夕不断;明堂天子,深宫帝心,诡谲阴谋致人死地,伏尸百万而兵不血刃。权谋交战之际,无形战场之中朝中百官尽为砧板鱼肉,受尽刀俎凌虐。
今日丞相之意不在火,在乎祸。
兰亭夫人由素弦扶着上前几步与魏夫人并列,“袁丞相今日——是想私设公堂?丞相虽为百官之首,也不能将皇城令视若尘土吧!”
袁旭眉峰微挑,“方才魏夫人也说了,今日之事说到底是袁府的家务事,本相处理自己的家务事又何须皇城令过问!”袁旭眼露寒光,“两位夫人如此与本相百般为难,难不成是——”
“丞相严重了,我与魏夫人都只是普通的内宅妇人,哪里敢干涉丞相府的家务事!只是丞相府这把火起得蹊跷、烧得又太旺,实在让人担心——就怕一不留神这把火就烧到了自己身上!”兰亭夫人神色平静,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意味。
袁旭心中恼怒,面上却不显分毫,维持着一张让人看不出丝毫破绽的笑脸。“几位夫人多虑了,本相定会秉公处事,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袁旭向一旁的相府管家抬手示意,“去叫袁鞍把人带到这儿来。”
相府管家应了声“是”,随即领命而去。
兰亭夫人敛了敛神色,这老狐狸究竟打得是什么主意?
袁旭望了素弦一眼,眼里含着隐晦的杀意和轻蔑。踏尘郡主······没有平王,你什么都不是!很快,就连平王府你都留不住了。
袁旭的那一眼自是没有逃过有心人的眼睛,袁旭也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眼里的情绪。兰亭夫人、魏夫人、茉萱俱是心中一紧,这奸贼究竟想做什么?
兰亭柳眷与钟离逐风对望了一眼,彼此心照不宣。
今日这把火,袁旭是打定主意要烧到平王府!
那素弦······素弦要怎么办?她······
兰亭柳眷担忧地望着素弦,他也只能望见素弦的背影。
钟离逐风右手捏着檀香扇的扇柄,他没有将自己的目光移到素弦身上,他在看袁旭。他总觉得此时的袁旭身上有着些许异样,是什么呢?钟离逐风展开自己的檀香扇,檀香扇微动,带出香风。是气味······是一种常人闻不到的奇异香味。常人闻不出来,钟离逐风却因久在脂粉堆中而对花粉有一些异于常人的辨识能力,故而闻到了这股异香。
钟离逐风回想了一下先前看戏时袁旭坐的位置,顿时明白过来。眼中浮现出些许笑意,当年的小丫头······真的长大了。
等待,分为无望的等待与有望的等待。无望的等待于人是煎熬,有望的等待于人是享受。
袁旭此刻就在享受等待猎物俯首的快意,他喜欢将自己的敌人一步步地逼入绝境,让他们在死前尝尽千种绝望、万种苦楚。
然而,袁旭并未能得意太久。在他等来袁鞍之前,丞相府内又起了变故。
钟离逐风嗅了嗅风中传来的气味,双眉微皱,“敢问丞相,相府西院的火可扑灭了?”
“自然是——”袁旭并未说完自己的话,因为他已亲眼看见了,西院方向又起黑烟。不——不只是西院!
相府四院同时升起黑烟。
“相爷,东院失火了——”
“相爷,南院失火了——”
“相爷,西院失火了——”
“相爷,北院失火了——”
四院仆人先后来报,袁旭的脸色刹时变得无比难看,“火势如何?何人在指挥救火?”
“回相爷,火势十分迅猛,其中以东院为最,管家方才已去了东院······”其中一名家仆回答。
袁旭还未来得及训话,袁鞍便带着人过来了。袁鞍的面色十分难看,袁旭在瞧清袁鞍身后跟着的人时脸色刹时变得不能用难看来形容。
危圄——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袁鞍身体僵硬地走在前方,显然对身后的那人极为忌惮。说是走在前方,袁鞍却是向右移了两步的距离,丝毫没有挡住那人的视线。
危圉是一把刀,一把积累了无数杀气的刀,一把不由人掌握的刀,一把连当今天子也不得不忌惮的刀。
袁旭虽不将朝中文武百官放在眼里,却对危圉有几分忌惮。只要是人,便有七情六欲,人一旦有了七情六欲,便有了弱点,危圉这个人却没有弱点。在大夏百姓眼里,危圉是神,惩恶扬善之神;在大夏官员眼里,危圉是刀,杀人诛心之刀。
从来没有人将危圉看作人间之人,这个不是人的“人”如同神一般在大夏创造了十年的神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危圉的地方就有神话。
“袁丞相。”危圉在距袁旭十步之外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冲袁旭抱拳行了一礼。
那活在神话之中的男子长身玉立,面色白皙非常,却身带肃杀之气,眉目之间浮动着寒刀戾气。没有人会将这容貌如文雅书生的男子当作是一个文弱书生,只要见了他的人就会发自内心地认为这男子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
“危神捕——”袁旭向前几步,“何时从梁州回来的?”
“益大人奉旨接任皇城内史,我便随他一同北上。”危圉简略地回了袁旭的话,“益大人偶然得知肸酃国奸细混入大夏、隐入皇城,意图对相府不利,故而派危圉暗中关注此事。”
“危神捕的意思是相府今日之难全是肸酃国奸细所为——”袁旭的目光移向被危圉的手下押着的几个“奸细”,“这几个便是今日在相府中放肆的贼人——肸酃国的奸细?”袁旭暗自向袁鞍投去一眼。
危圉眉目微微一动,示意手下将为首的一名奸细带上前方来,“这奸细正是丞相的手下先前擒住的贼人,丞相先前难道没有见过?说来丞相手下真是不乏能人异士,此人我已追踪了三日,始终不能将其擒拿,丞相的手下却在短时间之内将其擒住,当真是让人佩服万分。”危圉话中有话,语气轻缓却暗含机锋。
那奸细一脸病态,看面容,应已过而立之年。此时半死不活地低垂着头,谁也不看,一副万念俱灰的模样。
袁鞍走到袁旭身边,低垂下头,“相爷,此人正是袁募先前擒住的贼人。”袁鞍语气平静,眼中却尽是愤恨不甘。
袁旭已明白自己的计划出了天大的变故,原本安排好的大长公主身边的人变成了肸酃国的“奸细”······危圉不可能有问题,究竟是什么人有那么大的能耐竟然能从袁募手中不动声色地将人换走?他的丞相府已经到了让人来去自如的地步了吗?
“让危神捕见笑了,没想到肸酃国的奸细如此无孔不入,竟将今日的寿宴搅和得一塌糊涂。”袁旭对危圉的疑问避而不答,转而将问题引开。
“肸酃国的奸细虽然厉害,却敌不过丞相手下的能人异士。”危圉神色寡淡的脸让人看不出表情,“危圉斗胆请丞相将这些人交由皇城令发落。”
丞相府之事牵扯到肸酃国的奸细便涉入了两国之争,袁旭权力再大也不敢只手遮天。皇城令掌管皇城,危圉身为天门神捕之首,代天巡狩,今日之事断然是不可能朝着袁旭预期的方向发展了。
虽是“斗胆之请”,却含天子之威。
“危神捕言重了,此事牵涉到两国之争,再不是我袁府的家事,自然该移交皇城令。”袁旭正色道。
危圉又向袁旭抱拳行了一礼,“多谢丞相体谅,今日叨扰丞相了。”危圉行事从不拖泥带水,话一说完便带着人走了。
袁旭继而向众人拱了拱手,“今日之事是袁府对不住诸位,袁某人在此向诸位赔罪,还望诸位原谅袁某人的不是。”
众人的去留全凭主人的一句话,袁旭要留人便留人,袁旭要赶人便赶人。然而,看清了形势的也好,尚处于云雾中的也罢,没有人愿意继续留在相府掺和这趟浑水。
“相爷言重了——”
“相爷言重了——”
一番口是心非的客套之后,众人便纷纷告辞离去。
几番起落,丞相府的这场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一场大戏落下帷幕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结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场戏结束了,后面还有无数场戏等着上演。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一场场交织着人世种种悲欢离合的大戏。寿数有尽时,生死轮回却无穷尽,人世大戏也就永无落幕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