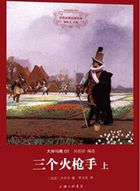咸海的北部和东部岸线曲折,分布有许多小湖湾和沿岸岛屿,锡尔河就从它的东北角注入,湖南岸为阿姆河口三角洲,西岸却是陡峭的石壁。发源于西天山山脉的这两大河流给这片海子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补充,它也成了这一带调节气候的重要一环,靠近海边的草场也是不可多得的优良牧场。
哲麦里一家在咸海的东边游牧了一些日子,等到锡尔河水冻实了以后才赶着马群过河,绕过北海岸来到咸海的西边,走出不远老人看了看周围就再也不想走了,越往前走草场变得越稀薄,在一座小丘陵旁老人止住了脚步。这里山头不高可还是能够抵挡一下寒冷的西北朔风,他找了一处背风坡就决定安营扎寨,看到儿子不情愿地蹙起眉头,老人耐心地说:别指望那些水草丰茂的好草场了,东边大批的畜群来到这里,草场好的地方就会人多畜多,我们远道而来不好过,当地人的日子也被搅乱了,时间一长人畜争地盘、争草场、争水喝的事就难免发生,我们争不过人家,这里草稀一点,麻烦事也会少一点。
老人的看法虽不能用高瞻远瞩来形容,但起码还是有点见地的。他嘱咐一家人,遇到当地人要友好一点。“骡子马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这是老人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或许是为老人的话做一个注脚,他们住下不长时间,当地人就赶着马群冲乱了他们,经过一番努力的唿哨和交涉,当地人离去了,清点马群他们还是损失了十余匹骟马。
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马群冲出围栏顺风跑出百余里,等到天亮风雪停了下来,他们好不容易收拢马群,又有几个当地人明火执仗地来打劫他们眼睁睁损失了八匹马,其中有三匹母马。法图麦的爸爸提起马鞍上的狼牙棒怒目圆睁,想催动坐骑上前理论,被老人横过来的马杆给打醒了老人眼里也喷着火,但他还是来到儿子跟前说:知道草原上没有老虎的原因吗?因为这里更适合狼群,老虎虽恶,也难敌群狼。还是忍了吧。这儿不是我们的地盘,等打完仗我们回到锡尔河再图发展才是正道。
法图麦爸爸手里握着的狼牙棒不停地抖动着显示着自己的愤怒,他的脸憋得通红:他们和蒙古鞑子一样可恨,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还忍心抢劫自己的同胞,算什么东西?
哲麦里老人咬得牙关咯咯直响,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赶快拢住马头,往回走吧。怕小人不算无能。
终于熬过冬天,人们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一家三代四口人挤在一顶小小的帐篷里,生活上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天气一转暖,户外活动就自由了一些。尽管这里的草场有些稀稀拉拉的,可当绿意覆盖了秋草和沙地的枯黄,各种颜色的鲜花争妍斗奇,许多不知名的燕雀翻飞乱舞的时候,一个生动的草原又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个春天,随着一批小马驹的诞生,马群又一次超过了百匹。哲麦里老人心头的阴霾散去了不少。他在帐篷后面用木头搭了个小亭子,用洼地里的旧年蒲草编织起顶子,又把四周围起来,找来一截比拇指稍粗的树杈作了个钩子,一个简易的沐浴室就建成了,他管它叫水房子。五时乃玛孜之前他就会让一家人轮流做大小净,然后在一个前面没有遮挡的地方铺下拜毡,领着一家人面向圣寺立定,肃穆庄重地抬手入拜,祈求真主的护佑,知感真主的恩德。
那是几天极其闷热的天气之后突然的一个暴风雨之夜,让哲麦里一家毫无防备地经历了一次咸海岸边强对流天气的威力,这是一次风、雨、雷电与恶狼借助黑夜发起的联合进攻。世间的一切事物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平衡一旦被打破之后,各种力量相互影响、整合,就会被放大十倍、百倍,然后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式释放出来,造成可怕的后果。
入夏后,太阳像突然发威的火炉,将地皮烤得发烫。白天在旷野里眯起眼睛就能看到草原上到处都氤氤氲氲的,蒸腾着一片雾气。空旷的草原上没有遮阳的树木,偶尔有他们也不能稍作歇息,这一点马倌就不如羊倌了,羊群走动慢,羊倌有时还可以把羊群赶进草场后自己找个荫凉歇息一会儿。马群动作快,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尥蹶子,撒开四蹄几十里就下去了,所以牧马人时刻不能离开马鞍子。哲麦里和儿子坐在马背上被当头的烈日晒的脸黑得都快赶上阿姆河南边的人了,一天下来就和草场上的青草一起打蔫了。海边上水汽蒸发量大,空气潮湿,气压很低,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天到晚一身臭汗,汗水稍干衣服上就会显出一圈圈的碱渍。出汗多只好不停地喝水。这里的水带有一丝淡淡的咸味,越喝越觉得口渴,可喝下肚的水又很快通过汗毛孔变成水珠钻了出来。到晚上闷热的更是让人难以入睡。帐篷没有窗户,一天晒下来到晚上热得像个蒸笼,哲麦里和儿子干脆就在帐篷外铺上一层干草打地铺。
他们的马群里大多是阿拉伯马,这种马本来是短毛马种,皮质薄,毛短且稀疏,一方面有利于排汗调节体温,同时也有不好处,就是不耐阳光暴晒,所以马群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是萎蔫不振的。
东边不时传来成吉思汗攻破花剌子模城堡的消息,讹答剌破城了,不哈剌失陷了,尤其撒马尔罕遭屠城的消息更令人闻之色变。哲麦里担心在那里守城的孙子,经常半夜里睡不着觉,但当务之急还是和儿子轮流值夜抗击眼下从未经历过的特大狼灾。
连续三天酷热难耐的高温让人对晚上防狼的火堆都唯恐避之不及,哲麦里老人只好选择帐篷和马群围栏的下风口点起了一堆篝火,又在帐篷前点了一个小火堆,即为防狼又能照明,天上一弯新月早早地落了下去,草原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只有这一大一小两堆通红的篝火在黑暗里闪着光芒,证明着这片草原还没有死去。
很多日子以来,营盘后面的山坡上,嗷嗷的狼吼声此起彼伏,在这寂静的夜空里久久回荡,引得两只大狗狂吠不止,最后连大狗的嗓子都有些嘶哑了。马群也竖起耳朵警惕地侦听着。
哲麦里老人并不很担心狼灾,他在离开火堆的草垫子上盘腿坐着啜着香茶。他喜欢喝茶,不管是花茶,还是生茶、红茶仰或绿茶。他每年去撒马尔罕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采购茶叶,每次都要买够半年的茶叶,最后一次去,也就是去年初秋,他已经知道了蒙古人要起兵来犯的消息,他怕商道受阻,买够了足足一年用的几大包各色茶叶。每到晚上他都要自己找出那把大宋那边过来的细瓷茶壶,也不用茶杯,而是右手执壶,直接嘴对嘴慢慢地啜饮,只有这时老人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一些。
不断有前方打败仗的消息传来,前些日子从东方来了一大批花剌子模的兵丁,说是保护沙王的部队,把个咸海四周围了一圈又一圈。哲麦里老人想去打听一下消息,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打听到,还把自己心爱的大白马也搭了进去,老人懊恼得好几天没吃下饭去。这边的情绪还没缓过劲来,海边上的兵丁却一哄而散了,据传是沙王在这片海子中间的小岛上归真了。说是由札兰丁王子继承了王位,正率领花剌子模的勇士们去收复失地。这让老人看到了回锡尔河草原的希望,同时也想起了萨乌丁和他的孙子札兰丁。
老人过去没事的时候常给法图麦讲他和萨乌丁一起追随老沙王在攻打塞尔柱时的一些往事,可现在,他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再也引不起一家人的兴趣,老人也没心情再去翻腾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了,只好自己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把个壶嘴嘬的吱吱直响。
法图麦娘儿俩进帐篷去了,法图麦爸爸也在草垫子上打起了鼾,连续几天这样的天气把人靠得有些支撑不住了。老人给火堆上添了几根较粗的木柴,回到他自己的草垫子上抬头看着天空发呆。
西北的天上有亮光划过,哲麦里老人伸长脖子看了看,又抬头看看头顶晴朗朗的天,星星特别得亮,偶尔也有一两道闪电划过,是那种露水闪,没有云彩只有闪电,仔细听也听不到雷声,这说明空气中的水分太大。其实不用看这些也知道,这里由于靠近海子,本来到处就是潮湿的,好像随便抓一把空气轻轻一攥都能攥出水来。
法图麦在帐篷里热得睡不着,走到外面喘口气想凉快一下。见爷爷一个人还坐在夜色里喝茶,便走到爷爷身边,轻声问:爷爷,您在想什么?
哲麦里叹了口气,他连续几天夜里做噩梦,每次梦里都见到萨乌丁,第一次是来约他去撒马尔罕说是给孩子准备聘礼,第二次说儿子没了要去找他的儿子伊纳尔只,还有一次只给了他一个背影,模模糊糊地离他远去,什么也没说。可老人不敢把这些告诉法图麦,只好苦笑着在黑暗里咧着嘴:想什么?想咱的锡尔河草原呗,这边的水土不适合咱们,连喝的水都是苦咸苦咸的,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还是咱家乡好。
法图麦给爷爷的茶壶里添了水,然后在爷爷跟前坐下来,像爷爷一样望着天空。西北方向隐隐约约的闪电里,像是有云彩在慢慢升起。法图麦回头对爷爷说:是不是要变天?
哲麦里老人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那里,瓮声瓮气地说:闷了好几天了,也该下点了。不然,人和马都受不了。
法图麦又看看那边的闪电:真要下大雨的话,就一个帐篷连个房子都没有。咱不出来就好了,老爷们后来都忙着打仗了,也没时间管咱们了再说,他们打仗与咱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哲麦里摇着头:历来兵匪一家,有时兵祸比匪祸还厉害。打败的兵输急眼了还有什么军纪,见什么抢什么。打赢了的就以为天下都是他们的也是什么都不放过,不刮下三寸地皮都不过瘾。有时长官为奖赏属下,还会纵容他们干些下三烂的勾当。
法图麦过去听爷爷拉起他们当年的壮举,是那样的义正词严,甚至还有些神圣感,这会儿忽然明白了一些。她低下头说:妈妈也这样说。她这两天老做噩梦,半夜里哭醒好几次了。
哲麦里继续望着遥远的天空,听了法图麦的话,他感慨地说:当母亲的就是这样,既不放心你,又挂念自己的儿子,不做噩梦才怪。唉!女人哪,永远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法图麦抬起头直直地盯着爷爷问了一句:你和爸爸不挂念哥哥?
哲麦里回头看了法图麦一眼,很明显是孙女的话戳到了他的痛楚,他怔了怔慢慢缓和了一下情绪,反问道:你哪?只挂念你的哥哥?
法图麦听出爷爷话里的意思,放在平时她早该和爷爷撒娇了,可这次爷爷说中了她的心事,她低下头去小声说:不挂念哥哥还挂念谁?他?他还不到派丁的年龄哪。
哲麦里叹了口气,他虽然不会说什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话,可他曾经上过战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夜晚,他挂念着自己的孙子挂念着萨乌丁,也挂念着札兰丁,因为那孩子毕竟是他看着长大并且是自己中意的小伙子。他端起茶壶凑到嘴边:是,不到年龄好哇。
法图麦被爷爷看出了心里的隐秘有些羞涩,偷偷地看看爷爷,见爷爷又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了,张张嘴刚想说什么。就在这时,帐篷后面的小山头上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把法图麦吓了一跳。
狼嚎的声音离得很近,就像是在帐篷后面发出的,一直在哲麦里老人旁边趴着的两只大狗“噌”地一声蹿了出去,狂吠着向狼嚎的方向奔了过去。哲麦里老人快到嘴边的茶壶停在了半空里。
法图麦爸爸也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拿着一把狼牙棒站了起来哲麦里老人没动地方,他示意儿子不必惊慌,又指点着远处的火堆说:去加点木柴,回头睡吧,没事的。
法图麦爸爸照着老人的话做了,刚回到他睡觉的草垫子跟前,又一声狼嚎划破夜空,是从马群围栏的另一侧传来的。刚刚回来的大狗又扭头追了出去,法图麦爸爸有些不放心了,他点起一支火把围着围栏转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才回到哲麦里老人的跟前,纳闷地说:这两次叫声好像不是一匹狼,难道是有狼群来了?
哲麦里示意他不要说话,他端着茶壶的手停在嘴边,凝神静气听了一会儿,预感到这个夜晚不那样平静了,他一边侧着耳朵听着远处的动静,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今天有狼群在四周围着,那咱可就在劫难逃了。
法图麦爸爸明白了老人的意思:你是说今天的天气?
老人神色凝重起来,抬头看了看西北的天空,闪电好像比刚才亮了许多,他慢慢地站起身:去把帐篷加固一下,把绳子拉紧了,法图麦进去把你妈妈叫醒,用不了多大一会儿那片云彩就会过来,恐怕今夜这场风雨小不了。
法图麦看了看西北的天空,疑惑地问了一句:云彩走得那么慢,又离得那么远,不会有事吧?
哲麦里:做好准备吧,风雨说到就到。
法图麦:那我们……
哲麦里:托靠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