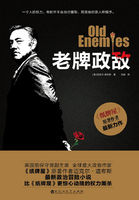札兰丁这才认出巴根就是当年抓他来的那个蒙古小头目,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在锡尔河草原他最后一次回望家园的景象,那浓浓的黑烟又一次笼罩在他的眼前。札兰丁的眼湿润了,他不想让这位蒙古的巴图鲁看到自己流泪,扭头看着远处阿尔布花山说:我也知道,我的爷爷、婶婶、弟弟妹妹都死在了你的手里,你还欠我好几条命呢。
巴根摇着头,晃着手里的马鞭:不,不,我杀过人,杀过很多很多的人,可不是你的家人。我只抢了你一张狼皮,我会还你的。
札兰丁这才回过头来,眼里依然闪动着仇视和倔强:百户长,你记得就好,别忘了我可是打过狼的。
巴根笑了笑:叫我巴根,你是打狼的英雄,我喜欢英雄,原来你是花剌子模人,我是战胜者,那狼皮当然应该归我。可从我抓到你开始,你就是大汗的子民了,那张狼皮就该还你了。
札兰丁撇撇嘴,梗着脖子大声说:是,该还我了,百户长。
巴根用手里的马鞭在另一只手上敲打了两下:你可以叫我百户长,也可以叫我巴根,但是你必须记住,这里是军营,长官对属下有无限的权利,这是蒙古军人的规矩。
巴根说完扭头走了,大伙也都散去了,可札兰丁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阿里和伊斯玛仪这才走上前来,和札兰丁一起看着怒冲冲远去的巴根。
一阵风吹过一阵黄沙,札兰丁吐出灌进嘴里的沙子,回头看着北面的阿尔布花山,好像它就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太阳早已隐去,西北的天空上翻滚着铅云,大山的几个高耸的山峰慢慢地隐于云雾之中,那山腰里缭绕的云雾就像当年在锡尔河草原升腾起的那股浓浓黑烟。该死的蒙古鞑子,杀我亲人,烧我家园,还要我给你们卖命打天下,只有野兽才做得出来。
一想到蒙古鞑子,他就想到了阿茹娜。唉———
天黑下来,空场上点了几堆火堆,火堆上架起了行军大锅,大锅里煮着羊肉,周围聚了好多人,阿穆尔丁和另一个包里的小伙子玩着蒙古式摔跤,这里有他的用武之地,他双脚灵便地闪转腾挪,不一会儿就把那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小伙子扛到了肩上,周围一阵哄笑,札兰丁不习惯这里的喧嚣,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远处看着那一堆堆篝火发愣。
卡萨尔斯走过来递给他一只羊腿,挨着他坐下小声问:白天听你说话的口音,你好像来自锡尔河草原。
札兰丁点点头接过羊肉,眼睛却还直直地盯着那通红的火焰:我家是锡尔河草原的牧户,姓萨乌丁。
卡萨尔斯一阵兴奋,他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札兰丁的对面蹲下我们是同乡,我也是锡尔河草原的老户,姓哲麦里。
札兰丁慢慢地扭过头,吃惊地盯着卡萨尔斯,他一下子想起了法图麦你姓哲麦里?和法图麦……
卡萨尔斯一听札兰丁提到法图麦,更来了精神:那是我的远房侄女他爷爷的爷爷和我父亲的爷爷是兄弟。你认识她?
札兰丁无法回答卡萨尔斯的问话。说什么呢?说自己曾和她有婚盟他觉得自己已经把童贞交给了另一个姑娘,交给了一个蒙古姑娘,就再没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了。札兰丁低下头去,半天才问:不知她现在是否还活着?
卡萨尔斯重新在札兰丁身边坐下来:活着。我在咸海西岸见过她一家。
六年了,札兰丁这是第一次听到法图麦的确切消息,眼里有些潮湿起来,他赶紧掩饰着扭头看那闪动着的火光,低声说:说说你吧。
卡萨尔斯是哲麦里家族在锡尔河草原的第五代人,到他弟兄辈这里也已有几十口人了,算是那块草原的老户了,也是望族大户。虽然平时各家忙于自己的日子不常走动,可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遇有婚丧嫁娶几十口人凑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
六年前,卡萨尔斯二十岁,家里有一个小他一岁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他被穆罕默德沙王征调进了撒马尔罕。他们也想同沙王一道抗击成吉思汗,相信蒙古人劳师远征,千里奔袭必定是疲惫之师,花剌子模以逸待劳,必将拒强敌于城外。他们在撒马尔罕夜以继日地加固城堡,搬运滚石檑木,准备保卫新都。可谁想到沙王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跑了。军心一乱城池也就不保了,蒙古人进城后挑选了包括卡萨尔斯在内的三万兵丁,随蒙古人往西朝沙王逃跑的方向追去,一直追到咸海。据说沙王在咸海的小岛上归真了,札兰丁王子继位当了新沙王。撒马尔罕被屠城的事他们也是日后才听说的。
卡萨尔斯说到这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怪不得我听你的名字这么耳熟,原来你和札兰丁王子重名。
札兰丁苦笑笑,卡萨尔斯不知道札兰丁和法图麦的婚盟,毕竟还没有正式下聘礼,还算不得有婚约,他想告诉卡萨尔斯,可想到阿茹娜,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好凑近卡萨尔斯小声地说:什么时候不打仗了,你回到锡尔河草原,转告法图麦和哲麦里爷爷,就说札兰丁还活着,只是对不起他们了。
卡萨尔斯小声地对他说,他们随蒙古军队往西追击沙王一直打过里海,一直征战了好几年,春天刚来到蒙古草原又要再打西夏,看来蒙古人是不会过消停日子的。最后,卡萨尔斯问札兰丁:你不想回锡尔河了?
札兰丁低下头去,眼睛有些潮湿:能不想?
卡萨尔斯忽然眼里闪过一丝急切:我是真不想再给他们卖命了,有机会我就跑,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札兰丁瞪起眼睛看着他:有什么办法?
卡萨尔斯凑到札兰丁耳边说:如果你能帮我,我自己就能出去,可我不敢和你一块走,人多目标大,就走不脱了。
札兰丁盯着卡萨尔斯问:你说,我怎么帮你?
卡萨尔斯回头见跟前没人,这才小声说:今晚值夜,你在我后面,到时候你起来接班上岗装不知道就行。有这个时间我就能混出去,趁这个时候还乱,以后安顿下来再想走就难了。
札兰丁紧盯着卡萨尔斯郑重地说:一定给我把信捎给法图麦,什么都不用说,只说我对不起他们就行。
卡萨尔斯点点头,他站起来向毡房走去,临走拍了拍札兰丁的肩膀:我早点睡一觉去了。
札兰丁扭头目送卡萨尔斯进了毡房,他回过头来看着火堆边喧闹的人们渐渐地安静下来,走过去拿起一块羊肉,一边啃着一边又坐回原处发呆他心里有些发堵,鲜美的肥羊在他的嘴里也失去了滋味。
刮了一天的风停了,空气中有些潮湿,天空没有星星,就像一口巨大的行军锅倒扣在人们的头上。营盘里安静下来,只有巡逻的兵丁走过的脚步声和佩刀的碰击声。札兰丁痴痴地望着篝火燃出的火苗,想起了在锡尔河草原的日子,想起了法图麦。他的眼睛也像这潮湿的空气一样湿润了依稀中法图麦模糊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动。
这是札兰丁自那年分别后第一次听到法图麦的讯息,已经六年了。他从自己的家乡被人赶到了这万里之外的蒙古草原,再也听不到锡尔河淙淙的流水声,见不到那里的青山碧草,闻不到熟悉的花香草香,他的心本来已经死了。
刚听到卡萨尔斯说出法图麦家的情况,他心里一阵激动,想向他仔细地打听一下法图麦的情况,可热烈奔放的阿茹娜几年里给予他的眷顾和一番深情也令他难忘,更何况她已经将自己交给了他,他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去打听法图麦的消息,甚至有些悔恨起自己的不忠来。
不知谁在篝火边拉起了马头琴,技法明显在伊斯玛仪之上,颤指、揉弦、抖弓,一曲幽怨艾绝的乐段让札兰丁感到一阵阵悲伤。这琴声让他想起了草原狼那一声声凄厉悠远的嗷嗷嗥叫,难道说草原狼之所以仰面朝天发出那种凄婉的吼声,也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悲欢离合,才向着它的长生天倾诉一腔情怀?草原的马头琴声里饱含着一种悲悯的情愫,可草原人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心,让苍生安静生息呢?
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此时的札兰丁和法图麦早该走到了一起坐在锡尔河草原一座漂亮的石头房子前,对着一堆篝火看着遥远星空,数着划过夜空的流星雨。
马头琴如泣如诉的乐曲让札兰丁心里一阵阵发紧,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陷入一种悲情之中。通红的火苗在他的眼里不再清晰,变成一团模糊的色块,橘黄、鲜红……
阿里来到札兰丁身边坐了下来,陪他一起静静地注视着那一团团跳动的火苗。良久,阿里轻轻地问了声:想什么?
札兰丁眼里的泪光在篝火的映衬下闪动了一下:法图麦,她还活着。
阿里吃惊地回头看看札兰丁:真的?
札兰丁点点头,嘴里重复着:法图麦还活着。
法图麦真的没有死,她还活着,此时她正坐在锡尔河草原的暮色里望着天边那片恼人的铅云发呆。
她已经回到家乡三年了,距和札兰丁分别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六年里,她和她的札兰丁只能在梦里相见。在咸海西边草原上的三年,她无时无刻不记挂着锡尔河草原,记挂着那个说好要为自己准备一份像样聘礼的札兰丁,记挂着札兰丁答应她的新房子。
在咸海西岸,每当暮霭升起,法图麦就坐在潮湿的雾气里回望家乡看到东方的地平线上有一丝云影,她就会想到家乡会不会是阴天下雨了第二天她的心情就会差到极点。有时她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丝云影会不会是远处的烟雾?那会不会就是锡尔河草原升腾起的狼烟?因为不断有人来到咸海西岸,说起蒙古鞑子的残暴,说起已经成为人间地狱的讹答剌、不哈剌和撒马尔罕,她的心就会被揪得隐隐作痛。
她开始失眠,在一个不该失眠的年龄一次次望着帐篷顶子睡不着觉每到这时,她都会在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时早早爬起来,如果东方现出灿烂的朝霞,她这一天就会觉得神清气爽,走路干活都觉得脚底下有劲儿如果那里还存有一丝暗影,这一天的饭食都会变得寡味。
后来,蒙古人打过了咸海西岸,这里和他们家乡的锡尔河都归入了蒙古人的地盘,再也不必东躲西藏了,她和家人这才终于回到了故乡,可是却再也没见到札兰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