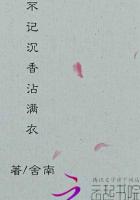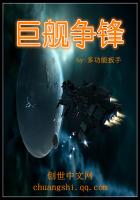巫月扭头望去,人群已自动闪开了一条通路。映翠拉着一位老丈在前,玉朱扶着一位老夫人在后,末尾还跟了几个腰跨长刀的武侯。
不等众人走到跟前,她赶紧迎上去见礼。打头这位高瘦挺拔、精神矍铄的正是里正杨明,后面那位白净富态、面目和蔼的则是他夫人宋氏。
巫月五岁以前一直住在扬州,父母两家皆是世代行医兼做药材生意。随着她家的买卖越做越大,药行于两京都开立了铺户,为方便打理,也在两地分别购置了宅院。
她在长安长到十岁,后因体弱多病又迁到了较为温暖的洛阳。她父亲巫柏青医术高超、宅心仁厚,在温柔坊的邻里中人缘甚好。
老里正的孙女丹娘与她一般大,同样羸弱,两家经常往来问诊间相处得颇为投契,便当成亲戚走动。夫妻二人对她一向爱如己出,也算多少弥补了她祖父母早逝的缺憾。
此刻见到两位老人,不管是出于原主的记忆,还是自己久无依靠的思亲之情,巫月一声“阿翁、阿婆①”叫出口,两颗泪珠儿便顺着脸颊滚了下来。
“月奴!我的儿,你可受苦了……”
宋老夫人几步上前,伸手将她揽入怀中,一时间也是哽咽难言。
杨里正不知是被那两个姑娘从哪里寻来的,一看就没少赶路,喘息了半天都没说出句整话。
映翠瞧着起急,跑到街边的铺户里借来了凳子和茶壶,几口水灌下去,杨明才算缓过劲儿来。
“丫头你可真要命,差点儿给我这把老骨头拉散架喽……”
巫月苦笑道:“今日事发突然,她们俩也是为救儿性命才心急了些,若有莽撞之处,还望阿翁见谅。”
“不必说了。“老里正沉着脸挥了下手,“巫家的事我心里有数,月儿你不在便罢,如今既然回来了,我自会与你讨个公道!”
那边的秦四娘早让人把柳氏拉回了家,另吩咐几个腿脚麻利的仆役去找家主。
转眼间她就换上了往常惯用的嘴脸,笑呵呵地走过来施礼。
“里正,夫人,这只是家里人闹得一点儿小误会,不想惊扰了众位街坊,还劳动您跑一趟,实在是罪过,老奴先替家主给您赔个不是。“
说完她又往前凑了一步,笑得愈加谄媚。
“您看这街上人多嘴杂的……要不还是请二位到屋中叙话吧。”
杨里正霍然起身,怒斥道:“老朽不才,做了二十几年的里正,如此舞枪弄棒的误会倒头回遇见!这强盗二字你喊得轻巧,可知方才若是有人报官,我也脱不开干系!况且这宅院的户主乃是巫柏青,现有他女儿在此,你请我们进屋,岂不是越俎代庖吗?!”
秦四娘一开口就碰了钉子,面上的笑都有些僵住了,正待辩解,又叫宋氏截住了话头儿。
老夫人也不看她,只一边帮巫月整理着发髻,一边冷冷道:“这巫锦程还真是耐得住性子,侄女丢了半年也不曾见他报官寻找。现下月儿回来已有半日,闹得坊内尽人皆知,他竟还未露面,却弄个下人出来应承,自家的亲叔父,反不如我们这些外姓人上心!”
宋氏话音方落,一个满头大汗的仆从就穿过人群跑了进来,口里喊着:“来了,来了,家主到了!”
众人扭向回头,但见一个富商打扮的高个男子刚好跳下马,正是巫月的叔父巫锦程。
当年巫月的祖父母行医游历路过洛阳郊外,在道旁救下了一个气息奄奄的五岁男孩,二老心生怜悯把他带回了家中医治,病好后这孩子对自己的姓名身世只字不提,且改口叫了耶娘,二老喜他乖巧便将其收为养子,起名唤作锦程。
巫锦程打小就心机深沉,喜怒不行于色。其身在商贾之家,却一直垂涎于仕途,无奈几次考取功名未果,巫家又是世代行医,虽然家资富足,但在官场一路对其并无助益。
巫柏青作为兄长见其终日郁郁,情愿出资供他生意之用,他自知进身无望,便潜心钻营,数载商海沉浮,倒也如鱼得水。近两年又和一胡商结交,专为其在闾里坊间搜罗奇珍异宝,获利颇丰,与当初的窘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巫锦程大步走到近前,一面说着:“姗姗来迟,望祈恕罪。”一面向周围众人拱手施礼,同时也快速的将相关之人都打量了一番。
巫月把他的举动全看在眼中,忍不住暗骂了一句:“老狐狸!”
她早知此人骨子里虽是见利忘义,却又深谙取舍,是个极难对付的。现下闹到这步田地,定然在他意料之外,今天倒要看其如何收场。
巫月待他拜过了一圈,便上前还礼,叫了声:“叔父。”
巫锦程足盯了她有半盏茶的工夫,才面无表情地挤出一句:“回来就好。”
杨里正也不耐烦与他客套,直接开门见山。
“今日之事纯属巫公内宅纠纷,本不该我等外人插手,但既已闹至街面,不如就由老朽当着众位贤邻替你们分解明白,亦可免双方私弊之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巫锦程稍一沉吟,随即躬身道:“有劳杨公。”
巫月作为一个成年人,自然懂得术业有专攻,她熟知的那套法律放在唐代已是毫无用武之地。而且巫锦程生性多疑,倘若锋芒过盛容易遭其猜忌,必然会影响案件的调查……
心念电转间巫月也拿定了主意,于是将自己半掩在宋氏身后,只露出一双水雾迷蒙的大眼,怯生生地回道:“全凭阿翁做主。”
噗!咳咳咳……
站在旁边喝水的萧逸看到她装兔子的模样,一口茶没咽下去,咳得是满面通红。
讨厌!
刚要入戏就跑出来破坏情绪!怎么不呛死你!
巫月低头,恶狠狠地丢过去一个杀人的眼光,萧逸顿觉遍体生寒,赶紧摆手道:“我没事……咳……你们继续,继续。”
“两位既是信任老朽,那我就不推辞了,巫公请看。”杨里正拿出一摞册子,递到巫锦程面前,“这是你兄长卧病时托付给我的手实计帐以及他在洛阳的过所,上面记载的明白,巫柏青与你早分为了两家,他现已过世,上无父母,发妻又亡,仅余一未嫁嫡女,按《户令》所列条律,死商之家财物理当由在室女收管。”
巫锦程将册子接到手中翻看,巫月因从未见过也凑上来细瞧。
这所谓的手实计帐基本上就等同于唐代的户口本,过所既是暂住证,从人口、奴婢、性别、年龄、面貌特征,到田地、铺户、家宅面积,林林总总都登记得相当详细。
其实对于这份家产,巫锦程并不十分上心。一来是已经搜刮得差不多了,二来是以他的经营,也不过七、八年的进项。
再说巫月能死里逃生一次,却不见得能躲得过下次。这笔钱财迟早会落入囊中,大可不必急于一时,更没必要拿到台面上来吵闹。
因此,他只大略翻了几下就递还给了杨里正,淡然道:“巫某仅有代管之责,现下侄女平安归来,自然都应交还于她。我来时已着人到家中去拿市劵地契,想来也快到了。”
围观的街坊邻居们见没什么八卦可看,刚要三三两两散去之时,谁知又从街口闯进来一伙人。
穿着打扮尽皆奇形怪状,一望便知是一群闲子恶少,为首之人正是巫锦程的独子--巫奇崇。
要说遗传基因确实神奇。巫月的这位堂哥若单论外貌,就长得和他父亲极为相似,一样的鹰鼻鹞目,身形高大。可脾气秉性又偏偏随了他母亲柳永秀,鲁莽残暴,说话办事从来不过脑子。已近弱冠的年纪,却书也不读,活也不干,每日里专门纠集一帮地痞无赖,斗鸡走狗、酗酒打架,完全是个标准的败家子。
在这春寒料峭的天气里,只穿了一件汗衫和半臂,又将长袖挽起,露着两条满是刺青的胳膊。
巫月突然就理解了她叔父为何要娶那么多房姬妾,但凡要再添个男丁,依着巫锦程的心性,一定亲手掐死这个混蛋儿子。
巫奇崇一摇三摆地溜达到人群当中,手冲着他爹行礼,眼睛却在周围人身上乱瞟,口里阴阳怪气的说道:“阿娘让儿过来问问阿耶要房契作甚,我也顺便来瞧瞧是哪个要夺我的宅子!”
巫锦程打老远看见他就一脑门子官司,但碍着众目睽睽不便发作,只得强压着火气道:“休要胡言!那本就是你伯父家的田宅,自当交由你堂妹收管!”
“那可不行!阿娘说了,大伯没有子嗣算是断了香火,要儿一门双祧,一子两不绝。我替巫家生儿子,这份田宅理当由我承受!她一个小女子如何挑门立户?最多打发她一份妆奁钱也就罢了。”
关于兼祧一说,巫月还是有所了解,这在父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她也清楚,宗法制度中有异姓不养的原则,若要过继必须是同族。
眼下他是想仗着外人不知巫锦程是养子,便要浑水摸鱼吗?
哼,真拿别人都当哑巴了!
巫月拉了下宋老夫人的胳膊,正准备出言挑明,一旁久未出声的萧逸却抢先说道:“《开元律》明定了子承父分,在室女只得兄弟聘财之半,依我看,这位小郎君说得甚是有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