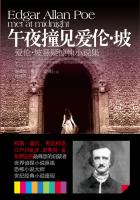矮子不服气,说个子矮的人通常脑子大,一抬头就能够仰望星空,一举目就能放眼全球。他绞尽脑汁地为我列举了一串身高在一米六以下的伟人。从拿破仑、希特勒,说到贝多芬还有我们的总设计师。他甚至嘲笑我的身高,说身高在一米六到一米七之间的男人长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一些活得最尴尬的人。
在场的子栋并不知道我和矮子在开玩笑,他说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话:“矮伯,你可能再长二十年就和我爸差不多高了。”在他看来,人会像他这个小孩一样不停地长个子,能够活到老长到老。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答应了矮子与我同行,一来带他出去转转,二来我也要一个伴。矮子现在几乎成了我身体的另外两只手,我不愿意做的,懒得做的他都会做。有他在我可以一懒到底,懒到烟叼在嘴上,手上拿着打火机也不自个儿点火,稍微停顿,矮子自会双手奉上火来。
杨二乃开车经重庆过遵义,一路把我们送到贵阳。到贵阳后我首先找到了老周哥,在贵阳一家高档的酒店请他吃饭,送了他一罐全国有名的、专供国家领导人的达川灯影牛肉干。
我们喝酒的时候回忆了去年冬天从拉萨到贵阳的历程,彼此深有感触。老周哥说在他一生的警察生涯中抓过无数的人,我是最有意思、最让他高看的一个人。杨米干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他定罪的关键时刻,他自以为平时关系好的一些官员会帮他。结果大失所望,所有和他有瓜葛的人都自保不及,替他讲一两句好话的一个没有,想半张嘴向着他都不可能。
“人是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锦上添花的事情有人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你找不到!”
对老周哥的说法我虽有些不以为然,可还是点了点头。我央求他把我再关回去年待过的监室,我要去看看那里的人,这是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的目的。
老周哥为难地说:“这几乎不可能。你没有犯罪,不好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不好羁押你。”
我说:“老周哥你可以收审我,你不是说过公安机关有权收审公民吗?”
见老周哥摇头,我说:“我现在骂你们政法委的领导混账、不讲理。你可以抓我了吧?他们胡作非为,凭什么关我,凭什么没收我的三十万?”
老周哥笑了笑说:“即使你犯了罪也不一定案子就会落在我手上,也不一定能回到去年关押的老地方。”他劝我不要这样想,更不要为了纪念一次过错而专门去犯罪。
老周哥的一番话是诚恳的,为我好的,可我还是为不能进看守所而遗憾,反复问他有没有其他办法?老周哥说我即使再进去看一下也没多大意思,前些时他提审犯人去过我原先待的监室,好像只有李荣一人是关了一年以上的,周大海被枪毙,其他人判的判了,放的放了,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我说那就安排我看一下,会见一下李荣。老周哥同意了,说他明天就安排。
第二天老周哥带我去看守所,在接见室里我等李荣时,想起石莲来看我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出乎意料的是,李荣不愿意见我,他托狱警带信给我,说是怕见到我更难过,谢谢我还想着他。
我问狱警108监室现有几个人?他白了我一眼说不能告诉我。我说想给那里关押的每人上五百元的账,他犹豫了一下,狐疑地看了看我,说里面有三十个人。
负责上账的是个胖得出奇的三十多岁女狱警,胸脯大得像屁股蛋,在将我递给她的一万五千元过验钞机时,冲我笑了笑,鼻子里哼了一声后摇摇头说:“什么样的事都有啊!”
在我接过女狱警给我的收条,看上面的收款人姓名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伯来为他的孙子上账。满头灰发的老人面对冷漠的女狱警,沧桑的脸上极尽讨好神情,颤颤巍巍的手从破旧棉袄的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叠皱皱巴巴的十元钞票,蘸着口水认认真真地数了几遍,一共是一百零五元。他迟缓了一下,递给女狱警五十元。
女狱警问老人:“没有了?”老人点点头。女狱警口气很不好地说,“专门上账,才五十元,还不如不上,找麻烦!来,在这签字。”
老人拿笔的手是抖的,像是落到纸上都困难,我想上去帮他,可他将笔放了下来,慢慢地解开棉衣的扣子,摸出里面剩下的钱,留下一张五元的票子,将其余的全交给女狱警:“同志麻烦你啦,我再上五十元。请你给我记好,我一共是上了一百元。你可别记错了哟!”女狱警将钱也不数就丢进抽屉,不耐烦地说,“真是越老越啰唆。”
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流不出来。老人本来留下的五十元或许是他的生活费,看他这个样子,想来钱是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的。他兜里剩下的五元钱,是够他在城里吃顿饭,还是够他买回家的车票?
我从包里摸了一叠钱,大约有两千元左右,在老人转身时悄悄塞进他的裤兜。老人并没有察觉,出门时回过头朝我们客气地点头。
我目送着老人在飞雪中远去的佝偻背影,看到他蹒跚的步履在雪地上留下东倒西歪的脚印,我后悔刚才没有多塞些钱到他裤兜里。
老周哥拍了拍我的肩说:“你真是个好心人,但天下事谁又能管得完呢。你就是有座金山也帮不过来啊!”
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怏怏地走出看守所。老人的背影一直在我心中,让我感到悲凉,感到凄冷。依旧坐火车的硬卧,只是这次是从贵阳去成都,而上一次是从成都到贵阳;没有押送我的人,只有我的跟班兄弟矮子,睡觉时我的手也不用拷在上下铺的梯子上。火车上的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到成都后我带着矮子去了莲花收审所,在高大的铁门边我们走过去,又走过来,徘徊了整整一个时辰。
我和矮子席地坐在冬日冷硬的地上,我指着铁门问矮子:“钢铁代表着什么?”
矮子说:“结实……牢不可破。”
我说:“专政是牢不可破的,即使它锈迹斑斑,除非它自我毁灭。但人的身体一旦不愿逆来顺受,是能够摧枯拉朽的。”
矮子看着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一位武警战士警觉地走过来,问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接人。”他打量了我们俩几眼,没再说话,正步走回哨位。
“接人”,我在心中念着这两个字,也在心中问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
许久,我明白了,我还真的是在接人,在接去年关在这里的自己。我还没完全从里面出来,在此地我为了借一支烟被人恶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份屈辱并没有淡然于心,到今天还一直记挂着。
我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烟,也叫矮子将身上的烟拿出来。我将这些烟挨个地排放在高墙的墙根下,还特意留一只打火机在烟旁。
矮子问我这是干什么?我回答他:“是留给去年的我抽!”
身边吹起了飕飕的干冷的风,抬头看了看天,太阳依旧挂在那里,照耀着它该照耀的,即使你感觉不到它的温暖。
在矮子的再三催促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扇铁门,朝着喧嚣的市区慢慢走去。
我不知道这趟来,是否接出了去年的自己?
到拉萨又希冀得到什么呢?
从拉萨机场出来,我仍住进了金谷酒店,还是208房间。这间房似乎在等着我来,当我们到达酒店前台时,原先住着的客人正在退房。去年我正是从208房间被铐走的,今年我估计它是以这种巧合来向我致歉的。
当日下午我打了一辆的士去拉萨看守所,我让车在距离看守所很远的地方停下,下车后慢慢地朝看守所走去。我想一步一步地靠近,慢慢地接触那些有围墙的低矮房屋。那些房屋在我眼前变得愈来愈大,大得我能把世态和从前看得很清楚。我看到去年的我跨进了铁门;看到自己坐在监房里发抖;看到沙丁鱼们在抱着取暖,在不停地运动;看到了一大团胡须却不见五官的脸……
我犹豫地停下了脚步,不忍心再向前走。也许去年到今年就隔这么远,日子是无法倒回过去的,只会离我越来越远,但我会触景生情,不仅仅偶尔才想起它。
我掉头转身,拔腿向拉萨市区狂奔。
走回拉萨的街上已近天黑,冬天的街头行人稀少,不时碰见几只流浪狗,它们无不翻眼瞟我一下然后疾跑。
回到金谷酒店,矮子正坐在宾馆大厅里焦急地等着我。他说:“去了这么久才回来,真让人着急。”
“去了回不来更着急,你知不知道?”我没好气地回答他。
矮子见我心情不好,马上满脸堆笑地说:“找到感觉了吗?”
“去了没走拢就回来了。坐车去很快,走回来很慢,知不知道这是啥感觉?”
矮子嘿嘿一笑,摸摸头说他能体会一些,但用嘴讲不出来,他又不是诗人,但他还是能估摸我的心思,知道我要从去年坐牢的阴影中走出来,很难,很慢。
这么多年来矮子一直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有时虽语言上无法交流,但心能够沟通。我身上空的、缺少的东西可以拿他勉强填上,在世上要找一个懂自己的人很难,矮子偏偏是比我的家人、妻子还要懂我的人。可以说,矮子懂我,比懂他自己还多。尽管他身上的恶习多,这么多年来也被我纠正得差不多了,时不时他还一副凛然正气的模样,让我觉得他快教训到我的头上了。
我对他也很了解,他心中想的我斜着眼也能看透。晚饭后,他问我是不是吃牦牛肉很上火?我“嗯”了一声,没有理会他。他再扳着手指头说“生牛肉酱”“爆焖羊羔肉”“青稞酒”这些吃下去都让人浑身火烧火燎的。他其实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想泻火,我顺手摸了五百元钱给他做开支。
他没有接我的钱,双手做了一个振翅高飞的动作,我就又给了他五百元。这回他接住了,咧开嘴笑了,说这是一次高高在上的享受。
想到他四十岁的人了还没个老婆,我就为他着急,他总是以歪门邪道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对他说:“你可甭飞狠了,栽下来就摔成一只矮脚乌龟了。”
为了让矮子享受,我让给他房间用,顶着寒冷在街上转悠了好大一圈。回去时见矮子正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抽烟,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真他奶奶的爽,简直不摆了……”说完便呼呼大睡。
看着矮子一副吃饱、喝足、嫖干睡死的模样。我竟有些羡慕他。从他身上我看到,人活着只要不多想,就不会多受折磨,就容易有幸福感,就能够很快丢掉痛苦。痛苦很多时候是想来的,不想它就根本没存在过。
我怕光着身子的矮子着凉,装作生气的样子叫醒他:“你他妈的命倒是好,到这里有福享。我到这里来,两次都净倒霉。”矮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说我不倒霉,说我已经想通了,他看得出我现在是轻松的。
本想在拉萨多待些日子,写些东西再走,雪域高原让我的心中鼓荡着诗的激情。巍峨的雪山是有天籁之音的,我能够听到,能够感受,我想把它们破译出来,可每次刚开了头就写不下去,只觉得自己的文字凡俗,不谙雪山之音,不近雪山之灵。我为此感到深深的痛,几乎天天夜不能寐,夜里写,白天全部撕掉,气愤地撕得粉碎。我用尽了自己的才思,最终却连一个字也未保留下来,只留下对自己的不屑,无奈而归。
飞回到成都后本想径直回达川,可一想到去年是除夕才回去,今年何不同一个时刻回去,反正没几天了。
在成都我找了家宾馆住下,这几天里我静静地想了想将来。我估算手上目前还有近三千万元的老本,过普通人的生活仅银行利息就够花了。人生只要要求不高,对未来期望不要太大,就不会有失败和失落,生活的前方就会一马平川,直取垂老。过高的索取只会让自己和目标背道而驰,即使你有这个胆,也不一定会有这个命。
我盘算着过完春节就带妻子和小儿去海南,在海南住上两月再去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等地,然后等娒琪和子栋放了暑假,我们一家五口去新疆,去看看妻子曾经长大的地方,到草原上去骑马,在葡萄架下摘葡萄喂到妻儿的嘴里。
在成都的这几个夜晚,我几乎天天就这样想象着,想着想着就笑着睡着了,梦中醒来,犹如在旅途中歇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