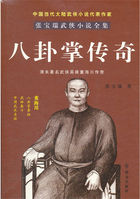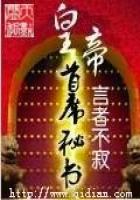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我一定得留下点什么做纪念,我撒了泡尿在境外,满怀深情地高唱了一首《我的祖国》,这一撒一唱后我的异国之旅就结束了。
第二天我坐汽车到德宏,从德宏飞昆明,再从昆明飞广州。
早上还在大山丛中的边关小镇,黄昏就到了繁华的南国都市。
陈大林和陶姐开车来机场接我。他们晚上要为我接风,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就到苏雷的川菜馆去吃吧!好久不见他了,有些想念。”
陈大林说:“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他的馆子,房我给你定好了,吃完饭过去休息。”
正是华灯初上时,大哥开着车在广州大街上拐来拐去,我从车窗望出去,两边街上灯红酒绿。车子拐进一条小街后速度慢了下来,街的两边全是水果店,琳琅满目的热带水果堆满了铺面。
苏雷的川菜馆在小街的中央,被水果店左拥右抱着。从车上下来我抬头看到一块长方形的栗色招牌,上面有三个红色大字“家乡远”,右下角是三个小字“川菜馆”。走进店堂,见里面面积不大但是布置得舒适雅致。生意看起来很不错,只有靠近厨房的一桌空着。
想到马上就要和苏雷见面,我心里乐滋滋的,来之前没给他打电话,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一位店员走过来笑吟吟地对陈大林说:“陈老板又来关照生意啦,不巧我们苏老板去了深圳,你们要吃啥我来帮你们点菜?”
我忍不住抢过话头来问:“苏老板几时走的?多久回来?干什么去了?”
店员没回答我的话,而是看了看陈大林,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陈大林连忙说:“哦,这是你们苏老板的好朋友,他从重庆来,你但说无妨!”
店员这才告诉我们苏雷是去深圳帮一个人收烂账,说是收回来了要给他三成的好处,具体的他就不清楚了。
我忧心忡忡对陈大林说,就苏雷那臭脾气,可别又弄出什么岔子来?陈大林让我不要担心,苏雷现在不是那种什么都无所谓的人,会有所顾忌。
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临走时我回头看看苏雷餐馆“家乡远”的招牌,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是啊!故乡远在千里之外,你可千万别在异乡出什么事啊!”
我到的第二天拉玉石的车到了广州,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了一周时间,从中缅边界到达祖国最南端的繁华都市,一路上平安无事,我悬着的心落了地。
货直接下到了陈大林的厂里,他和厂里负责业务的人看了这批货都很满意,就是感觉量太大了,吃不下。
我说:“这样吧,大哥,如果你资金紧,石头就放在这里,你将来慢慢付给我货款就行。”
陈大林说:“我在南海和朋友合开了一间车行,资金压在上面不少。不如发进口车给你,内地来进车的人很多,你回去一转手资金就腾出来了。”
我说:“好哇,那我巴不得,这样我又多了一桩买卖,还可再赚一笔。”
我立即就给在重庆的白镜泊打了个电话,问他公司还需不需要车。他说他公司的两台车不敷使用,正准备再买两台进口车。车型要好一点,想要凌志400和蓝鸟王。我问他什么价位能够接受,他说两辆车一百万能成交最好。
问到陈大林,凌志400和蓝鸟王这两种车他都有货,直接送重庆连送车费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八十六万元。转过来与白镜泊商定这个事情,他立即要打钱过来。我说不用了,我到达川发展时他借给过我一百万元,刚好还给他。白镜泊说他不差这笔钱用,我可以先留着。我说事情就这么定了,不要打钱过来。
事情处理完了我便急着回去,一分钟都不想在广州待。
这一趟出来这么久,心里牵念娒琪和子栋,也放不下石莲。一路上每次有打电话的机会我都不放过,不论话费有多贵。石莲挂电话前总说:“你几时回来?我太想你了!”
陈大林希望我在广州多待几天,计划带我到南海他的车行看看,我只有等下次来再说了,见我无心多留他也就没再劝。
我把在章凤赌的那块石头交给陈大林,他的工艺师说可以做两副手镯,剩下的随料随形做各种挂件。我说做成的两副手镯,一副送大嫂陶姐,一副送石莲,剩下的全雕成十二生肖。这些生肖挂件娒琪和子栋各一个,其他的送朋友。
在重庆下飞机后我直奔临江门西图大厦,白镜泊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三步并作两步。他见了我也是十分激动,把我们上次分手至今的日子记得清清楚楚。
晚饭后我和白镜泊散步,重庆的变化真大,四处疯狂向上长着高楼,跟前几年比简直翻天覆地。山城的夜景流光溢彩,让人恍惚。
“人在山中进了城,山在城中进家门。”此等写照不由得让我联想到边陲山寨的贫瘠,感叹天上人间的区别。
来到解放碑,先前的这座重庆制高点,如今像个瘦小的侏儒站在巨人脚下。我指着解放碑调侃说:“大哥你看,解放碑像不像一根竖着的男根?”
白镜泊说:“琪弟说得好。没有这根雄壮、历久弥新的生殖器插在渝中半岛,又如何能生出今天如此多的高楼大厦呢?他是这片土地的根,长出了参天的树,结出了丰硕果。”
“你不正是硕果之一吗?”我说。
白镜泊左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右手握成拳头说:“我还不够理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有些不解地问白镜泊:“如今随着大型国企的解体,大量的下岗工人涌到了社会上,而这些密密麻麻的高楼为何愈来愈高,愈来愈多?”
白镜泊转过头来看着我,认真地说:“社会的发展,有进步的时候会伴随堕落,新生和毁灭是发展中的一对矛盾。这么说吧,改革是一把双刃剑……”
我觉得他的回答过分抽象,有套话的成分,似有难言之隐。我说:“你是在回避?”
他微微叹了一声气说:“琪弟,我们不关心这些事好吗?我们尽量做好自己的事,不要也不必陷于这无底深渊的思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些是必然发生的吧……”
我伸出右手把着他的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你要是成了资本家,而我成了失业工人,你可不要认为我是活该的牺牲品,是时代的弃儿哦!”
白镜泊笑而不答,随着夜风点了点头。我们过去在一起时说过,苟富贵,勿相忘。
夜渐渐深了,街上行人稀少,我和白镜泊边谈边往回宾馆的路上走。他已经有了自己事业的根,有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活得激情洋溢,光芒四射。而我呢,我的根在哪?
家乡的小生意,那一亩三分地难道就是我的根,就是我全部的事业和毕生追求吗?
不!我在心中肯定地回答自己。
那么我的根在哪儿?我在心中一遍遍地问自己,而答案就像这愈来愈深的夜不可琢磨。
从前来重庆称为回来,如今到重庆就只能叫路过。曾经的家已不复存在,离婚就是一把无形的锯把家锯开分成两半,又让双方去重新寻找彼此对应的另一半,要么就在自己这仅有的一半上独自过完自己的一生。
到宾馆的房间以后,我照着镜子,用手使劲地拍着镜中的头,我想知道我的另一半是否存在?如若存在此时她该在何处,她是否就是石莲?或者我还是再回到毓娒身边才能够完整?
一次远行竟让我对家的意义变得耿耿于怀。回到达川后我仍没有回家的感觉,觉得还在漂泊。父母的家总归不是我的,我已成家立业,但长年包租宾馆的我,女儿和儿子还不得不寄养在二老那里。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独自在达川的小巷里漫步,这时候是我最伤感的时候,每一个窗户都似乎告诉我那是一个温馨而完美的家,人家在享受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我走到巷尾进入黑暗时,恰如从自己破裂的家的缝隙中穿过。
女儿娒琪常来办公室找我,有时坐坐走了,更多的时候是要求我回家去看婆婆爷爷。每次当我答应她时,她都会喜笑颜开,挽着我的手一起走回去。她老爱唱一首《光阴的故事》,我问她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她总是笑着回答我说:“老爸,我就是喜欢这首歌,难道不可以吗?”
我似乎明白,这首歌讲述了我们父女之间的一些故事,女儿唱着唱着就长大了,一晃都十一岁要上初中了,个头也一下长到了一米五五,她在大街上挽着我手依偎着我走时我开始有点不自在,从前都是牵着她走。
每次走到楼下她都会大声地喊,“婆婆,婆婆,我又把爸爸找回来了。”这个时候我母亲总是从阳台上探出头来慈祥地笑着,那笑容足以让我在任何暴怒和沮丧的时候马上心平气和。
我又有了大段和石莲在一起的时候,她将我儿子子栋带过来照看着,笼络着小家伙,让他开心,让他离不开她。她几次向我暗示结婚的事,我都用沉默对付过去。
怪我无情无义吗?她曾经用一封笔迹娟秀的信捏造我的卑劣行径,把我的家破成两半,为的就是和我重建一个家,一个属于我和她的家。她现在对娒琪和子栋好,是想用孩子的感情来绑架我吧?尽管我期盼着有个家,尽管我对她也是有感情的,但就是不敢和她走到婚姻那一步。
见我迟迟不答应她,她哀求:“今年我都二十七岁了,女人青春易逝,容颜易老,可我还是想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你。琪,我们该有个家了,我们结婚吧!”
结婚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白头偕老,结婚只是个形式,以此得到世俗的认可……
提到结婚,我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完全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
名分对女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得考虑石莲一而再再而三的结婚要求,何况我们该有个小孩,我也得对家人有个交代。更重要的,似乎与石莲结婚才能够证明我在那件事上彻底地原谅了她。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下了决心和石莲结婚,虽然这件事和石莲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旁听了达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对杨军一的审判。
我刚来达川时,杨军一曾在我公司下面经营部干过,解散公司后他自个单干,干着干着就将自己干进了公安局。他是因涉嫌诈骗被捕的,他还在用老一套的方法运作,将肥皂厂的肥皂诓骗到手上,贱卖以后偿还他拖欠别人已久的货款。此一时彼一时,肥皂厂等不及他再诓别人什么来填坑就报了案,新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对这一类行为定为违法,达川市公安局新成立的“经济案件侦查支队”就是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这个不长脑子,跟不上形势的家伙,人家都知道你是怎么骗的了,你还去骗不是找牢坐吗?
庭审时我看见很多过去开皮包公司,做跳楼生意的人都来了。我们彼此相顾一笑,心里怕是都在想,若早几年法律完善坐在被告席上的就免不了你我他。杨军一被当庭宣判八年有期徒刑,他老婆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听了判决抱头痛哭,判得这么重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杨军一没有在庭审笔录上签字,他振臂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好!
市场经济高于一切……
他呼喊的口号连续且不重复,众人目瞪口呆之际,他猛扑到法官席上,将主审法官打倒在地,大呼打倒“四人帮”!
几名法警冲上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杨军一按住,法官被他压在身下久了,衣服被扯成好几片,起身后愣怔在那里发抖。
谁也不怀疑杨军一疯了,我想他不是在法庭疯的,做那笔涉嫌诈骗的生意时就疯了。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每当我无法入睡时,法庭上的一幕幕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现。同在一个时代生存,为什么每个人的命运竟如此大相径庭?我想到了白镜泊、苏雷、刘萍,还有一直都无法联络得上的周向阳,甚至想到了B国那些住茅草房赤足的山民。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胆识、智慧、机遇等造就了每个人的现行生活境遇和不同的状态。我们在生活中看似时时刻刻都在主动地选择,却分分秒秒地在被动接受,循环往复地被生活所派定。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的其实就是接受。
那好吧!我与石莲结婚,时间定在旧历七月十五,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平静地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石莲,甚至都没有注意她的表情,我好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或者这个决定是别人帮我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