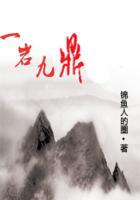一封匿名信毁了我的婚姻和家庭。
正当水车楼热火朝天地准备开业时,毓娒打电话来要我回重庆,说有十万火急的事。
这时候我离开达川是不合适的,我一再追问是什么事情,是不是非得要我回去?毓娒的态度非常坚决,口气也很硬,说我回去后自然知道原因。
我心中隐隐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向陈先生交代了一下工作后连夜赶了回去。
上午本该去上班的毓娒在家里等着我,什么话也不说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摔在我面前,叫我认认真真地读,多读几遍,读懂,读透!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从她那暴怒的神情中知道这封信一定对我不利。
展开信见是写给毓娒的,我急急地看了一遍:
毓娒老师:
你好!
冒昧地给你写这封信,我也不知道是否恰当,但忍不住的我还是提笔写了。
我该怎样来介绍我自己呢?或者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显得唐突的信?我是王琪在达川一位好朋友的妻子,我丈夫是王琪在达川形影不离的狐朋狗党。
王琪来达川后仗着生意做得好,有钱,一直都在吃喝嫖赌,和好几个女人同时明来暗往,尽干些伤风败俗的事。害得几个女人为他离了婚,而他又不理人家。起初我以为王琪没有家室,只是借着谈恋爱多搞几个女人,后来才从我丈夫口中得知,他不仅结了婚而且还有小孩。
我丈夫本来是一位老实人,可自从和王琪搅到一起后就常常日不归家,夜不落屋,动不动就跟我说离婚。他虽不敢像王琪那样明目张胆地搞,可也变得和从前判若两人。我看着心痛却又毫无办法,我实在不想家庭就这么毁了,只好给你写信,求你管管你的丈夫,哪怕是言语上的也好。
我们达川是大巴山中的一座小城,这里民风淳朴、传统和保守,从未有过像王琪这样的人,他自己干坏事还带着别人干,还标榜自己是一个诗人,说什么文人无行。我相信他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你是不知道的,你是被他蒙在鼓里的。我告诉你这一切,是为我自己,为我的家庭,也为无辜不幸的你。我们都是受害者,而只有你可以让他悬崖勒马。
至于他具体干的坏事,我不好在信中一一列举,我也难以启齿,因为他毕竟是你的丈夫。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他和一个姓徐的和一个姓顾的女子有关系,姓顾的女子还说要到重庆来找你,要你将他让给她。
写这封信我考虑再三,犹豫了好几次才决定的。希望你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挽救他等于帮助我。
我是从王琪父母那里婉转打听到你的地址的,有所打扰,抱歉。
谢谢你!
余雪梅(草)
我要过信封看,信是投递到毓娒的单位而不是家里。这封信来自达川是无疑的,整篇都是无端捏造,措辞之激烈、语言之恶毒,让我触目惊心。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一位好朋友的妻子叫余雪梅,我的第一反应是,因为我和石莲的交往,有人故意从中作梗给毓娒写了这封信。我将信折好了放进信封还给毓娒,问她:“信里的内容你相信吗?”
毓娒冷冷地说:“我相信!”
我说:“这是无稽之谈,恶语中伤;是不怀好意的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手段也太差了一点。”
我的解释令毓娒情绪激动起来,她大声说:“王琪,无风不起浪,怎么没有人写封这样的信给你说我怎么样?我早就对你有所怀疑,今天算是证实了而已。”
我见解释不通便不再说什么,搜肠刮肚地想会是谁写了这封信?
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在达川的好朋友就那么几位,没有谁的妻子名字叫余雪梅,写这种信的人用心险恶,也不会用真名。我急得青筋暴涨,又无法对毓娒辩解。什么姓徐的姓顾的女子,我根本就不认识,要说在达川男女方面的事情,我还是很注意的,除了与石莲接触,没有其他的人。再说和石莲到今天也没有到那一步啊,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一定要冷静,这件事最终会水落石出的。”我对毓娒说。
毓娒说:“事情已经很清楚地摆在面前,还不清楚?难道我要等到那些女人找到门上来要我让出你?”
我摇摇头,说了声“天方夜谭”,毓娒拿起茶几上的茶杯摔在地上说,“我不会等到那一天,谁稀罕就拿走,我奉送,反正是一钱不值的东西……”
我问毓娒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你还听不出来啊,是离婚的意思,让你无拘无束地风流快活去……”
我走开去,坐到边上去抽烟,我希望她能够平静下来,那时候我再做解释,再安慰她。
毓娒抽泣了一阵子,地上扔满了她擦眼泪的纸巾。到听不到她的哭声时,我走过去抱住她,要她相信我。
她似乎已经铁了心,偏过头说:“王琪,我们离婚吧!”我说:“不可能。就这么一封无中生有的信,破坏我们的家庭,不可能!”
她推开我说:“不仅仅因为这个,离婚的念头我早有过了。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爱是牢不可破的,同时也是纯洁的。到后来我发现你总是在破坏,你建设的同时在破坏。祸事不断,过日子让我如履薄冰。如今你竟然将污秽涂在我们的爱上,让她变得龌龊。我蔑视你生活中的这些肮脏东西,同时也为我曾经对你付出的爱感到不值,算是我有眼无珠。”
我知道毓娒大学毕业后就分到单位,和我结婚后整天围着孩子和锅碗瓢盆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我们无法想象的一面,就她的社会阅历,她的心境,肯定是无法接受信上所说的那些的。
我苦口婆心地说:“事情定有蹊跷,给我时间,弄明白了再说。”
毓娒自信地说:“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只是我无法感谢这位不相识的好心人,是她让我从自以为是的美梦——其实是他妈的噩梦中醒过来。”
“你何苦一定要一意孤行,凭一封来历不明的信就要离婚,你真是一个愚蠢而固执的女人。”我一激动话也说得不那么好听。
“呵,呵!愚蠢,是啊!我确实愚蠢,才有今天的结局,我也想早点结束这种愚蠢。”
临近中午了,我希望孩子们这个时候回来,他们或许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我问毓娒是不是该去接孩子?她摇摇头说孩子与我没关系,她已经安排了朋友去照料他们,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将事情处理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吃饭,我大口大口地喝水,以此控制自己的情绪。沉默了一大段时间,毓娒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我面前。
“你滚,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不要待在这个家里,你离了婚回达川和那些女人鬼混去。”
我低下头,什么也不说,我知道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你要是个汉子就马上和我离婚!”毓娒几乎是指在我脸上对我这么说。
我宁愿她说这话有赌气的成分,甚至是由于冲动或者情绪不稳定。可我也确实冤枉呀,那封信我想到了也受不了。我火气一下子冒了上来,拿起茶几上的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暴跳如雷地说:“离就离,有什么大不了。你纯粹是头发长、见识短,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毓娒轻蔑地冲我说:“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后悔!就怕你后悔,说同意了又不承认。”
我真是怒火中烧,外面遭了暗算,妻子又如此绝情,我联想到她从前对我的冷漠,有些怀疑这是她预谋已久的事,只是被今天这无端的导火线点燃了。
“好吧!明天就离!了你的心愿。”我气急败坏地咆哮着,像一头找不到出路的猛兽,落荒而逃般地离开了家。
出门后我在楼下的马路上徘徊,望着楼上那扇熟悉的窗户,心里一阵阵寒冷,那是我的家,家里有我的儿女,难道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要被剖成两半?
我的心仿佛在被一把刀绞割着,疼痛而又无助。我狠狠一脚踢在树干上,几片枯叶慢慢落下,弯腰拾起来两片,将它们揉得粉碎。
我等在家附近,想看到毓娒接孩子回来,怎么等也没有见到。眼看都天黑了,我拨通了白镜泊的电话,他是我最信任的挚友和兄长。我带着哭腔把发生的事对他讲了,他安慰我不要急,事发突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约好了在人民宾馆的酒吧见,我坐了出租车过去找他,望着车窗外雾霭茫茫的夜色,我忽然觉得自己心中有太多的酸楚。
这令人迷茫的城市不知还会给我往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故,但我只能去接受,去面对。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在选择生活,但实质上我在被生活屡屡设定,跌跌撞撞地走向未知的将来。
见到白镜泊以后,他说怎么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毓娒是一位知识女性,通情达理的人,我们的感情是十分有基础的,不会就这么一触即散。
“关键是事情就是这样摆在面前了,她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事情不仅仅因为这封信这么简单,她也承认早想和我离婚了。反正我也答应了她,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吧。”我说。
白镜泊说:“你们这么做让我很无奈,都有赌气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冷静和理性,以免造成你们两人终生的遗憾。事情果真要走到那一步吗?你的一儿一女又怎么办呢?大人离婚,会让孩子无辜地遭罪,想离婚的人很多,想到这一点就不离了。你可得深思熟虑,不能率性为之。”
我向白镜泊说我的难处,毓娒是铁了心要离婚,甚至说我要是不答应离婚就不是条汉子。我现在也后悔当时冲动的情况下答应离婚,我明天可以不去办离婚手续,可以赖在这个家里,但那样有什么意思,我还有什么自尊可言?我会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面对无可奈何的我,白镜泊也没主意了,说这种事朋友的意见只能是参考,最终还得自己拿主意。他问我:“琪弟,你相信命吗?”
我说:“我不相信,我现在什么都不相信。人是最差劲的动物,说起来有思想,但遇到扯淡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难免猜忌、狭隘、自私、想入非非……我只能认命,不认命怎么办?”
白镜泊说:“琪弟你太偏激了。卢梭说,人生来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冷静下来。”
“是呀,我人生自由没有看到,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所以我狗屁不如,我行尸走肉,我只能随波逐流,一旦特立独行就自食其果,就成了人所不容的异类。你知道毓娒怎么说我,说我在生活中总是一边建设,一边破坏……”
我情绪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白镜泊看到周围的人在打量我们,抬起手臂翻腕表给我看:“时间不早了,走,我去旁边给你开个房,你安下心好好想一晚上,明天慎重地拿主意。”
这一晚我躺在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很多,但似乎什么也没想,眼睁睁地看着窗户外天发白,街面上喧闹起来。
我必须去面对毓娒,只祈望她能够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想想我们的过去,看看身边的两个孩子,她能够回心转意是我人生最大的造化了。
回到家,毓娒在沙发上正襟危坐。她说:“我在等你了,介绍信都开好了,替你也开了一张。”
我问:“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替孩子想想?”
她说:“替孩子想好了,儿子跟我,娒琪跟你。”
我彻底无言了,我要她想的是孩子的将来,是孩子的健康成长,是给他们一份完整的爱。她想到的却只是怎么分开他们,谁带走儿子,谁带走女儿。
既然这样我只有答应她,离婚是要分家的,分子女,也还要分财产。钱的话,我可以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部分都给她,这部分大多在我的投资中,假以时日我会一分不少给她。
她说:“钱不要,一分都不要,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反正你只喜欢钱。等过完年我把娒琪给你送到达川去。”
这句带嘲讽的话让我哑口无言。我也不想再和她有什么争执。
就这样突如其来的,在二十四小时不到的时间内我离了婚,失去了家庭,并且莫名其妙。我发誓一定要找出写信的罪魁祸首,我要对他实行严厉的报复。
我离开家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毓娒上班,娒琪上学,儿子和保姆出去买图书。我收了几件衣服提着包在客厅、卧室来回转了几圈就是走不出门,这里曾经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港湾,住着我的妻儿,可往后它再也不属于我了。
像当初被学校开除时一样,我只手提着几件衣服和几本书,沉重地跨出了门。
上次出门时女儿和儿子抱着我腿依依不舍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我彷徨而又迷茫地挪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离家,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头其实也回不了了,我死死地咬紧牙关。
回到达川,我情绪低落,终日一言不发,一心扑在事业上。
本想瞒住父母,等以后再对他们解释,可毓娒打电话告诉了他们。为此,母亲天天暗自流泪,父亲成天阴沉着脸。
气不过的父亲最后还是跑到公司来找我,他从未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可以说是声嘶力竭:“我这么好的儿媳妇,打起灯笼都找不到的儿媳妇,你就这样放手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达川和那个莱丽、那个妖精明来暗往,暗度陈仓,哪有不漏风的墙?你在外风流不能连家都不要了,儿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你简直就是个什么责任心也没有的男人,还想成大业,做大事情……呸!”
“你不想想昔日毓娒对你有多好,人家不嫌弃你被学校开除,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不怕风言冷语,坚决和你在一起,还四处帮你凑钱开店。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人一生,平安才是幸福,家庭和睦才是幸福。你脑子里简直就是装的豆腐渣。”
我低着头,默默地听随父亲指责,在父母眼里毓娒是个好儿媳妇,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忤逆,是不争气,是有好日子不过。
我也确实对不起毓娒,没有信上所说的那些事情,我与刘萍、与花红的关系也不是正当的啊。可这些我都可以对她承认,但我错不在她所说的那些,我还是不服气。我对父亲解释说:“全是因为那封信,那封莫名其妙的信。”
父亲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我知道坏在这封信上。”他气得全身发抖,“我要是知道了信是谁写的,非和他拼命不可。”
父亲骂完了我就回乡下去了,连饭也不吃一口。
我打电话给石莲,让她到公司来,她问能不能换一个地方,到她家也可以。我说不行,必须马上来。
等石莲的那会儿我觉得奇怪,自己对她怎么是这样的态度啊?
石莲来了以后我并没有对他说我父亲来过的事,我想自己憋着。她见我陷在沉思之中,也不说什么,陪我坐在那里。
这一坐就坐了三个多小时,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石莲要回家了。出门的时候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该发生的必然发生,不该发生的也已发生了;也许开头就是一种错误,但愿结局是好的!”
她的话让我疑惑,我望着她说:“那你的意思……是往后不会理我了,全身而退?”
她说:“不,我不是那意思。正相反,我会对你好……”说到这里她深情地望着我。
我没有心情去承受这种目光,这种表达,在这个我心情乱糟糟的时候。我顾左右而言他,“时候不早了,我让矮子送你回家。”
她站了下来,双手交抱在胸前,头和上身向左右晃了晃说:“你知道我爱你。爱是会伤人的,已经伤你、伤她,接下来一定伤的是我。这是爱的代价,敢爱就得去承担,什么后果我都无怨无悔。”
她是担忧吗?那封信好在没有指名道姓说到她,父亲听到一些风声是不会在外面声张的。至于别人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说三道四我没有办法,但我一定不能够在我的困局中牵涉她,更不能让谁伤害到她。
我手搭在石莲双肩上,轻按了一下说:“放心吧,谁也伤不了你,我不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