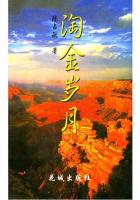杨二乃第二天就找到公司来,这个人至少有一米八的个头,长得粗壮、结实,眼神看人略带些邪气。他自我介绍,说是公安局杨局长叫他来上班的,杨局长是他哥哥,亲哥。
杨二乃坐下来抽了根我递给他的烟,就像是我的老朋友一样热络起来,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达川的人和事,什么道上的大哥是狼头,生意做得最好的是市委书记的儿子焦英,官场上分本地帮和外来帮……又讲他自己在达川是如何的风光,有性格、有脾气,从不拉稀摆带,黑白两边都要给他面子等等。
听他讲得头头是道,我说:“那以后可就得仰仗你了,你要尽心尽力做好事……”未等我话讲完,杨二乃马上把话抢了过去,“王总,这你放心,我就是没读过书,我要是读了几年书,那现在有可能邀不到台(就是很不得了的意思)呢。”
我布置杨二乃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请客,把达川当地有能力的皮包公司老板都给我请来,我请他们喝酒。
杨二乃问我请多少个,我让他看着办,但一定要请那些人品好的。
不出三天杨二乃请到了达川市十家皮包公司的老总,我在达川最好的餐厅设宴款待他们。
请来的这些人在酒桌上一落座就扯开了龙门阵,这个说最近赊了一批布料准备便宜卖掉,那个说有一批酒谁谁可以拿去抵债……各摆各人事,把达川目前的商贸状况谈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郑重地站起来端酒敬大家:“今天能认识各位我很高兴,达川是我的家乡,回来发展万望大家关照。我希望以后与在座的各位合在一起共同发财,资金我有,以后你们有困难,有业务都可以来找我。我能帮忙的一定帮到,能合作的生意,一定是双赢的,钱我们大家一起赚……”
杨二乃事先对这些人吹嘘过我,我的敬酒词和开场白表明了我与大家的合作态度,顿时赢得一片喝彩。
酒一喝开就有人在桌上和我谈生意了。一位叫刘志学的说,他最近准备撞的一批货是洗衣粉,差十万元预付款,我如果能帮他打这十万的预付款,一月之内他还我十五万。
一个叫杨军一的人说,他要来一批电缆线,差一点费用想请我帮他先垫上,只七八天就可以和我分利。
杨二乃讲这几个人是达川市皮包公司的代表人物,算是有点名气的。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他们经营得青黄不接,在生意路途上走得气喘吁吁。当时有一句话,“十个锅儿九个盖,这边揭了那边盖。”能够盖起来的就算很不错了,好歹他们还盘到一些货,有生意的路子。
在座有一位叫陈聪的很少讲话,他是这几个人中生意做得最好的,听杨二乃讲此人好色,找来的钱全用在女人身上,情妇有五六个。他胆子忒大,用钱很洒手,皇帝买马的钱都敢拿过来先用了再说。
我说:“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一条丝线和一股绳,谁更容易断不言而喻,只要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合众人之力,集集体的智慧和关系,捆在一起必然会做出大的成绩。如今商海大浪淘沙,要最终修成正果必须联合起来。”
我的话说到了他们的心里,生意做到今天他们是尝过酸甜苦辣的,当即就有人提出我来领头的意见,并得到好几个人的附和。
我以为他们也就是在酒桌上说说,哪知道第二天他们专门为这件事到我公司来与我商量。
经过几天的谋划,我决定公司下面设立三个经营部。请刘志学、杨军一和陈聪分别做这三个经营部的经理,我来全面掌控和把握。我分别和三位说这件事,他们都很乐意。
我马上在华大酒店给他们每人设一间办公室,业务人员由他们自己组织,资金和费用全由我来负责,每一笔业务下来五五分成。
说穿了我是组织他们出去找业务,把数额较大的容易过成现钱的货撞回来,然后通过打官司、法院裁决用同等价值的货物去充抵,从中产生利润。当时商品都要通过物价局核价,物价局核定的价格就具有法定效应,不管这种商品是否有市场,是否能真正流通进入消费环节。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业务很快开展起来了,河南的粮食,陕西的洗衣粉,新疆的白糖,贵州的纸张,甘肃的地毯……一批批货从外地发到了公司。货的价值都是我要求的在一百万元之上的,也是我指定的市场上能卖出去的品种。
这些商品很快就出手了,价格高低平扯,刚好可以按合同进价迅速变成现金流。另一方面,我委托重庆的赖死皮帮我接跳楼货,什么壮阳酒、解放鞋、皮革等商品一般以物价局核价的20%左右接下来准备在库房里。我们所做的业务合同执行期一般都在一至三个月,也有的合同签定后货到即付款。对于厂家派来收款的我们就无中生有地找些理由应付和搪塞。一句话,就是不付款。到最后摊牌,我们要么给你们同等价值的货物,要么你们去法院告我们,我们等法院裁决。对有的供货厂商我们还主动起诉,说质量不合格,包装不过关,鸡蛋里面挑骨头。一般的诉讼我们都让它发生在我们本地,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合同签定地和交货地点。当时的地方保护主义很强,各地都偏向着本地公司企业。加之外来厂商本地又无关系,自然吃亏的是他们。
我们的生意笔笔顺畅,单单过关,那些背后的故事精彩到可以做成热播的电视剧。很多企业都在这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被活活地整垮。
那年头三角债比比皆是,国企、集体企业、私企相互拖欠、赖账,最后弄成呆账、死账,死缠烂打,理不清解不开,很多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达川的生意是依靠着甄刚这棵大树在做的,在这里我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似乎找到了一个事业的支点。在重庆,自从白镜泊走后,我总有一种没有着落的感觉。他到南京很长时间了,我们仅通过一个电话,也不知他近况如何。
春节一天天临近,我想回重庆过年,一想到娒琪和子栋我就归心似箭。打电话回家,娒琪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哭,“爸爸我好想你,好想好想你,就是见不到你。”我心里酸酸的。
待听到毓娒的声音我就心灰意冷了,她冷漠地说:“回不回来随你便,反正我回成都。现在你和这个家反正没多大关系,你的本性就是漂泊,就喜欢流浪。”
我心一横,决定留在达川过年。我有一种预感,我和毓娒之间要发生变故,直觉告诉我这是迟早的事,这段日子生意虽蒸蒸日上,可我心里却总是忐忑不安。
大年三十晚和父母一起团完年,我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望着远近烟花爆竹起起落落。
我心中十分想念远在成都过年的娒琪和子栋,在这节日的夜晚我真想和他们在一起,抱抱他们,亲亲他们,给他们发点压岁钱。
寒风在爆竹声中呼呼而过,我在心里祝愿着,愿风为我的儿女送去节日的快乐,带去我的思念。
公司是元宵节后开始做生意的,重庆赖死皮那边发来好几车顶债的货。我希望赖死皮随货一起到达川来,我们好好聚一下,赖死皮本来答应好的却又没来。我邀请过他几次,他不是推说生意忙就是无由头地爽约。我问送货来的赖死皮手下石平,赖死皮是不是有什么麻烦脱不开身?石平吞吞吐吐地说没什么,我追问他才告诉我,赖死皮现在吸毒,时间虽不长但量已经很大。他不敢来是怕路途中瘾上来。
得知这个情况我很着急,不能看他就此堕落。晚上我打电话到他家,以朋友的身份劝他不要碰白粉,可他说,眼下时兴抽这玩意儿;这叫玩格,这种格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前些年他穷,现在有钱了该享受享受。在他的心中吸毒是一种境界,是一个人的身份、气派的象征。跟他在一起的兄弟也多半在吸。苦劝他一阵没效果,我也只好作罢,谁都知道染上吸毒要戒很不容易。
为赖死皮吸毒的事郁闷的当口,白镜泊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一个大好的消息,他已经从南京回到了重庆,一回来便到我家里找过我,听毓娒讲才知道我在达川。这两年他在南京干得很成功,积聚了重重的第一桶金,准备回来做房地产开发。
我问他杨荭是不是也一道回来了?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说:“她,不说了,没回来,我们已分手,她嫁到英国去了。”
听白镜泊的语气似乎有难言之隐,我也就没多问。我说过几天他若不来达川玩,我就回重庆,我们一定好好聚聚。他爽快地说他到达川来,过几天就来。
第二天广州的结拜大哥陈大林也打来电话,说很久没看见我了,要到达川来看我。我说太好了,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也要从重庆过来,他是个能干之人,到时我们可以好好交流。
我公司所在地华大宾馆是达川最好的一家宾馆,整个四楼被三家公司包租。我们算一家,另一家公司是市委书记儿子焦英开的。听杨二乃讲焦英是达川生意做得最大、最好的一个人。焦英主要经营钢材,由于他在达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各个道上的人都给他面子。他和银行关系更是不一般,下午需要钱上午就能如数从银行把贷款办出来。
另一家的老板叫木又寸,公司专业做生丝、青麻业务。这个人是个江湖奇人,十岁时让家里给他凑一千元做生意,他租了一辆拖拉机到农村收猪肉拉到达川菜市场批发。有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他拉着满满的一拖拉机肉到菜市场,由于时间尚早他就趴在拖拉机扶手上睡着了,一觉醒来车厢里价值一千多元的肉全被人偷光。想想回到家肯定无法向老爹交代,又怕打,他就一个人四处流浪,最后上了少林寺。在少林寺习武修身一年半,吃不下苦又一个人偷偷跑下山,四处走江湖卖跌打损伤药,小小年纪吃足了苦头后凑足两千元钱回家。1983年严打时,他因流氓罪获刑三年,案情冤枉之极,只因他酒后在大街上抱着女朋友幺妹亲嘴,当时派出所的人认为这是抓了“流氓罪”现行。他坐牢期间幺妹常去看他,出狱后便结了婚。算起来他是因为吻了自己的未婚妻坐了三年牢。
我很想和焦英、木又寸结识,平时大家在一栋楼里,去去来来难免碰头,彼此先是相互打招呼,慢慢地熟悉了便开始互相串门。他们也听说了我的一些事,所以彼此惺惺相惜,相处得不错。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做生意当中,他们差资金时找我借,我需要关系时找他们通融。
我们三人在一起打牌是玩钱的,打梭哈、砸金花。开始只是小玩,玩玩就大了,经常一场输赢在二三十万,我又多了一样不好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