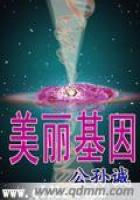经过多日反复的拉锯战,虽然阵地依然控制在我军手中,但这无名高地下的一切运输线已被全部切断。弹药、水、粮食和棉衣却一直送不上来。大虎也曾派人秘密和强行通过封锁线,但成功率几乎为零。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战士们只能躲进坑道和猫耳洞,等到敌人冲锋时他们再忍受着饥饿、干渴和寒冷和敌人厮杀。
天慢慢黑了下来,太阳又在陌生的他国外乡的山那边落了下来。大虎接过通信员刚刚从封锁线抢回的一件军大衣刚要往身上穿,但他又停了下来,对身边的通信员说:“把它送到一线阵地上去。”
大虎从干瘪的干粮袋里掏了又掏捏了又捏,然后把找出来的半把干沙面添到嘴里,他使劲的嚼呀嚼呀,始终难以咽下。是啊,被困在坑道里已经一个星期了,断水、断粮已使他们忍受着世人无可忍受的磨难。干渴火燎的咽喉已无点滴丝毫水份来滋润全身的细胞。大虎从步枪上抽下一把刺刀,存细搜索、抚摸着发暗而潮湿的坑道石壁,哪怕有一个小小的缝隙,他都要插上刺刀深深的挖上一会或几刀,哪怕只是一滴水,但都失败了,他把脸贴在有些潮湿的石壁上,把干裂带血的嘴唇贴在潮湿但无一滴水的异乡山体,突然,大虎看到石壁一角处有几颗发亮似水珠的东西在几根细草根上垂了下来,大虎几步跑上去一看,果然是几根草根上吊着几滴晶亮的水珠。大虎立即把干裂的舌尖伸了过去。
“东方……东方……我是高山……。”一阵干哑急速的电话兵的呼号传了过来。此时,大虎本能的离开了垂着的水滴,等电话兵通完话,大虎忍着嗓子的干渴疼痛提了提嗓门轻声叫到:“小江,过来。”等电话兵急速的跑过来时,大虎命令似的说道:“把它喝下去,我的那份已经报销,这几滴归你了。”大虎说完便迅速转身离去。大虎像一个急急待乳的婴儿,他把干裂的嘴唇靠在潮湿而无水的石壁上,大虎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条“哗、哗”流淌的大河,干渴难耐的大虎猛的跑了过去狠狠的喝了一顿,这甘甜清凉的河水是什么地方?大虎忽然想起来了,这是桃花沟啊,这里的水啊,清清的甜甜的,喝不尽用不完啊……
“嗒、嗒……”一阵激烈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大虎,他一个人提起一支卡宾枪离开指挥所快速向一营前沿阵地走去。
在一营前沿阵地上,趁着茫茫夜色和飘飘的雪花,大虎存细的观察着前沿阵地的一切,忽然,大虎又看到前面山下横穿公路边上那条似乎白色的、不规则的长带一样伏在地上的白色东西,他确定了,那就是敌人为了不让我们接近得到水源而严密控制封锁的那条小河,不过现在下着雪,那条小河被雪一覆盖,那白色的小河便呈现的稍微清晰。大虎伸出手来试了试风速风向,然后又看了看在寒风中飘飘的雪花,然后急速转过身去迎着刷脸的小西北风急急的朝团部指挥所走去。大虎一边走着一边对跟来的身后警卫员命令道:“快,跑步传达我的命令,二十分钟内各营、连长到团部接受行动命令。”
按照团长大虎的命令,各营、连长很快都跑步来到了团指挥所。根据团长的命令,各连都组织了“抢水队”。趁着黑乎乎的夜色和飘飘的雪花,抢水队每人都到炊事班拿了一条盛面粉用完的空袋子,在路上每人又特意各捡了一块似锤子样的石头,根据团部统一规定,在夜十点整开始行动。否则一旦十一点后随着时间和温度下降,那对砸冰一定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困难。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时间已到,负责掩护的战斗小组那黑黑的枪口紧张的监视着敌人的阵地,又住了约半个小时后,抢水队回来了,他们躲过敌人一阵阵探照灯的光柱和无目标的机枪扫射,每人还真背回了一袋子透亮的冻冻片。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抢水队又趁夜抢回了一部分冻冻片。炊事班和各个坑道内的盆盆罐罐全都盛满了冰片和冰片化成的水。
对着昏暗的油灯,团长大虎又从上衣口袋掏出了那还是抗战时期在国内西海军分区独立团徐团长为他带武工队出发时送他的怀表对坦克、神狐狸和长臂猿说:“今天是打败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吧?”“是啊,据三营报告,昨天夜里有一个班的战士在潜伏中都冻死了。今天已是第三次了。”坦克立即点头回答着。大虎望着黑洞洞的坑道口站起了身,然后接着说:“是啊,太残酷了,让我们记住他们吧。”大虎起身站了起来焦急的说:“我们的增援部队到现在还没来?”这时候长臂猿微微用胳膊碰了神狐狸一下说:“哎,神狐狸,你再算一算。”此时只见神狐狸微微抬起右手用手指弹了弹油灯上的灯花胸有成竹的双眼一眨说:“早算了,早算了,当年能打败小日本的土八路,今天的志援军照样,照样能扒下纸老虎的皮嘛。”
“你呀,我的神狐狸参谋长。”大虎看了看神狐狸然后说。大虎话刚说完,炊事班长便端上每人只有半碗热气腾腾的、用冰片烧开的热水拌炒面。当他们看着那散发着诱人香气的半碗炒面时,他们好似不舍的喝一样望着。大虎轻轻的看了看坦克说:“我听后勤来的同志说,这炒面,还是从咱胶东来的呀。”“是啊,炒面可是咱掖县凤山区的特产。说不定啊,还真是咱掖南县的啊。”坦克深情的说着。说到这里长臂猿深情的说:“乡愁啊,不能忘,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吃到娘作的炒面了。我记忆的最深的是有一次,那还是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是刚拔完麦子打完场,我正朦朦胧胧似醒非醒时,忽听厢屋磨房传来推磨的声音,我知道,这又是娘在抱着磨棍推磨,等到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娘把起早拉黑拤辫子卖的钱割的半斤肉炒出了油又把不多的一点点白面放进了锅里,然后炒呀炒,那个麦香味和油香味真是太馋人了。自从娘没了后,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从此再也没吃到炒面。”
“咳,有时在作战间隙,也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在家的那些事,那些耍伴,就拿俺桃花沟来说,从古至今流传的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都市呀,大街呀,咱们那里也不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这山呀,这水呀,养活着咱,咱要爱护她,咱要保卫她。这是咱们的家,咱要爱护她,咱要保卫她,这是咱们的家……’就拿我们桃花沟那帮同龄的年青人来说,当时都是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长大的。当时在一块那一颗颗火热跳动的心啊,是火热火热的,同龄之间,男女之间,都被歌词所打动,都在一块立下誓言,不论何事何人,不论何年何月,都永远相居桃花沟,可是现在想一想,真是孩子话,当年为保卫桃花沟,而舍弃一切。像我们当时的桃花九侠,还插草为香山盟海誓相厮相守。但人世间那有这种事,还不是都一个个分开了……?”
“团长,等战争结束了,像我们这些人还能干什么,也只能回乡找个不嫌弃咱的山姑娘过日子吧,俺可没那个福像你有两个漂亮年青的姑娘争你。”大虎听了摆了摆手:“不该叛逆的叛逆了,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骑兵战友百灵鸟……”
“团长,不想这些了,咱再唱一唱那桃花沟的歌,想一想家乡。”说着坦克一开口,大伙也跟着唱了起来:“都市呀,大街呀……。”
那古朴、浑厚的,故乡的歌,在异国他乡的大山中慢慢响起和回荡。在大虎的脑海中,仿佛又出现了桃花沟那低矮熟悉温暖的山草屋还有那清清流淌着的桃花河,那满沟盛开着的红桃花和那挂满树枝的甜甜的大蜜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