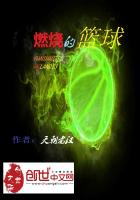她紧握刺条子正要对着牛的脊背狠打,端着一盆冷水的梅花赶紧把盆扔在台阶上,然后冲上去说:“娘,娘你何苦跟它动气呢?它要是像人一样懂事哪还叫牲口吗?看在它平时辛辛苦苦给咱们犁地的份上,你就饶了它吧。”
原本就心肠软的王翠花经她一劝就扔下刺条子走到屋檐下洗脸去了。
瞅着从牛的鼻孔里直往外冒的鲜血,梅花别提有多心疼了。心想,别看它不会说话,可其实它啥都明白。娘也真是的!下手那么重!她抚摸着它的脑袋,然后打了一桶冷水说:“你一定渴了,喝吧。”
冷水有凝血的作用,它喝水的时候,梅花就按着它的头,想让它把鼻孔在水里浸泡一会,那样,血就会慢慢止住。谁知这家伙像是有意似的,狠狠憋了一口气,又狠狠出了一口气,然后气浪把水喷出来溅的她满脸都是。
梅花伸出手掌想抽它一把掌,可见它摇头晃脑,鼻息连连,水汪汪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就没舍得打它。见它的鼻孔没再出血,就很温柔的对它说:“臭屁虫,以后别再惹祸了知道吗?你要是惹了祸,爹娘打你我会难受的知道不?”
那头牛似乎不太喜欢“臭屁虫”这个名字,那个声音很大的鼻息就像人不高兴时的叹气声一样。
梅花伸手摸了摸它的大门牙说:“臭屁虫不好听吗?谁让你平时爱放屁呀。我就是要叫你臭屁虫,臭屁虫。呵呵!臭屁虫。”
这时,白志钢回来了,看到她就说:“你咋老喜欢对牛弹琴呢?它要是能听懂人话我那就省心多了。唉!不争气呀!”
梅花这才给牛圈里放了许多草,然后把圈门关上,跟在他后面边往上房走边说:“爹,谁说它听不懂人话了?刚才我叫它‘臭屁虫’,它就特别不高兴。”
一脸不开心的花蝴蝶站在自家屋檐下把他们父女俩的谈话听的清清楚楚,于是就小声嘀咕:“哼!把我的衣裳弄成这个鬼样子了还有心情在那说笑?别以为就这么算了,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们算。”牛蹄子本来就重,那几件皮衣都被踩烂了。穿是不会再穿了,只能拿去卖了再买新的,可恐怕都没人要。
白志钢一边洗手一边说:“它要是能听懂人话,就不会把人家的衣裳踏成那个样子。唉!不要脸的牲口真是比淘气的碎娃还让人操心呀!”
梅花帮忙把饭菜端上桌子,然后问:“爹,衣裳可全烂了?”
还在生闷气的王翠花说:“不全烂也烂的没剩下几件好的了。那难缠的女人—花蝴蝶说的对,干脆把它一刀捅死算了。一年四季,天晴下雨都要人喂着,看着,真是累死人了。你回来时,她说啥了没有?”
白志钢把手擦干,拿起筷子说:“啥都没说,看样子不会为难咱。就算她故意为难,恐怕远光也不允许。好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吃饭吧。”
爱胡思乱想的王翠花说:“你太小看那臭婆娘了,远光虽然是一家之主,可啥事不听她的?夜里脱的光溜溜的,搂着远光在炕上滚三滚,他就啥主意都没了。她那个人呀,我太清楚了,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心眼可龌龊了。”
她一唠叨,白志钢就感到心烦,于是狠狠把筷子往桌上一扔,说:“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事情还没到到那个地步哩,你就先在这里胡猜乱想,万一,人家没这心思你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说着又把筷子拾起来,端着碗出去了。
咽不下那口气的王翠花冲着门外说:“你不信那咱就走着眺,真是怪了!胳膊肘子老是往外拐,那不要脸的臭女人是不是给你喝了迷魂汤了?你为啥总是向着她?”
闷了许久的梅花这才说:“娘,你就少说两句吧,爹干了一天活又累又饿,你就做个闷葫芦,好让他吃个安心饭呀。”
听到这话,王翠花有点不耐烦了,于是也端着碗来到院里。像是和白志钢过不去一样,偏偏坐在他背后,屁股对着屁股,背靠着背,吃饭的时候有意弄出很大的声响。
花蝴蝶把衣裳一件一件查看完,无意间抬头看见他们不禁感到好笑。见他们都阴着脸就想,贫贱夫妻百事衷呀!我以为你们两口子有多恩爱呢,还不是屁大一点小事就脸红脖子粗的。哼!她把脏了的衣裳放在大铁盆里,烂了的衣裳拉平整挂在屋檐下的尼龙绳上,好让王他们一家三口随时都能看的见,使他们心里不痛快。自从栋栋不在以后,她是看他们不顺眼,总觉得他们是老天派来的克星,专门克他们叶家的。
吃过饭,已经快四点多了。突然从后头沟里刮来的风把房前屋后的树吹的吱吱作响。烂棉花做的棉袄棉裤已经穿在身上,可太阳一落山,冷风透过衣裳直把人的皮肉吹的起疙瘩。
王翠花先把碗筷收拾到灶房,然后就把闪着银光的铡刀扛出来,和白志钢铡包谷杆子(玉米秸杆)。铡碎了牛吃起来省事,到时候圈里的牛粪也好拾掇。
一向勤快的梅花非要帮忙,王翠花说:“赶紧写作业去,别到了学校老师一检查这没做完受批评。”
梅花只好回到厢房,把书包里的书全倒在炕上,然后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挑出来,一本一本认真的写起来。
傍晚昏黄的天光反照在院里,是那的暗淡,冰冷,起初还能看清书上的字,不一会儿,就一个字也看不见了。为了省油,梅花就把作业收起来,准备明天再写。
明天是周末,万一碰到不会做的题,她就可以拿到清水河边去问俊娃。这是他们事先约好了的,那个不太干净的石头崖子下,虽然有栋栋和张妮的过去,可毕竟这么长时间了,一切不好的阴影也淡化的差不多了。那里比较隐蔽,他们在那里见面,不容易被村里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