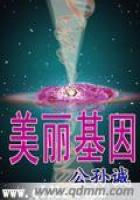此处与上一界层的构造不同,并无什么迷宫,仅有的是铺陈开的坚冰与遍地而生的晶柱,但温度较之上一层却是更冷了几分,天花板压低不少,寒气自上与下夹对着袭击二人的躯体,冰冻所带来的痛楚与怖惧之意无端就控制了大脑,不胜压抑。
况且谢荆生还曾说过,这个冰窖,不知何时便会融化崩塌……尽管它看上去坚固异常。
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呵!拓跋延抖了抖,内心之中近乎暴走地狂吼。
合眼,溯安凝住神,制造出一些驭气集于体内,却不外放,只是控制着,令驭气循着经络运转,疏通内里,以助其抗寒。
见状,拓跋延恍然明了,亦试着牵动起自己的驭气,只可惜使得不当,效用甚微。
轻轻瞥其一眼,溯安道:“走罢。”
同是年少之人,同秉持一颗好胜之心,拓跋延短时间内五次三番得助于溯安,心中自有一丝难堪与不服,于是便犟着不动,不愿顺其道而行。
尚未翻开的眼睑之下,溯安无声地亮出一个白眼。
掀开眼皮,溯安也不再说些什么,径直走出,擦过拓跋延的肩步向一方,神情漠然,瞳中仅一片寂寥的冰原之景,而一人未有。
换言之,面对拓跋延的不合作,溯安直接选择漠视,只顾自去完成后续。
诶呦,还来劲儿了是吧?!拓跋延面对溯安如此坦然的忽视,恨得有些牙痒。
可到头来,拓跋延还是跟了上去。
尽管仍是不情不愿,但拓跋延不可否认,二人并行,诚然是比一人孤立于寒气之中要暖和上些许。
二人同行奔驰许久,居于前方半步的溯安能够清晰觉察到源自后方地骚动,此骚动持续已久,几乎从未间歇,溯安内心隐隐作祟的不耐烦愈演愈烈。
于是乎,溯安突然停下了脚步。
那阵骚动地始作俑者尚是神游未归,蹭过溯安的肩角,险些摔在光滑的冰面之上。
“你干什么啊!”差点跌倒地拓跋延气道。
“你才是,在别人背后鬼鬼祟祟张望些什么?”溯安反道。
“我?”拓跋延甩了甩略有些僵化地胳膊与指掌,站直身体继而又将目光投向四周的冰面,“任务啊,找阴阳鱼啊!不这样怎么找?”
放眼,周遭皆是一片空荡,实不存有什么可藏东西地处地,倘若真要有什么阴鱼、阳鱼——大抵,也就该是被封于冰层之中了罢。
拓跋延如是想着,自认不错。
无声之间,溯安叹息。
“啊,这是什么?”视野之中忽现一黑色器物,纵于不远处一簇冰晶之中。
呃……不会就是阴鱼吧?
拓跋延一下子提腿趋向那处,每近一步,心潮便掀高一丈——这一场任务,他绝不能败!
浪潮溢于拓跋延的胸膛,以至于全然湮没了身后出自溯安的一声“小心”。
拓跋延奔向那处,正在他伸出手,将要触碰到那一状似逗符的黑色物件之时,自脚下所踩的冰面,传出了悚人的支离之声。
转瞬之间,一记脆响迸发,如破碎的镜面一般,锋利的冰层碎片陨落,向那尚是不可洞察清深之几许的冰洞底部砸去。
同一时间,将与碎冰一齐坠下的拓跋延,望见了扎立于冰洞之底、寒光与利光交错狰狞的尖锐冰晶。
先行落下的那一“阴鱼”坠地之后并不有损坏或是碎裂,而是在一撞击声后,直接化作一阵雾气消散不见——那只是个赝品。
拓跋延毫无形象地叫了出来,死死闭眼,深觉死期将至。
片刻之后:诶?怎么没掉下去?
腰部使劲,拓跋延在半空之中勉强回头向上,这才发觉,原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自溯安的物资包中划出两道强劲的筋线,一左一右束缚住自己的两条腿,且将两线的另一端头结于流星镖上,深深嵌入地面的冰层,拉扯住自己不再向下坠落,这才免遭一祸。
不然……至少得是毁容了。拓跋延略有些后怕。
“你是……蠢的么。”
最后一个字音被咬下,溯安攥住筋线的双手猛然出力,半透明的两线于空中扫荡而过,筋线那头的拓跋延被翻带而上,回归冰面之上,但免不了一顿不轻的磕碰。
“很明显是陷阱罢。”数米开外,他溯安都能够见着冰面之下被刨出洞壁的痕迹。
拓跋延心有余悸,忽地抬头撞上溯安的视线——对上一双了无温色、未有一丝波澜的眼睛,黛墨之色的球珠恍若深渊无底,却从中影映出一个,孤弱无力的自己;且于无故之中,又若衍生出隐隐几味轻蔑……如同芒刺,扎入拓跋延的肺腑与心脏。
“要你管啊!”拓跋延的双目几乎要开始吞吐火焰。
溯安再不置一词。
两人相顾,半晌无言。
转而同一时间甩过脸去,同自鼻腔肿嗤出一气。
一声倔强,溢满不甘;一声淡漠,全显不屑。
拓跋延一紧牙龈,起身便背面着溯安,于一片腾腾的寒气之中大步离去。
越隔一个空间,注视着此中一切生事的眼睛,至此愈发冷然。
·
初春的白昼仍旧落幕及早。
天色渐沉,虽不曾削弱了冰窖之中的光亮,然而温度的再降则实是无可避免。
即便如此,拓跋延仍是固执地一人面迎寒冰冷雪。
因此,他也不曾想到,即使在下了决心要在这场任务中与溯安分道扬镳之后,在空旷如此的冰窖之中,二人还是不得不再度会了面。
·
先前与拓跋延分道之后,溯安照旧行着自己的线路。
于实,他的所行之路向来不是漫无目的,早在谢荆生传达下指令之后,他便已悄然开始想周测铺散开自己的驭气,已达到感知、侦察的目的,故也不必同原来拓跋延所做的那样四处张望。
方才拓跋延所落下的洞坑十分之深,以此看来,这一层想必以是在冰窖最底了罢。
不久,溯安于某一处停住下步履。
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