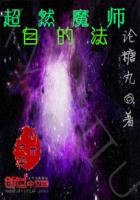(八)
我和老大的约会时间,大多都是下班之后。我骑着一辆酒红色电瓶车,在离乐园不远的天桥下等他,他每次都来不及换衣服,穿着短袖衬衣和西裤,像一个小圆点,在放大镜面前慢慢被拉长,拉近。每次在天桥下望见他,我便自觉地把身子往后座摞,双脚踩在地上支撑着轮子,然后扯开嘴笑。
老大走近,总是倒吸一口气,张开修长的腿坐到“驾驶位”上,我抱着他,哼着戴佩妮的歌,心满意足地跟着去吃好吃的。
在不会开四个轮子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工具仅限于此。
离十八岁只差半个月,我已经离开乐园。那日,爸爸兴奋地拿着我的身份证和照片让我在楼下等,手中已经准备好一大摞红色的毛主席,他说,马上你就可以见到你师傅了,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师傅。严肃的表情吓了我一跳。
我懵懵懂懂地点着头,知道我要开始学车了,好奇的并不是学车练车的模样,而是爸爸如何神通广大将还差十多天满十八岁的我报上名的。师傅解释道,你爸爸太心急了,要先交钱,让我在你满十八岁那天就把你的名给报上。
就这样,我开始学开四个轮子。
教我的师傅姓箫,也是我妈妈的师傅,当年在教我妈妈的时候还是属驾校老师,如今已自立门户自己开了个驾校,铺面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交通学院后门。由于学校刚成立不久,学员不多,每次练习都只有两三个人,踩离合踩得脚掌疼,直羡慕那些排着队练习也同样羡慕我们的别校学员。
箫师傅是个喜早的人,总在冬日被窝还有温度的早晨七点被他一个电话催醒,然后裹着厚厚的蓝色羽绒服下楼来,而教练车已早早地在路边等候。
一日,和往常一样裹好衣服坐到教练车上,转过头,后座空空荡荡,我眨巴着大眼睛望向师傅,问,“今天就我一个人啊?”
“一个人不好吗。”师傅启动油门看着挡风玻璃前方。
“好······咳咳。”干咳了两声,快速看了看脚上的咖啡色Nike板鞋,我能想象到它踩一天离合后的样子,心底瞬间生出一丝悲凉,我可怜的脚。
冬日的早晨总是苏醒的比往常季节慢很多,大雾将一切遮挡得一片严实。训练场上,只稀稀落落几辆愿意起早的教练车和一群围着厚厚围巾等待一旁的学员,一眼望去,属箫师傅的车上最为冷清,只我一人。
车内很暖,但空气闷重,一股汽油味不断涌入鼻中,我将窗户打开,憋着一股气,每到吸气时,总朝着窗外狠狠地呼吸,生怕沾染上它的味道。
坐在副驾上的师傅已经借上厕所的名义下了车,本以为可以借此偷个小懒,岂料离合刚一往下踩一抬头,师傅已经坐在了挡风玻璃前的黄色小木凳上,圆圆的眼镜框下一双更圆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盯得我毛骨悚然,赶紧松开了离合,开始一遍遍练我的“侧方位停车”。
透过教练车左边后视镜,我在倒车途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影,直愣愣地站在远处望着我,目光接触的一霎那,我躲开了,如果碰见理由都编好了,早晨雾气太大,没有看清。
那人是乐园运营部部长,也就是我曾经上司的上司的上司,一个有点矮胖,能力强大,为了穿上婚纱更漂亮而减肥每日在食堂吃素菜啃苹果,心灵知性,外表并不知性的三十岁女人。
乐园的离职是提前申请的,记得我拿离职报告书给设备长、运营专员签字时出奇顺利,直到最后一步递到她面前,她才直接跟我说了句不同意,语气是毋庸反驳的坚定,随后在办公室内找我沟通了好半天,愣是要我将离职的原因说出个所以然,我能说什么,因为我和平在一起了,所以我要离职?我深知这样会直接影响到老大,于是摆出破罐子破摔的状态,说,你要不同意我辞职我就偷偷摸摸地走,你要同意我就光明正大的走。部长尴尬地笑着,让我把离职申请书留在了她的桌上。
最后在N次要回离职申请书无果的情况下,我离开了公司,正大光明的,丢掉了半个月工资的代价下。我的表现并没有好到让一个堂堂运营部部长注意到我,所以我一度以为他们是不愿意付我那半个月工资才不让我离职的。
再一次遇见她,没想到是在驾校训练场,又一次遇见更没想到,是在驾校训练场的女生厕所门口。
“嗨。”前部长使劲用凉水冲着双手,侧着脸叫我。
“倪姐。”我也装模作样洗着手,其实只让凉水打湿指尖便涩涩地收回去,实在不愿在冬日与凉水相交,“好巧,你也在这儿。”说这句的时候,明显底气不足。
“我见你一个人练车很久了,羡慕,我们那车要排好久的队。”前部长笑着,目光随向了正在练车的同伴。
“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低着头看她扔进垃圾桶的纸巾,有点不敢看她,“踩得脚疼。”
前部长望着我,“你和平怎么样了?”像是无心带出的一句话,却在等我回答。
“······”一瞬间,像是慌了一般,愣了近三秒钟,想开口问她是如何知道的,脱口而出的却是“挺好的。”保密工作做的还不好?
“那就行。”说完前部长朝练车的方向走去,没有说再见,也只字未提未提我私自离职的事。
此后在驾校训练场再没见过她的影子。
教练师傅的话总是不灵的。
倒桩练得炉火纯青的时候,师傅坐在副驾上姿势舒服的躺着,说,“你去考吧,百分之百过。”语气好似考官是他家亲戚一般。于是我信誓旦旦去了,结果考了四次,耗时大半年。
场地练习时再也不敢马虎,师傅又跟我说,“你去考吧,百分之百过。”有了前四次经验,听见师傅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快哭了。可怜巴巴望着他老人家,“师傅上几次考试你也这么说。”果不其然,又挂了。历时小半年。
最后一项路考师傅安排我和一考了整整四次路的女孩一起,练习期间,师傅总说,“你看看人家的技术,再看看你的技术。”然后头像拨浪鼓似的摇着,样子十分滑稽,“算了算了,你这次肯定考不过,当买个经验吧。”可最后的结果是,我过了,她没过。
捧着黑色的驾照小本本,乐得笑开了花。
拿到驾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到体验店面试。工作不到一个星期,爸爸便将车钥匙交给我,于是有了这一幕交停车费的曲折。
“下班了,关机。”丹丹的一声乐叫让我瞬间苏醒。
我抬头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吓了一跳,“这么快。”甩了甩脑袋,这一日尽瞎想了。
“哎哟,肚子疼。”丹丹最近的行为越来越粗鲁,印象最深的一次她脱下盘鞋拿在手里问枭臭不臭,一群人狂笑,枭则尴尬地躲到一边没有说话,“走走走,上厕所。”说着便跑过来拉我。
“我不去。”指了指手上的平板,“关机呢。”
“平常怎么没这么积极。”丹丹喃喃道,走到枭面前说了句什么,一溜烟没了人影。
九点,天色已暗。玻璃外,是一片光灿灿的夜景,车流不息,每一盏车灯都仿佛流星,明亮的弧度划过眼睛。
“喂。”我任枭继续一排排关着屏幕,竟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常好脾气地让着我,比如我不打扫卫生的时候,偷懒的时候,抢他顾客的时候,于是久了,便更不客气。
“怎么了?”枭停住了,望着我,眸光在强烈的灯光下炯炯如星,或许是距离近的原因,里面清晰反映着我的脸。
“下班怎么回去?”我直接跳上了iPhone展示台,享受着居高临下坐着都比别人高的瘾。
枭顿了顿,眼光好似受了创伤,“走路。”半响,才吐出两个字。
“送你?”我霸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用。”枭客气地笑笑,继续开始关屏幕,“习惯走路了。”声音压得很低。
没有再说话。完毕,我坐上了那辆白色卡罗拉,没等车子升温,便将它炮弹似的弹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