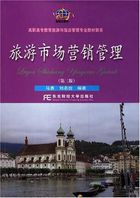(三十一)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和枭之间的关系,像两个熟识多年互相了解的好友,了解到一个眼神一撇嘴都能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像别人眼中那对恩爱又爱拌嘴的小情侣,上一秒吵架下一秒撒娇,情节就像在演电视剧;又像一对已经生活在一起许久的老夫妻,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生活的点滴上。
冬日的清晨早起是需要勇气的。
我总在枭上晚班或者休假的早晨闹钟响了还不肯起,赖在他的臂弯里不出来,直到赖皮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才慢吞吞从被窝里的臂弯处爬出来,姿势浓缩得像只乌龟。
枭睡觉睡得很死,常常在我起身换好衣服洗漱后回房间拿包还能听到他轻微的鼾声。总是忍不住凑到熟睡的人儿旁边挨上他的唇,枭的唇微启,只是稍稍抖动了一下便恢复原状继续他的美梦,感受他身体里传来一股均匀有力的热气,然后满足的关上房门去美甲店。
枭总会开我玩笑说,我今天又梦见有个姑娘偷亲我了,说话的时候半眯起眼睛,一副预备看我笑话的样子。
枭不用上班的早晨,洗手间是没有挤好牙膏的牙刷。
平日里早上上班途中路过枭工作的体验馆或者有时中午去找枭吃饭的时候枭总会送我一截。那是一截不用过红绿灯的捷径小路,在体验馆马路对面,魏叔餐馆的门前。小路很隐蔽,地图上搜不到,如果不是常常在魏叔处吃饭听魏叔讲起,可能枭也找不到。
小路往里走是旧时农家巷子的模样,又窄又破,窄巷子两旁是稀稀落落爬着青苔的高壁。巷子里很少有人,每次拉着枭走在巷子里的时候都感觉背后凉飕飕的一阵冷风,直到右转后看见另一边巷子口尽头的烟摊和烟摊背后的小面馆招牌后心里才像哽急了喝了一罐水似的瞬间舒坦开。
枭把我送到巷子尽头的时候常常看见烟摊处的老大爷拿着一根长长的黑色烟斗,银色的烟斗头裹着棕黄色的长叶子烟,老大爷看着来往的行人悠闲地吸着烟头,烟斗处是浓浓的一阵烟圈。
枭总站在老大爷的烟摊旁看着我,偶尔在我蹦跳着过马路的时候身后会传来一阵高声叮嘱,“你给我看着路上的车点!”我总偷笑着,想象着枭盯着我的背影皱紧眉头的样子,一股莫名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是喜欢看枭皱紧眉头一脸无奈的模样的。
枭不喜欢我的工作,这一点他明确表示过,‘干什么不好非要学美甲,给别人画指甲’,特别是在听我说我们店内那些鸡毛蒜皮小插曲的时候更是不耐烦,皱着眉头不说话表示无声的抗议,所以在美甲店学习的半个月时间里,枭从来没去过店里,连在哪条街都不知道,可半个月后的休假日,终于在我头天晚上的软磨硬泡下答应来店里看我。
枭来看我的那天天气很冷,已经中午了,挂在店门前榕树下的白霜还久久未散去,他身上是挂在衣柜里那件我许久未穿的纯黑色Nike羽绒服。
互穿衣服是我和枭一直以来的习惯,常常在衣柜里抓起对方的衣服就往身上套,比如枭的毛衣常常在我身上,我的卫衣常常被他穿走,但当我接过枭的电话抬头看窗外,看见他穿着黑色羽绒服立在落地玻璃前冲我挥手的时候还是愣了一下,随即放下手中的电话走了出去。
那件Nike羽绒服是我十九岁生日那天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买衣服的时候妈妈和老大都站在我旁边。我扎着丸子头,试衣服的时候把头扬得高高的问老大,好看吗,全然不顾旁边爸爸眼神里微妙的变化。那是我和父母、老大在那场三天的离家出走抗议后的第一次四人行,也是唯一的一次。
什么时候有父母的家散了,散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连打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什么时候有老大的日子也没了,过了很久,久得像隔了一整个世纪。
想到这儿,鼻子一酸,赶紧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生怕眼泪流出来,也生怕被枭看见。出门接枭的时候拉过羽绒服袖口枭的手,指尖冰凉,我一边帮他搓手一边领着他往美甲店内走,嘴里还不忘叨唠,“你怎么不把手放进羽绒服口袋里,口袋里可暖和了。”
枭静静地走,不说话。不管多冷的天气,他总是不习惯把双手放进衣服口袋,他说男生那样看起来太怂。我总是撇着嘴骂他,冷死你才好。
枭进来的时候kk坐在美甲区咯咯地笑,然后挥着手说“hello”;‘特别的女生’坐在kk旁边继续倒腾着她的假指甲,只是进门的时候抬头望了望;琳达依旧躺在收银台旁边的沙发上半侧着身子,那是没有顾客的时候她一直以来习惯的老地方,见我和枭进来的时候也没说话,眼睛一直放在我拉着枭的手上。
我是想跟同事介绍的,在心里犹犹豫豫了许久还是没有开口,反正人情冷暖也没人有兴趣知道他是谁,于是直接将枭领到美甲区,我坐在他对面。
正店休息,副店出去吃饭了,推门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美甲师的座位上给枭磨指甲,把五指磨成椭圆型。枭这次算很给面子,不皱眉头不闹,乖乖坐在那儿任我折腾他的手,与平时在家拿着死皮剪追着他跑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男朋友。”副店刚进来,眼睛瞟过我,我就急忙指着对面的枭说,副店愣了一下,随即那个黑色背影转身朝他点头示意了一下他才恍惚地点着头说了声你好。
副店是个色鬼,我总是这样跟kk说,而kk总是嬉皮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线跟我说,他只是对你一个人色罢了,话毕,总会迎上我的一拳暴力。
第一次觉得他色是在刚去美甲店做学徒的那个星期六,天气不好,下了一整天的小雨,明明是下午五点店外却是乌云压顶,店长摇晃脑袋叹着气,让大部分人都提前下班,只留下我和副店守店。
本来好好的守在美甲区涂假指甲,窗外下雨,旁边放着手机,屏幕里是韩剧里撕心裂肺的分离画面,副店突然凑过来坐到我对面问我,“要不要做指甲,雕花的?”我猛地点头像小鸡啄米,眼底是兴奋的光。对于美的东西,女生是从来没法拒绝的。
涂甲油胶只用了半个小时,雕花却用了整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指针已经指向晚上十二点。副店一边搓着我的手一边问,“要不要去吃点宵夜?”这是美甲的最后一道工序,涂手霜按摩,我分明感觉到副店那双灵巧的手在我刚做好雕花的手上来回抚摸。
“不用,我要回去了。”我笑着从副店手中抽回双手,感觉到面部僵硬的表情像在哭,随即补充道,“谢谢。”
第二次觉得他不靠谱是在一次手机没电借他手机给枭打电话的时候。刚滑开手机屏幕上就显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男孩剪着西瓜头,穿着蓝色条纹背心,踩着光脚,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尖尖的齿牙,一副可爱的模样,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小孩谁呀,这么萌?”
“他儿子。”正店冷不伶仃冒了一句,手心继续托着顾客的手在画指甲。
“不是,不是。”副店脱口而出,一把抢过手机,“我哪有儿子。”
我看着角落正在偷笑的kk,不冷不淡朝副店说了句,“你儿子真可爱。”说完转身去找kk借手机,心里的ps是,渣男,连自己有儿子都不承认!
副店笑起来,脸上写满尴尬,顿了好久才慢吞吞说,“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说话的时候低着头,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第三次下定论他是色鬼是在kk给我种睫毛的时候。当时店内种睫毛的业务虽然已经开展很久了,但真正会的人只有副店,趁着人不多副店开始教kk,之后的几天kk只要一逮着人就开始练手,当然,我也是她每天练手路上的一位牺牲者。
一次,kk正在给我种睫毛。平日里种睫毛的时候顾客都躺在美容床上,师傅坐在美容床挨着顾客头部的位置,头顶是一个光度很强的日光灯,恰巧那一日为了敷衍kk,我连美容床都没有躺,半靠在美容床上嘴里喊着“赶紧、赶紧”,kk搬了个伸缩椅坐在我对面。
种睫毛种到一半的时候,副店进来了。刚开始只是站在旁边指导kk,没两分钟就直接抢过kk手中的工具说,我来。
副店给我种睫毛的时候顺脚把美容床对面的伸缩椅踢开了,刚开始只是弯曲着身子在我睫毛上工作,后来身子越压越低,直到他弯曲的身子离我的身子还差一个拳头的距离。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把双手放在身体上,憋红了脸有点结巴地说,“那个···我想上厕所。”
“马上就好了,忍忍。”副店说着,身体依旧还在往下压,我正欲起身推开他,我的救命恩人kk突然从旁边冒了出来,“我来。”说着不由分说直接从副店手中拿过工具。
以上三点总结,副店是个对家庭孩子没责任心,喜欢吃人豆腐,好色的渣男。当然,美甲店中的这些个插曲我没有告诉枭,只是在后来枭离开店问起的时候跟他介绍,那个是我们副店长,很讨厌的一个人。